無可非議,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是世界電影史上最老練的導演之一。他的每部電影都是探索電影技巧極限的旅程,其技巧如絢爛煙花般令人眼花繚亂。當然還不止這些。
撰文 |安德烈·巴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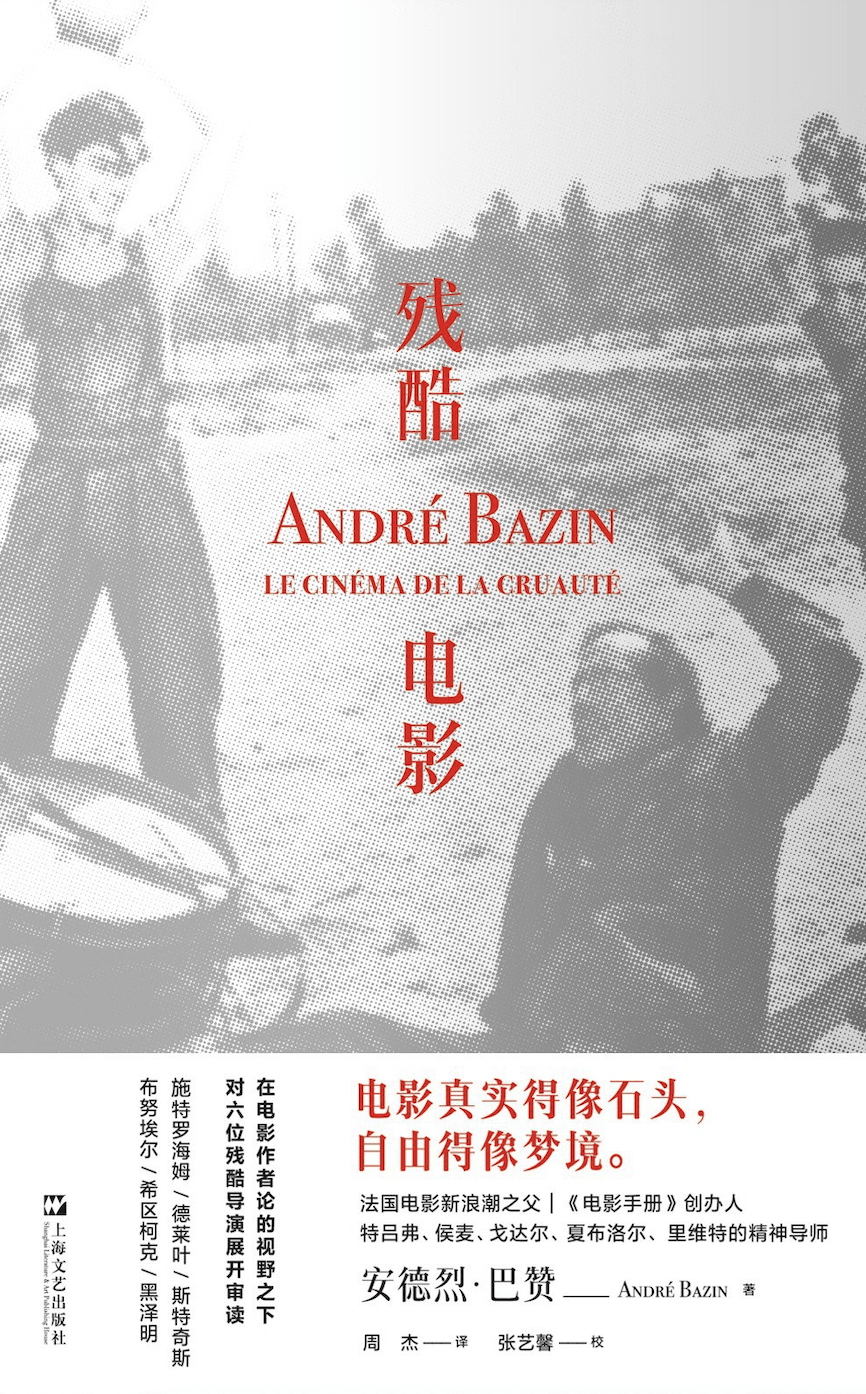
《殘酷電影》,作者: [法]安德烈·巴贊, 譯者:周傑譯 /張藝馨校,版本:版社:拜德雅|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3月
1939 年,希區柯克離開英國攝影棚,前往好萊塢,在此之前,他給英國電影留下了一部罕見的一流作品,這部電影拍攝於戰前,它就是我們最近看到的《三十九級台階》。這部電影雖然拍攝於 1935 年,但並沒有過時,可能一些次要的技術細節除外。當然,這部電影的技巧不是那麼重要,基本上,這是一部由演員主導的劇情片(多麼好的劇情!)。這部電影的場面調度迅疾而出色,但絕非雜技。希區柯克到美國時,或許就已經是氣氛與心理警探片的專家了,但還遠非攝影高手。因此,希區柯克在題材選擇方面發揮特長,從而進一步肯定了自己。這種情況在好萊塢十分常見。但另一方面,他很快越來越傾向於在技巧產生的效果和高超的場面調度上下功夫——不是在宏大與驚人的意義上,而是在更加細微的電影表達的意義上。在拍攝《辣手摧花》《愛德華大夫》《美人計》《怒海孤舟》 之後,希區柯克成了分鏡界的塞西爾·德米爾(Cecil B. DeMille)。他在電影史上有兩個獨特的貢獻,這也是他實驗的標誌,它們談不上荒謬,但也很難實現:在《怒海孤舟》中,地點的同一性僅體現在一艘救生船上;在《奪魂索》中,電影嚴格遵守時間的同一性,整部電影僅用一個鏡頭無中斷拍攝完成(實際上用了十個鏡頭,因為每個膠捲只有三百米,但這種特殊情況純粹是出於偶然,膠捲結尾的銜接並不引人注意)。
1942年的《辣手摧花》,1946 年的《美人計》,戰後我們很快熟悉了這些影片,它們幾乎與《公民凱恩》(Citizen Kane,奧遜·威爾斯導演)和《小狐狸》(Little Foxes,威廉·惠勒導演)同一時間出現。這些電影在那時引起巨大轟動,「青年批評家們」將希區柯克列入他們的美國眾神行列。他們認為希區柯克是1940年至1944年推動好萊塢電影進行重要演變的主要希望,我們法國如今也在經歷這樣的演變。正是在這個時候,亞歷山大·阿斯楚克提出「攝影機鋼筆」(caméra-stylo)的口號。其實,希區柯克的攝影機就是鋼筆,而且是一支不同尋常的派克筆。這支裝有墨水的筆無所不能,無所不寫,在水下寫,把腳踏在牆上寫,把手放在後背上寫……影像在膠片上滑動,沒有任何早期蒙太奇打字機留下的細微、老舊的摩擦痕跡。在希區柯克的掌控下,攝影機將品嘗到時態一致,以及虛擬式的未完成過去式的滋味。
我自己也對此反覆思索。我對《奪魂索》最後的幻想也破滅了。顯然,《奪魂索》中的技巧所帶來的成效幾乎未給影片增添什麼。實際上,威爾斯、惠勒甚至愛德華·迪麥特雷克(Edward Dmytryk)或者約瑟夫·曼凱維奇(Joseph L. Mankiewicz),他們與希區柯克現在所走的道路沒有可比性,但這並非意味著把希區柯克的技術看作無用功,而是已證明了且還在證明最近才被充分認識到的真相:電影不同於戲劇劇本,不只是劇本+場面調度,而是像小說一樣只有書寫與風格。然而,這樣研究的好處不在於豐富電影技巧,因為那樣的話,希區柯克就沒進行過什麼重大創新(實際上威爾斯也是),他只是在為他的技巧尋找另一種用途。
因此,可以預料到,1940年至1945年的影片在形式上的大膽與想像最終將體現在返璞歸真,即回歸到不加修飾、已被掌握的主題上。如今,先鋒不再體現為景深鏡頭與長鏡頭的使用,而是體現為聲音以及新的自由風格,從而擴大了電影的邊界。讓·雷諾瓦的傑作《大河》(Le Fleuve)就是例證。雷諾瓦通過《遊戲規則》成為這種演變的先驅者,現在他又向所有人證明,對老式分鏡的修正會走向何方:用更少的「電影」表達更多東西的可能性。可以在《偷自行車的人》(Voleur de bicyclette)和《鄉村牧師日記》中發現真正忠實於《公民凱恩》的元素。這正是希區柯克無法理解的——他電影的演變方向恰恰相反。《辣手摧花》是一部簡練翔實的作品,充滿真實的神秘與令人不安的詩學,然而它的技巧一直處於附屬地位。
一部部電影看過來,我們發現希區柯克運用的技巧越來越多,且愈加雜技化。在《愛德華大夫》中,一隻眼睛鋪滿銀幕,瞳孔成為犯罪的鏡子。在《火車怪客》中有些許進步,我們可以通過受害者跌落在地上的眼鏡所折射的扭曲倒影看到這場兇殺。

《驚魂記》劇照。
《火車怪客》的前二十到二十五分鐘可圈可點。警探片的想法也非常高明。該片可比肩格雷厄姆·格林優秀的偵探小說,另外在場面調度上,無疑也比卡羅爾·里德(Carol Reed)的《第三人》(Le Troisième Homme)中的表現主義更連貫。但在那之後,希區柯克就只是為了讓我們感到緊張而不擇手段,甚至故技重施,搬出格里菲斯在《黨同伐異》中發明的平行蒙太奇(montage parallère)來製造懸念,然而就連如今西方的B級片也不再使用該手法了:罪犯與嫌疑人之間進行的時間賽跑。這一邊,罪犯把嫌疑人的打火機放在犯罪現場,另一邊,嫌疑人要去收回這個會引火上身的打火機,但又不得不打完網球錦標賽。網球比賽本身扣人心弦,但這位電影界的紳士用平行蒙太奇這種手法同時呈現兩邊發生的動作,實在是有失身份:在兩次換髮球中間,我們看到兇手的打火機掉進柵欄下水道里。
無論如何,希區柯克的讚美者駁斥我忽略了他使用大量手段時所展現的聰明幽默。確實如此,這是該作品尚存的希望之光,藉此,希區柯克最不能被接受的修辭超越了自身,而且可以成為他的遁詞。我們知道希區柯克有個癖好:非常短暫地出現在他所有的影片中。在《怒海孤舟》中,他出現在一張雜誌照片上,這本雜誌滿是油漬,飄在船骸間。在《火車怪客》這裡,可以瞥見他扮作肥胖的音樂家,拿著低音大提琴登上火車。我們不應該只將其看作迷信或導演的個人標記。希區柯克的每部作品都有一種反諷,它提醒道,情節必定有某些言外之意,只有那些看透明顯表象的人能理解。然而,有時這個令人驚奇的潤滑機器會發出奇怪的刺耳聲。通過美國電影修辭上的、傳統上的,總之,令人安心的施虐主義,希區柯克會讓你在受害者駭人的叫聲中,聽到不含欺騙的、真實而喜悅的叫喊聲:他發出的。
《觀察家》—1952年1月17日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摘編自《殘酷電影》。作者:安德烈·巴贊;摘編:張婷;編輯:走走;校對:柳寶慶。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周刊》2023合訂本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