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無聊幾乎成了最常被提起的感受之一。為什麼今天的人們會更頻繁地遭受「無聊」之苦?在心理學家弗洛姆看來,「無聊」之所以令人痛苦,本質上是因為我們從未真正意識到無聊的痛苦。
看似同義反覆的背後,其實揭開了當下文化中的一個迷思。如今,我們的許多活動都是為了避免無聊而被喚醒的,但因恐懼無聊而產生的一系列感受和情緒並沒有隨之消失。正如我們做很多事是為了節省時間,但卻因為不知道如何利用時間,又白白消磨了時間。最終如輪中的倉鼠,陷入原地靜止的無力感。而在直面無聊、甚至嘗試學會與無聊共處之前,或許癥結在於更深的觀念層面,在於我們如何看待積極與消極的區分。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富足與厭倦》。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作者|[美]艾里希·弗洛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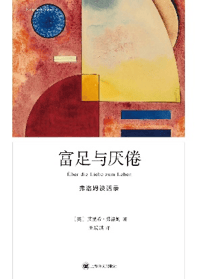
《富足與厭倦》,[美]艾里希·弗洛姆 著,王瑞琪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4年2月。
積極是激情的驅使,
本質上都是消極
現在讓我們先思考一下在過去兩千年里,亞里士多德、斯賓諾莎、歌德、馬克思和其他許多西方思想家所提出的關於積極和消極的經典概念。
積極被理解為一種表達人內在力量的東西,它賦予了生命,帶來了新生——無論是身體上、情感上、智力上還是藝術能力上。當我談到人類內在的力量時,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無法完全理解。因為我們通常認為力量和能量存在於機器中,而不存在於人體中。如果說人類擁有超能力,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發明和操作機器。我們對機器力量的欽佩與日俱增,但對人類神奇力量的洞察力卻在減弱。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有這樣一句話:「世界上有許多美好的東西,但沒有什麼比人更美好。」
這句話對我們來說已不再有任何真正的意義。在我們看來,通往月球的火箭往往比矮小的人類奇妙得多。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相信我們用現代的發明創造了比上帝造人時更奇妙的東西。
當把興趣轉向意識和作為人類潛能的多種力量的發展時,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不只是說話和思考的能力,還有獲得更深刻的洞察力,發展更成熟的能力、愛的力量和藝術的表達能力——所有這些都賦予了人類,並等待著被實現。我剛才提及的思想家們筆下的積極活動,正是人類自己發展、表現的力量,但大多被隱藏或壓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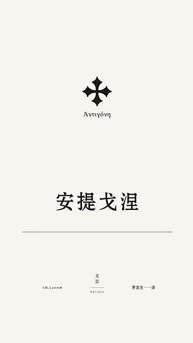
《索福克勒斯悲劇集1:安提戈涅》,[古希臘] 索福克勒斯 著,羅念生 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5月。
我在這裡引用卡爾·馬克思的一段話。大家很快就會注意到這是一個完全不同於在大學裡、媒體里、宣傳里、左翼或右翼描繪的馬克思。我引用的是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若以人為人,人與世界的關係為人的關係,那麼你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以信任來交換信任……如果你想影響別人,你必須真正地激勵和促進自己成為一個能影響別人的人。你與人、與自然的每一種關係,都必須是你真實的個人生活的某種特定表達,與你的意志對象相對應。如果你愛而沒有引起對方反過來愛你,也就是說,如果你愛著卻不能得到相互的愛,如果你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被愛的人,那麼你的愛是無力的,是一種不幸。」
「若以人為人,人與世界的關係為人的關係,那麼你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以信任來交換信任……如果你想影響別人,你必須真正地激勵和促進自己成為一個能影響別人的人。你與人、與自然的每一種關係,都必須是你真實的個人生活的某種特定表達,與你的意志對象相對應。如果你愛而沒有引起對方反過來愛你,也就是說,如果你愛著卻不能得到相互的愛,如果你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被愛的人,那麼你的愛是無力的,是一種不幸。」
大家可以看到,馬克思把愛說成一種積極的活動。現代人不會用愛來創造什麼,他們主要且幾乎只關心被愛,而不關心自己愛的能力——用愛來產生相互的愛,從而帶來一些新的東西,讓一些還不存在的東西進入這個世界。這就是為什麼人們也相信被愛要麼是一個偉大的巧合,要麼是通過購買任何可能導致被愛的東西——從合適的漱口水到優雅的西裝或最昂貴的汽車——來實現的。漱口水和西裝到底效果怎樣,我也不太清楚。不過,事實是許多男人因為他們時髦的汽車而受到喜愛。必須補充的是,許多男人比女人對汽車更感興趣。然後一切似乎步入正軌——或者過不了多久,這對男女就覺得無聊甚至憎惡,因為他們相互欺騙或覺得自己受到欺騙。
他們相信自己被愛,但實際上他們是假裝去愛,而不是主動去愛。

電影《電話情緣》(2008)劇照。
同樣地,在傳統意義上,消極不是指某人坐在那裡思考、冥想或看著風景,而是只單純做出反應或被驅使。
單純做出反應是指:我們不想忘記,我們之所以「積極」,是因為我們對刺激、對誘惑、對情況做出反應,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一旦發出適當的信號,就需要做一些事情。巴甫洛夫的狗一聽到曾經在喂食時響起的鈴聲就會產生食慾。當它衝到飼料盆前時,它當然是非常「積極」的。然而,這種積極只不過是對刺激的反應,像機器一樣運行。我們今天的行為心理學正是研究這一過程:人類是一個反應性的存在,刺激產生,並迅速帶來反應。可以用大老鼠、小白鼠、猴子、人,甚至貓來做這個(實驗),儘管有點困難。用人來做是最容易的。
我們認為,人類所有的行為大體上都是基於獎懲原則的。獎勵和懲罰是兩大刺激因素,可以預見,人類的行為和任何動物一樣,準備好去做他們會得到獎勵而不做他們被威脅會受到懲罰的事。人類甚至不需要真的受到懲罰,威脅本身就足夠了。不過還是有必要時不時懲罰一些人作為警告,這樣威脅才不會成為空洞的威脅。
現在我們來聊聊被驅使是指什麼:假設我們看到一個醉漢,他總是很「積極」,大喊大叫,指手畫腳。或者想想那些處於狂躁狀態的人。這樣的人過於「積極」,他們相信自己能夠拯救世界,他們說著話、發著電報、忙著跑腿。他們展現出超乎尋常的「積極」。但我們知道,這種「積極」的動力是酒精或躁狂症患者大腦中的某種電化學紊亂。他們的表現也是極端活躍的。
「積極」僅僅是對刺激的反應,或者以激情的形式被驅使,本質上都是消極的,不管有多么小題大做。「激情」這個詞與痛苦有關。當談到一個非常有激情的人時,你會使用一個相當矛盾的表達。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曾經說過:「嫉妒是一種激情,它(使人)狂熱地尋找造成痛苦的東西。」這不僅適用於嫉妒,也適用於一切給人帶來激情的東西:對名譽、金錢、權力和食物的迷戀。所有的癮都是製造痛苦的激情。它們都是被動的。我們今天的語言使用在這一點上有點混亂,因為激情被理解為非常不同的含義。但我現在不想多說這個。
只要工人們不感興趣,
他們就是消極的
如果你只看那些做出反應或被驅使的人的「積極」——傳統意義上消極的人的「積極」,你就會發現他們的反應並沒有帶來任何新的東西。這只是慣例。反應總是相同的:對於同樣的刺激反應相同。你很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一切都是可以預測的。此處沒有個性,力量沒有施展,一切似乎都是程序化的:同樣的刺激,同樣的效果。這也是我們在動物實驗室中觀察到的老鼠的情況。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行為心理學,它認為人類主要是一種機制,人會對特定的刺激做出特定的反應。理解這個過程,研究它,並從中得出訣竅,這就是人們所謂的科學。也許這就是科學,但它是不通人性的!因為一個活人不會以相同的方式反應。
他每時每刻都是不同的人。他從不會完全不同,也不會完全相同。赫拉克利特是這樣說的:「人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因為「萬物皆在流動」。我想說:行為心理學或許是一門科學,但它不是一門人的科學,而是一門被異化的人用被異化的方法進行異化研究的科學。它雖然能夠強調人的某些方面,但不會影響活著的人,影響尤為人性的那部分。
我想用一個在美國工業心理學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例子來澄清積極與消極之間的區別。
埃爾頓·梅奧(Elton Mayo)教授在被西部電氣公司雇用時做了如下實驗,目的是研究如何提高芝加哥霍桑工廠低文化水平工人的生產率。當時人們認為,如果早上給他們十分鐘的休息時間,或者給他們十分鐘茶歇時間,他們可能會工作得更好。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要做一些非常單調的工作,也就是繞線軸。不需要手藝,不需要動腦,它是你能想像到的最被動、最單調的事情。當時,埃爾頓·梅奧向他們解釋了他的實驗,並首先開啟了下午的茶歇時間。生產率立即提高了。然後,他又設定了晨間休息時間,生產率再次提高。進一步的福利會導致進一步的生產力,足以彌補公司因這些福利造成的費用和損失。
換作一名普通教授,他會在這一步時結束實驗,並建議公司董事們通過損失二十分鐘的時間來實現更高的生產率。埃爾頓·梅奧則不同,他足智多謀。他想知道如果削減福利會發生什麼。因此,他首先取消了茶歇時間——產量繼續增加。然後他取消了早晨的休息時間,產量仍在繼續增加。
就這一情況,一些教授會聳聳肩說:好吧,可以看出這個實驗並不具有說服力。但忽然有一個想法出現在我們腦中:也許這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對他們在工廠里所做的事情感興趣。繞線軸依舊單調乏味,但他們已經被引入了這個實驗,所以覺得自己在一個相互關係中發揮了作用,他們所做的貢獻不僅對某不知名廠主的利潤很重要,而且對全體工人都很重要。
梅奧能夠證明,正是這種意想不到的興趣和參與感,而不是上午或下午的休息,使工作變得更有成效。這為新的思考方式提供了契機和動力:提高生產力的動機更多地在於對工作本身的興趣,而不是休息、加薪和其他福利。
我只是想以此展示積極和消極之間的關鍵性區別。只要工人們不感興趣,他們就是消極的。在參與實驗的那一刻,一種合作的感覺在他們身上油然而生,他們變得積極並且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的態度。

《人生切割術》(2022)劇照。
人們沒有充分意識到
無聊的痛苦
現在讓我們來看另一個簡單得多的例子。
大家試想,有一名遊客——手裡當然拿著相機——來到某個地方,看到一座山、一片湖、一座城堡、一場展覽。但他實際上並沒有直接觀賞,而是從一開始就通過即將拍攝的照片來看。對他來說重要的現實是被記錄、被占據的現實,而不是展現在他面前的現實。圖像作為第二步,先於第一步觀賞本身。如果他的口袋裡放入這張照片,他就可以把它給朋友們看,就好像他自己創造並記錄了這世界一隅,或者他十年後仍記得他當時在哪裡。無論如何,照片作為人為的感知,取代了原始的感知。許多遊客甚至連瞧都不瞧一眼,便立即拿起設備,而優秀的攝影師會首先接收他馬上要用相機拍攝的內容,也就是說,首先與他接下來拍攝的內容產生聯繫。這種「優先觀察」就是一種積極行為。
這種差異無法通過實驗來測量。但是你可以從他臉上的表情看出這一點:一個人因為看到美麗的東西而高興。他可能會拍,也可能不會。也有一些人(當然只有少數)拒絕拍照,因為照片會破壞記憶。在照片的幫助下,你看到的只是一段記憶。但如果你試著在沒有照片的情況下回憶風景,那麼它會在你身體里重生。看到風景栩栩如生地展現在你面前,風景也就回來了。
這不是一段像背書一樣的記憶回歸,而是你自己重新創造的風景,你自己製造了這種印象。這類積極的形式使人精神煥發、如沐春風、精力充沛,而所有的消極都使人無精打采、情緒低落,有時甚至充滿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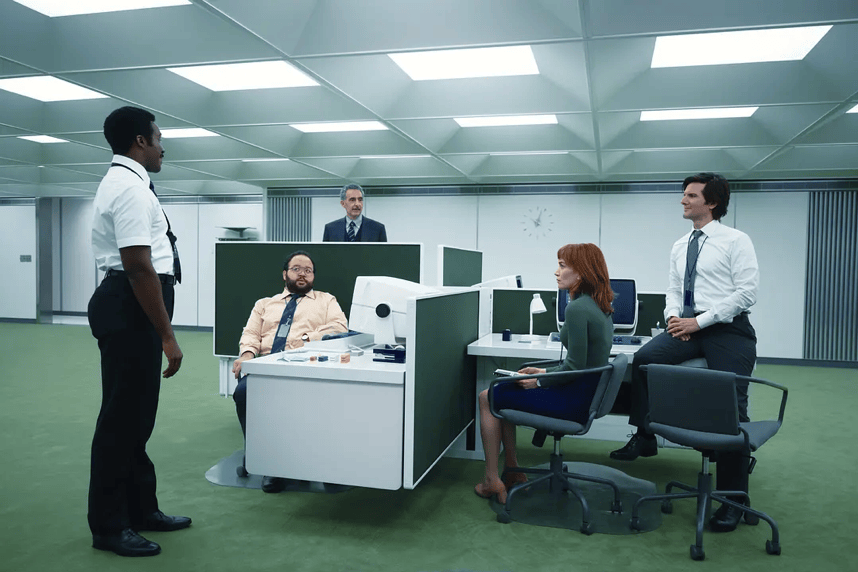
《人生切割術》(2022)劇照。
設想你被邀請參加一個聚會。
你已經確切地知道這人或那人會說什麼,你會說什麼,然後他再回答些什麼。就像在機器世界裡,每個人都說得很清楚,也很規範。每個人有自己的觀點,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當回到家時,你的內心深處會感到非常疲倦。當身處聚會,你可能看起來非常活潑和積極:你和你的對談者一樣說話,甚至表現激動,但這仍然是一場消極的談話,因為對談的雙方就像刺激和反應一樣說著自己的內容,不斷地重複「播放」著破損的、陳舊的「唱片」;沒有什麼新東西產出,只有純粹的無聊。
在我們的文化中有一個奇怪的事實,那就是人們沒有充分意識到無聊帶來的痛苦。如果有人被單獨囚禁,而且這個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不知道憑一己之力能做些什麼,他內心沒有想法去做一些鮮活的事,去產出一些東西或者召喚自己的思緒,那麼他就會覺得無聊是一種累贅、一種負擔、一種癱瘓,而這些他自己也無法解釋。
無聊是最糟糕的酷刑。它非常現代,非常猖獗。受無聊支配卻無法保護自己的人感覺就像一個嚴重抑鬱的人。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無聊是多麼惡劣、多麼痛苦?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今天我們生產了很多人們可以接受的東西,幫助人們克服無聊。人們要麼服用鎮靜劑,要么喝酒,要麼從一個雞尾酒會到另一個雞尾酒會,要麼和妻子爭吵,要麼被媒體分散注意力,要麼沉迷於性生活來掩蓋無聊。
我們的許多活動都是為了避免無聊的情緒被喚醒。但不要忘記當你看了一部愚蠢的電影或以其他方式壓抑你的無聊時,經常會出現糟糕的感覺;也不要忘記當你意識到這實際上非常無聊時,當你沒有利用好時間而是消磨了時間時而產生的懊悔。這在我們的文化中很奇怪。
我們做任何事都是為了拯救時間、節約時間,可是我們拯救或節省了時間,又將它白白消磨掉,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利用它。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原作者:[美]艾里希·弗洛姆;摘編:申璐;編輯:走走;校對:柳寶慶。封面題圖素材為《當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2007)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周刊》2023合訂本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