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3日,艾麗絲·門羅去世,走完了她92年的生命之路。雖然生命消逝了,作為小說家的她卻也早已把自己的人生以文字形式留存下來。
門羅小說的故事背景大多與她的現實生長環境有很強的相似性,其生活的某些經歷也出現在故事中,因此,在「事件」層面,門羅的寫作確實有一定的自傳性。然而,一個小說家除了使用自傳性素材,必然還需要依靠想像力的牽引乃至提升。當門羅被問到「你的故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傳性的」時,她的回答是:「就事件而言,不,不是自傳性的,但就情感而言,百分之一百,是的。」
本篇文章完整、細緻地回顧了門羅的一生,梳理了其生命經驗與小說創作之間的緊密交織,揭示了門羅「遊走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寫作特性。
我們僅以此文紀念艾麗絲·門羅。

艾麗絲·門羅(Alice Munro,1931-2024),加拿大作家,被譽為「加拿大的契訶夫」。1968年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並獲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後來共創作了14部作品並多次獲獎,同時作品被翻譯成13種文字傳遍全球,受到讀者與媒體的高度評價。2013年10月10日,艾麗絲·門羅獲得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
撰文 | 周怡(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
「我只希望我的故事是關於生活的……希望講的故事能讓讀者感受到:合上書,他從此是個不一樣的人。」
——艾麗絲·門羅(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感言)
「如果你仔細地讀了很多艾麗絲·門羅的作品,你遲早會在其中的一個故事裡,和自己面面相遇。」
——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
「你的故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傳性的?」
這幾乎是門羅在每次訪談中都會被問到的問題。
而門羅是這樣回答的:
我猜我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標準答案……就事件而言,不,不是自傳性的,但就情感而言,百分之一百,是的。就事件而言,即便是像《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這樣的作品——我猜我或許可以稱這一部為自傳性小說——故事裡所發生的事都已經對現實生活中真實發生的事做了藝術轉換了。有一些事件是完全虛構的,但情感是真實的,譬如女孩對母親的感情,對男性的萌動,以及對於人生的所有感悟……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自傳性。對此我完全不否認。
——艾麗絲·門羅(約翰·邁特卡夫訪談)
門羅同時舉出了《星期日的下午》《男孩和女孩》以及《烏特勒支停戰協議》這些故事為例——她最初使用自傳性素材的嘗試。
門羅從不迴避自己對真實生活的使用,她從不迴避自己書寫的就是「她的生活」,而且她會反覆使用「真實的生活」,儘管這樣的創作傾向對於大多數作家而言是危險的,因為評論界的傳統觀念認為,非虛構類作品的藝術性要低於虛構類作品,例如諾貝爾文學獎的設立初衷就是頒給創作理想傾向作品的作家。琳達·哈欽在《加拿大後現代主義》一書中特別以門羅作品的這種特質,論證體裁之間傳統限界的消失,即長篇小說與短篇故事、虛構類與非虛構類、小說與傳記之間界限的消失,代表了一種後現代主義的態度。對於門羅而言,在創作中嵌雜自傳性的「生活寫作」,也是她突破傳統束約、自我探尋的一種書寫策略。
小鎮:靈感之源
1931年7月10日,門羅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休倫縣的威厄姆鎮,人口2900。在門羅日後的寫作中,這個具有典型安大略地區特徵的小鎮始終是她最重要的靈感之源。《謝謝讓我們搭車》就發生在休倫湖邊上一個荒涼衰敗的小鎮,「教堂灣,人口1700人,公路布魯斯出口。」而在《關係》中,敘述者說:「我們住在西安大略休倫縣的達格萊墟鎮。小鎮邊界有塊牌子上標著小鎮的人口:2000。」在門羅筆下,無論是「歡樂鎮」「塔上鎮」「達格萊墟鎮」「漢拉提鎮」「羅甘鎮」「卡斯德爾鎮」還是「沃雷鎮」,都同樣僻遠封閉,必須經過「一個複雜的由大路和小路組成的道路系統」,並且「從地球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輕輕鬆鬆地到達。」(《關係》)
門羅是她那代人中非常典型的安大略人:父親是蘇格蘭後裔,母親是愛爾蘭新教徒,兩邊家族都是在1810年至1820年間,即拿破崙戰爭之後的大移民時期遷移到安大略的。在《荒地小站》《錢德利家族和弗萊明家族》《愛的進程》中,門羅都使用了很多母系愛爾蘭祖先的素材,而在短篇小說集《岩石城堡上的風景》中,門羅則借用了父系蘇格蘭裔雷德勞家族的遷移背景,「以安崔克的故事起頭,隨著開拓者們西進至伊利諾伊斯州,又一路北上來到了安大略,最後回到了開拓者們的家族宗譜,並以作者尋訪失落墳墓的場景結尾:作者被困於高高過膝的長青藤蔓而動彈不得……既是回憶錄,同時也是一部虛構作品。」(卡爾•米勒)
門羅的父親羅伯特·雷德勞性格溫和,隨遇而安;而母親安妮·錢梅尼則出生貧寒卻立志向上,與當時的加拿大小鎮環境格格不入。另外門羅還有一對年幼的弟妹。在其處女作《快樂影子之舞》的開篇故事《沃克兄弟的牛仔》中,門羅就是以自己的家庭為藍本,塑造了典型的喬頓一家:雄心勃勃的母親、沉默避世的父親、敏感而愛幻想的大女兒、以及務實精明的弟弟。這也成為門羅最具標誌性的家庭模式。門羅尤其寫了很多探索母女關係的作品,譬如短篇小說集《女孩和女人的生活》《你以為你是誰?》,以及其他眾多的短篇故事如《紅裙子——1946》《艾達公主》《渥太華山谷》《愛的進程》《冬日寒風》《烏特勒支停戰協議》等。母親是門羅藝術的啟蒙者,也是情感的操控者和禁錮者,是門羅作為獨立個體在成長中必須褪去的束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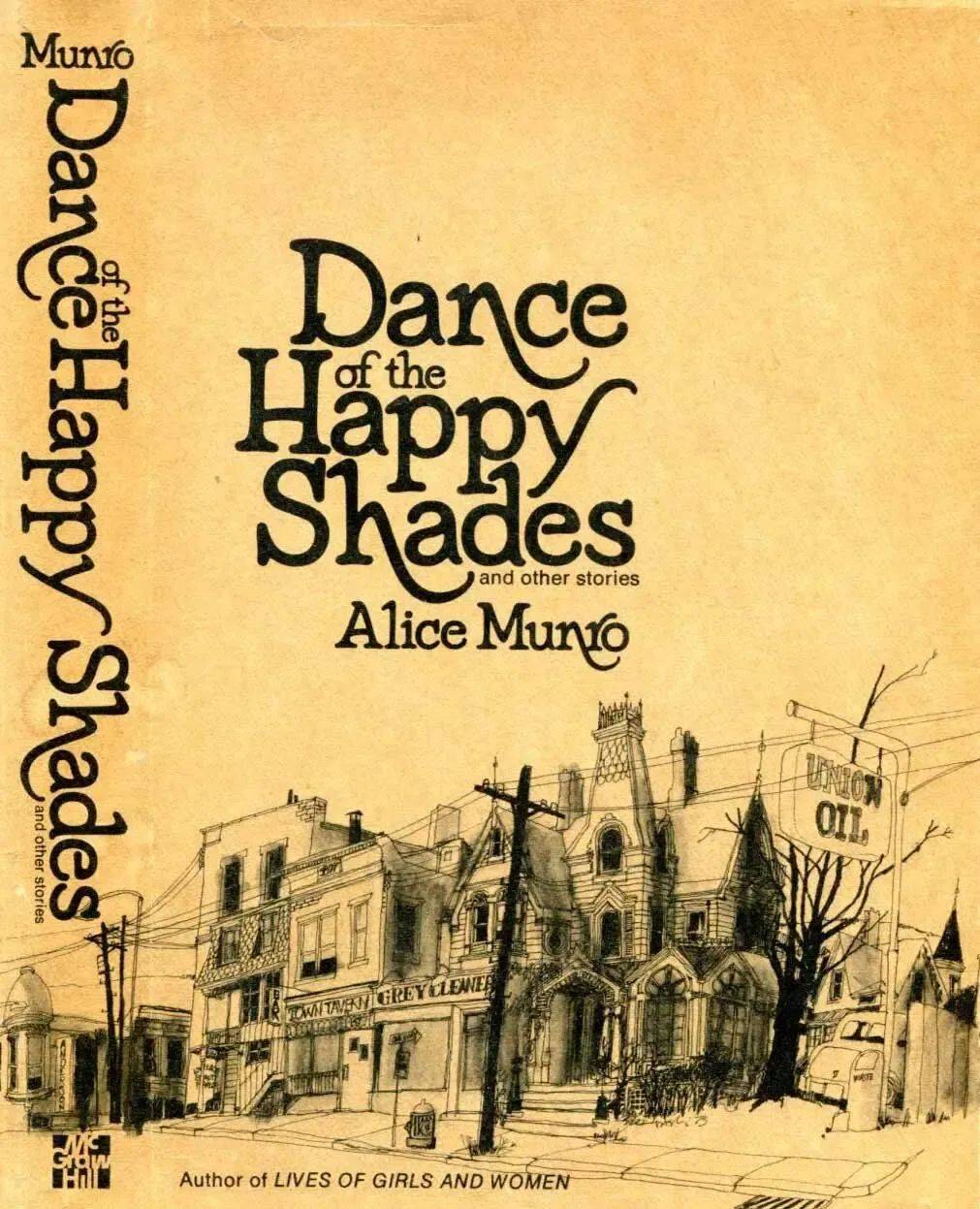
《快樂影子之舞》外文版封面。
門羅的父母當時經營家庭養狐場,最多的時候養了超過200隻狐狸。這段經歷也被栩栩如生地記錄在了諸如《男孩和女孩》的很多故事中:「我的父親是一個養殖狐狸的農場主。也就是說,他養銀狐,養在圍欄里;每到秋天和初冬的時候,他會把它們殺了,剝皮,把皮毛賣給哈德遜灣公司或者是蒙特婁皮草行。」同樣反覆出現的還有小路盡頭的房子、拮据的家庭經濟、孤寂敏感的成長、封閉壓抑的小鎮道德……門羅在《弗萊茨路》中這樣寫道:「我們的屋子位於弗萊茨路的盡頭……弗萊茨路不屬於鎮里也不屬於鄉下……」而在《錢德利家族和弗萊明家族》中,門羅更詳細地描述了家庭環境的尷尬:「我們住在達格萊墟鎮西的一條路的盡頭……我家的房子很體面,是一座相當規模的磚頭房子,但它已經漏風了,格局也舊了很不方便,門板也需要重新油漆了。」類似的房子在門羅筆下數不勝數,帶著強烈的哥特主義風格,充滿了象徵意味:到處漏風的窗戶、吱吱呀呀的樓梯、廢棄不用的傳送菜的通道、後建的不隔音的廁所……
1937年,年幼的艾麗絲進入威厄姆鎮邊緣的下城小學讀書——她在《特權》里記錄了學校獨特的「蠻荒」氣質。「那個學校……就是我自己讀過的學校。那是全書中最具自傳性的一部分。也是我所寫的最具自傳性的一個故事。但是它真的就是那樣的。」(羅伯特·撒克:《艾麗絲·門羅:書寫她的生活》)1939年,艾麗絲8歲,母親將她從下城小學轉至鎮中心的威厄姆公學,從此她每天長途跋涉,跨橋穿越過西威厄姆下城,進入相對繁榮的威厄姆鎮,穿過鎮中心,再到達學校。引用《皇家棒打》中的經典片段:
那就是漢拉提和西漢拉提,中間有條河隔開了他們。這裡是西漢拉提。在漢拉提,社會結構是從醫生、牙醫、律師到鑄造廠的工人到小工廠的工人到馬車車夫;在西漢拉提,從上至下則是由小工廠的工人與鑄造廠的工人到大量的窮人家庭,比如說釀私酒的,妓女,還有不成功的小偷什麼的。蘿絲覺得她的家就跨在河上,因此哪裡都不算,但那並不是真的。她家的店是在西漢拉提,因此他們也屬於西漢拉提,就在主街扭扭曲曲的尾巴的盡頭。
河岸兩邊的巨大差異不僅僅是地理上的,更是經濟、文化、社群層面的,這種強烈的階級意識在幼年的艾麗絲內心打上了深刻烙印。
1944年,艾麗絲通過高中入學考試,升入威厄姆高級中學。在另一個故事《半個葡萄柚》中,門羅僅以一句話開篇:「蘿絲通過了入學考試,她走過了橋,進入了高中。」與此同時,門羅的母親開始出現帕金森綜合症的早期症狀,家庭的狐狸養殖場也因受二戰影響而最終破產。1944年至1949年是雷德勞家庭最困頓的時期。艾麗絲忙於照顧生病的母親和年幼的弟妹,沒有太多時間學習,但她會在考試前幾天拚命熬夜背書。1949年,艾麗絲以優異的成績從威厄姆高級中學畢業,並拿到了西安大略大學為期兩年的獎學金,由此她得以離開故鄉小鎮,進入大學學習。
西安大略大學—溫哥華—維多利亞:
離家與歸家
1949年,艾麗絲入讀西安大略大學。那年西安大略大學總共招收了4000名學生,其中二戰老兵占了差不多一半,而女性學生的人數則很少,比起戰時大有減退之勢。大部分女生都來自安大略省西南部的普通農戶家庭,不少人都與艾麗絲相同,是靠著獎學金才得以入學。「只有靠獎學金支付她的學費,靠(家鄉)小鎮提供的獎勵金買她的書,用300元的助學金做生活費;就那麼多了。」(《乞女》)因此艾麗絲在學校勤工助學,有時也會為了一些額外的花銷去賣血。英國文化研究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理察·霍加特曾在《文化素養的運用:工人階級生活面面觀》中首次提出「獎學金男孩」的概念,指出這樣的身份標籤暗示了一種文化背景的劣勢,大部分獎學金男孩都來自下層勞動階級家庭,僅憑超乎常人的學習天賦才得以進入大學學習,他們同時會具有矛盾的雙重性:既希望保留原有階級的根,又介意自己的背景,渴望與勞動階級原本的群居屬性分道揚鑣。艾麗絲作為「獎學金女孩」也經歷了同樣的邊緣感,正如霍加特一針見血指出的:「情感上被從自己原有的階級中連根拔起,倍感孤獨。」
1950年,基於共同的文學愛好,艾麗絲與同學吉姆·門羅相識相戀。吉姆是富裕中產階級家庭的長子,熱愛藝術,聽歌劇與古典樂,性格保守,言談舉止從容得當;而艾麗絲出身小鎮的勞動階層,口音明顯,敏感又自尊,個性更自由化。後來,門羅在很多作品中都對這種因階級差異而導致的文化隔閡進行了深刻剖析。比較典型的是在《乞女》中,艾麗絲化身為貧窮的來自西漢拉提鎮的鄉下女孩蘿絲,吉姆則變成了溫哥華島豪宅里長大的富家公子哥帕崔克。為了去溫哥華見帕崔克的家人,蘿絲賣了更多的血去買新衣服,結果卻被帕崔克家面朝大海的豪宅壓抑得幾乎無法呼吸:
到處都是引人注目的大尺寸,以及不同尋常的厚度。毛巾很厚,地毯很厚,刀和叉的把手也很厚。到處都彌散著一股令人不安的絕對的奢華。在那屋裡待了一天時間左右,蘿絲就覺得泄了氣,手腳無力。她鼓起力氣拿起刀叉;那些炙烤得恰到好處的牛肉卻讓她不敢切割,難以下咽;她幾乎連爬上樓梯都氣喘吁吁。她以前從來不知道有些地方會如此地讓人感到窒息,完全地扼殺生命力。雖然她原先也去過一些不太友好的地方,卻都沒有這一次的感受強烈。

門羅,1968年。
1951年,為期兩年的獎學金結束,門羅不得已退學。同年聖誕節,吉姆為門羅做出犧牲,提前畢業以便能夠和門羅結婚。婚後不久吉姆就去了溫哥華的伊頓百貨商店入職,門羅也隨遷至溫哥華,成了全職家庭主婦。門羅很快成為三個孩子的母親。家務的職責幾乎占據了她大部分時間並使她筋疲力盡,因此門羅遭遇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創作「瓶頸期」。她只能在洗碗的時候構思故事,在洗衣房等衣服烘乾的時候把文字一點點整理在紙上。在此期間,她曾向加拿大藝術委員會申請寫作項目經費,沒有成功。事後,門羅認識到她失敗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她在申請書上寫想用項目經費請保姆,這樣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寫作;而一個男性作家申請經費時則會使用做「風土人情考察」之類更為堂皇的理由。
1960到1961年,門羅因為寫作需要短期租住了一位朋友家的辦公室,並以此經歷創作了名篇《辦公室》:一個年輕女作家臨時租了一間用於創作的辦公室,卻因房東無休止的偷窺與騷擾而被迫搬出。門羅後來還寫作了《有關寫作<辦公室>》,將其稱為「是我所寫過最直接、最具自傳性的一個故事。」門羅後來在《環球郵報》的訪談中說:「當我想到男性作家……當我走進一位男性作家的住宅參觀他的書房的時候,我簡直沒法表達心中的敬畏之心。你知道的,就感覺到整座房子都是專門為他的寫作而服務的。」但是女性作家呢?即便她可以關上門寫作,社會的責備目光卻仿佛無處不在。
1963年,吉姆從伊頓百貨商店辭職,全家搬至維多利亞城經營「門羅書店」。雖然創業艱辛,但書店很快就步入了正軌,家庭的經濟狀況大為好轉。1966年,吉姆不顧門羅反對,購買了一個有五間臥室的大房子,門羅為此苦不堪言,因為這意味著她每天要花更多的時間做家務,更少的時間休息和寫作。她後來在一次訪談中說:「我太累太失望了,我不再關心書店的事,自顧不暇。吉姆沒有變,但是我改變了。」1968年,門羅終於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並在次年獲得加拿大文學最高獎「總督文學獎」,維多利亞小城的居民震驚地發現,他們身邊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婦居然是個隱藏作家。門羅的文學生涯漸入正軌,但她和吉姆之間的感情裂縫已無法修補。
1971到1972年期間,門羅反反覆復地經歷了幾次離家和歸家,過程很痛苦,因為門羅很難把年幼的孩子留下,就像《孩子留下》中所描述的那樣。分居期間門羅還在家附近租過一個小公寓,以便在早晨的寫作結束後還能趕回大房子照顧中午放學的孩子。但最終,1973年9月,門羅永遠地離開了維多利亞,留下了孩子,一個人踏上了返回安大略的旅途。故鄉的土地,成為作家門羅最渴望的情感避風港和取之不竭的創作源泉,她也從此走上了真正意義上的職業作家之路。

門羅,1979年。
重返安大略:
作家生涯的轉折點
門羅的傳記作者羅伯特·撒克將1974年門羅接受哈里·保羅的訪談視為其作家生涯的重要轉折點。首先,她從英屬哥倫比亞省回到了故土安大略省,從此再沒有離開。其次,門羅的第二任丈夫,也是曾經的校友傑瑞德·富蘭克林聽到了這次訪談,重新聯繫上了她,門羅因而離家更近了一步:回歸休倫縣。最後,麥克米倫出版公司的道格拉斯·吉布森也聽到了訪談,開始熱忱地跟隨作家門羅,門羅下一階段的文學生涯隨之開花結果。門羅曾經創作過《家鄉的那些地兒》(未出版),後來她將大部分內容改寫進了《你以為你是誰?》。在這部短篇集中,門羅幾乎完全以本人的人生故事線,即女性藝術家的成長為主線,記錄了小鎮女孩蘿絲從離家求學、結婚生子,到再次走出家庭,重回故鄉,最終成為經濟獨立、事業有成的新女性的全過程。
1974年,門羅的第三部短篇小說集《我一直想對你說的事》出版,獲崔林文學獎,同年出版了美國精裝版。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加拿大文壇有了「三個瑪格麗特」的戲言:即勞倫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瑪格麗特和並不姓瑪格麗特的艾麗絲·門羅。

門羅(左)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2005年。
1976年,門羅和吉姆正式離婚,門羅與傑瑞德·弗蘭姆林結婚,吉姆同年再婚。1978年《你以為你是誰?》出版,門羅二度獲加拿大總督文學獎;美國版與英國版也隨即出版,併入選當年布克獎短名單。1977年門羅獲得了加拿大-澳大利亞聯合文學大獎,第一次遠赴澳大利亞訪問。1981年門羅隨加拿大作家代表團出訪中國,並在廣州度過了自己50歲的生日。1982年《木星的月亮》出版,同年《乞女》的挪威語譯本出版,門羅出訪挪威、丹麥與瑞典。同年首次門羅研討會也在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召開。1986年《愛的進程》出版,門羅第三次獲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門羅也成為瑪麗安·恩格爾文學獎的首位獲獎者。
此後門羅的寫作日臻成熟,基本以三年一本的速度穩定推出新作,同時也是《紐約客》以及各類文選集的常客,被評論界公認為當代世界最重要的短篇小說家,「我們這個時代的契科夫」這一評價更是廣為流傳。1990年,《我年輕時候的朋友》出版,獲加拿大崔林文學獎。1994年,《公開的秘密》出版,次年獲英國W.H.史密斯文學獎,同年9月,門羅再獲萊南基金會文學大獎。1998年,《好女人的愛》出版,獲加拿大吉勒文學獎與美國國家書評人大獎。2001年,《恨、友誼、追求、愛、婚姻》出版,獲歐·亨利短篇小說獎及瑞文學獎終身成就獎。2004年《紐約客》推出門羅特刊,同年《逃離》出版,獲吉勒文學獎。2005年,門羅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世界100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2006年,《城堡岩石上的風景》出版,這是一部介於回憶錄和短篇小說之間的作品,一度讓人猜想是否將是門羅的最後一本書。但2009年門羅再次出版《太多幸福》,獲吉勒文學獎提名,為了避免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競爭,門羅最終決定退出評選;同年門羅獲得曼氏布克國際文學獎。2012年,《美好生活》出版,次年獲崔林文學獎。
2013年10月,艾麗絲·門羅成為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的首位短篇小說家,首位加拿大作家,以及第13位女性作家。
2024年5月13日晚,艾麗絲·門羅病逝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霍普港的一家療養院中,享年92歲。她在家鄉寫作,也最終逝於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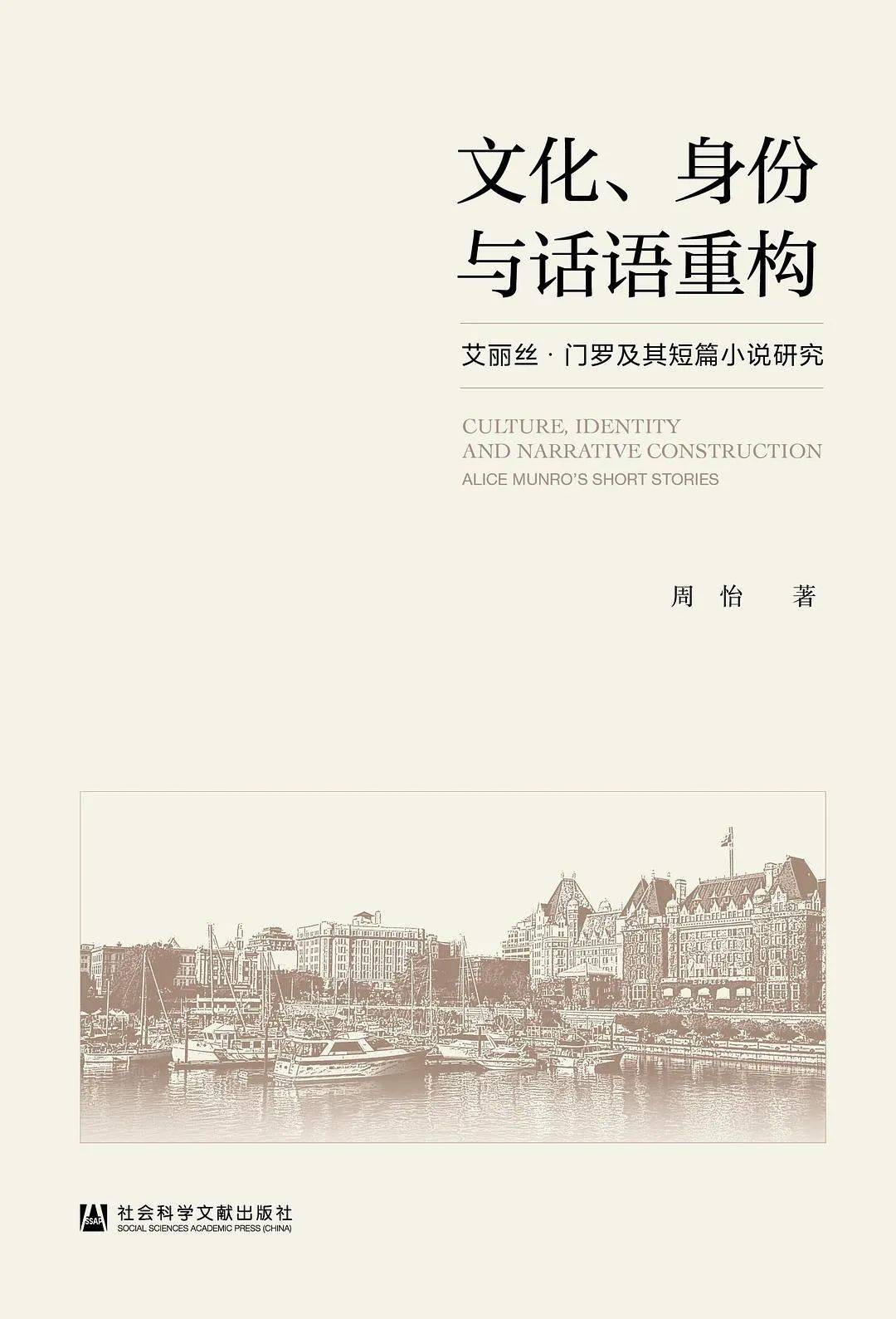
《文化、身份與話語重構:艾麗絲·門羅及其短篇小說研究》,作者:周怡,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2年2月
遊走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
無論門羅的作品多麼接近自傳與回憶錄,門羅始終強調,一如她在《岩石城堡上的風景》前言中所寫:「這些是故事。你可以說這些故事比通常的虛構性作品更加關注生活的真相。但別真以為它們是真的。」真實,在門羅的作品中,並不拘泥於歷史記錄上的真實,而更看重人心感覺上的真實。門羅在《信使》中如此寫道:「現在所有這些我所記錄下的名字,都在我心中和那些活著的鄉親們一樣真實,那些消失的廚房,那些寬敞的大黑爐子上擦得光亮的金屬裝飾板,那些從來都沒有真正晾乾過的酸木濾水板,那些煤油燈發出的暈黃的光。」
而在門羅最後的一部短篇小說集《美好生活》中,最後的四個故事被合成一組。門羅在序言「終曲」寫道:「這本書的最後四個故事並不完全是故事。它們構成了一個獨立的單元,感覺上是自傳性的,但有時候,實際並不完全是。我覺得關於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說的都在那些故事裡,從最初到最後,直到心靈的最深處。」

門羅。
尤其在最後一個故事,也是小說集的同名故事《美好生活》中,門羅似乎是總結性地,密集地重訪了自己的眾多經典:《皇家暴打》中那種既不屬於城鎮亦不屬於鄉村的身份尷尬,《特權》里騷亂的小學和污穢的廁所記憶,《沃克兄弟的牛仔》中父親與母親之間價值觀的差異與摩擦,《男孩與女孩》里女孩對女性空間和男性空間的第一次認識和挑戰,《烏特勒克停戰協議》中母親的帕金森綜合症和全家持久的羞恥感……最後,在這個雜糅了回憶與想像的故事中,類似《你以為你是誰?》中的小鎮怪人奈特菲爾德夫人突然入侵了艾麗絲的家園。當她粗魯地試圖破門而入時,母親拼著命地、緊緊地抱著才幾個月大的女嬰艾麗絲,躲在房間的隱蔽角落,害怕地不敢呼吸。事實上,故事的標題「美好生活」(dear life)是一個雙關語,在故事中的出處是「拼著命」(for dear life),可是門羅在標題中巧妙地省略了一個介詞,使得整個詞語的意義發生了完全的逆轉。
這些熟悉而又溫暖的記憶碎片,散落在門羅無數的故事中,事實、回憶、想像與感覺全都融合為了一體,通過虛構性的變形和再創作,與作家其他的作品相互重合、補充,彼此交相輝映,構建了一種亦此亦彼的開放性,也承載著人類經驗的流動、不完整、變幻無常和「未知」。最後借用英國著名作家A.S.拜厄特對門羅的評價:
「即便是在她寫作生涯的最初階段,她幾乎也沒有寫過傳統的那種『結構結實』的小說。她的故事是片段性的,時空顛倒的,啟示性的,但是它們通常能在很短的篇幅中表達出一種整體性,一種完整的生命體驗,並指明背後所蘊含的哲理。」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周怡;編輯:張進;校對:柳寶慶。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周刊》2023合訂本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