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緬懷

陳先達(1930.12—2024.10)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教育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哲學學部召集人,教育部哲學領域「101計劃」專家組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陳先達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24年10月10日5時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陳先達,1930年12月生,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會名譽會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市哲學學會會長、第三屆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哲學組組長,1991年獲政府特殊津貼。著有《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被肢解的馬克思》《問題中的哲學》《處在夾縫中的哲學》《哲學與文化》等,著作及論文曾獲「五個一工程」獎、教育部優秀著作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特等獎、吳玉章著作獎等。2015年出版《陳先達文集》14卷,2016年獲第五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近年來,出版《偉大的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十五講》《歷史唯物主義與中國道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必修課》《一位「85」後的馬克思主義觀》 《哲學與社會——老年沉思錄》等。
今天小編和大家一起重讀陳先達先生的著作,共致哀思!
《哲學與社會》
自 序
陳先達
人在不同年齡階段會有不同的體驗。老人體驗到的問題,是年輕人難以理解的。我讀過《康德書信選》,甚感人到老年會有一種青年人無法體會的難以訴說的無奈。他在1798年9月21日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我的身體還算得上健康,但動起腦子來卻像是一個殘疾人。在一切涉及到哲學整體(無論是在目的方面,還是在方法方面)的事情上,我再也不能有所進展,永遠看不到它們的完成了。」康德晚年在信中常常訴苦,說時光不再,精力衰退。偉大哲人尚且如此,何況我等凡人呢。
尤其是老年多病,到了在墳墓邊徘徊的時期,更容易傷感。我很佩服日本的哲學家中江兆民,在患喉癌被宣布只能活半年時仍然寫了《一年有半》。書中只偶爾提到自己的病,主要是談政治,評論日本人物。到期未死,又接著寫了《續一年有半》,其中談哲學,談唯物主義,談無神論,批判唯心主義和有神論。中江並沒有因為臨近死亡而相信來世和天堂。照我們現在的哲學水平來說,中江的這本哲學書當然算不上什麼傑作,但他那種面對死亡仍然靜心寫作的精神值得我們敬仰。將軍解甲不談兵,人到死時盡信佛。相比之下,中江的精神值得讚揚。死,是對人的信仰和世界觀人生觀最具實踐性的驗證。
我已高壽,完全可以徹底休息,何況我於2019年3月退休。我完全可以習慣退休後的生活,因為我本來就不是個愛熱鬧的人。但我很難停止思考。我寫過一些文章,出過一些書,我並不滿意。這不是矯情,而是因為我知道其中並沒有我自己的思想。誇張點說,我們大多數作者都是「小偷」,是盜竊別人的思想。我們的文章只能說是讀後感,是對前人或經典思想的反嚼。真正的思想是原創性的,應該是言前人之未言。這種文章我一篇也沒有。
我經常提醒自己:我是屬於書生式的知識分子。除了讀過幾本書外,對社會了解太少,也無實踐經驗。這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來說是個致命傷。對人類歷史無知,卻大談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從未跨出過國門一步而又大談全球化問題;從未擔任過任何一個實際職務,甚至連小組長都未榮任過,卻大談如何治國理政;對社會實際問題,對社會兩極分化的實際狀況毫無認識,卻只是從應然和實然的抽象概念出發去爭論什麼是公平正義。紙上談兵的趙括總算讀過不少兵書,而我們比起趙括還遜一籌。我們寫自己不懂的東西,以為文章無非是寫出來的,實則不然。腦子裡空空,文章必然是空空。以空對空,必然是空洞無物。從血管里流淌出的是血,從水管里流出的是水。寫文章並不容易。文章乃經國之大事,一篇好文章可以振聾發聵,起生命於白骨。這不是寫作技巧問題,而是真正把握了時代脈搏,切中腠理。馬克思說過,真理是不能謙遜的,不能瞻前顧後。寫文章也要有膽有識、有文采、有風格,這實在不易,但基礎是實踐經驗。沒有實踐經驗,一切都無從談起。
人的一生,年年有出生日,壽數就是生日數。生日如何過,也是人生遭遇的一部分。就我自己而言,外出上學工作從來沒有想到過生日。對我來說,生日只是個平常日子而已。不過,我也有過隆重慶賀生日的時刻。那是我十五歲生日,我家為我舉行了一次特別的生日儀式,請和尚道士為我打了一堂生日還願醮,讓上天保佑我平平安安,一連弄了三天。父母確實是誠心誠意為兒子求上天保佑,不知上天聽懂了這些人間的花言巧語沒有。
我也有以特殊方式過生日的時候。第一次,在1969年12月30日,是在去江西幹校的火車上過的,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天是我的生日。革命年代,誰還會想到生日不生日呢。火車到劉家站,我們下車。
開始,我們有些人集體住在一個破爛的戲台上。後來陸續來人,開始分連,我分屬五連,屬於種菜班,由出版社、幼兒園等單位組成。一住就是三年,生日早丟到爪哇國去了。
第二次,1977年12月29日,是在體育館批判梁效寫作組的萬人大會上過的。雖非正日,只差一天。在批鬥會過生日,值得記一下。我一生還從沒有過這種生日。我們這群人,大概二十多個吧,排隊,低頭,魚貫而入,接受批判。誰發言,說了些什麼,我一點也沒有記住,有點麻木不仁。心不在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確實如此。改革開放以後交上好運,生日過得比較好。兒女們祝賀不必說,八十歲時學生也來祝壽,熱熱鬧鬧。楊耕大力支援,博士生熱情籌備。八十歲生日,學院舉辦,紀校長出席講話,袁貴仁以部長名義發來賀信。還來了不少同行學者,煞是熱鬧。
九十歲的生日,悄無聲息。因為疫情的原因,一切都停擺了。之所以記下這筆,因為它反映的不僅是我個人的遭遇,也是我們社會發展的實際。我的生日小事一樁,但它卻是我此生經歷中值得記錄的,因為在去幹校火車上和在被批鬥中過生日,與學生祝壽、喜氣洋洋中過生日終究不一樣。
天氣可以變化,人的命運也不是一次就能定論。三起三落,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偉人如此,普通人也可能有大災小難坎坷不平的際遇。沒有自己的親身體驗,不能體會到過生日這種純屬個人生活小事,也可以反映時代的變化。這可能是我此生最後一本書,伸出這個小小無關緊要的分岔,作為結語,以作此生的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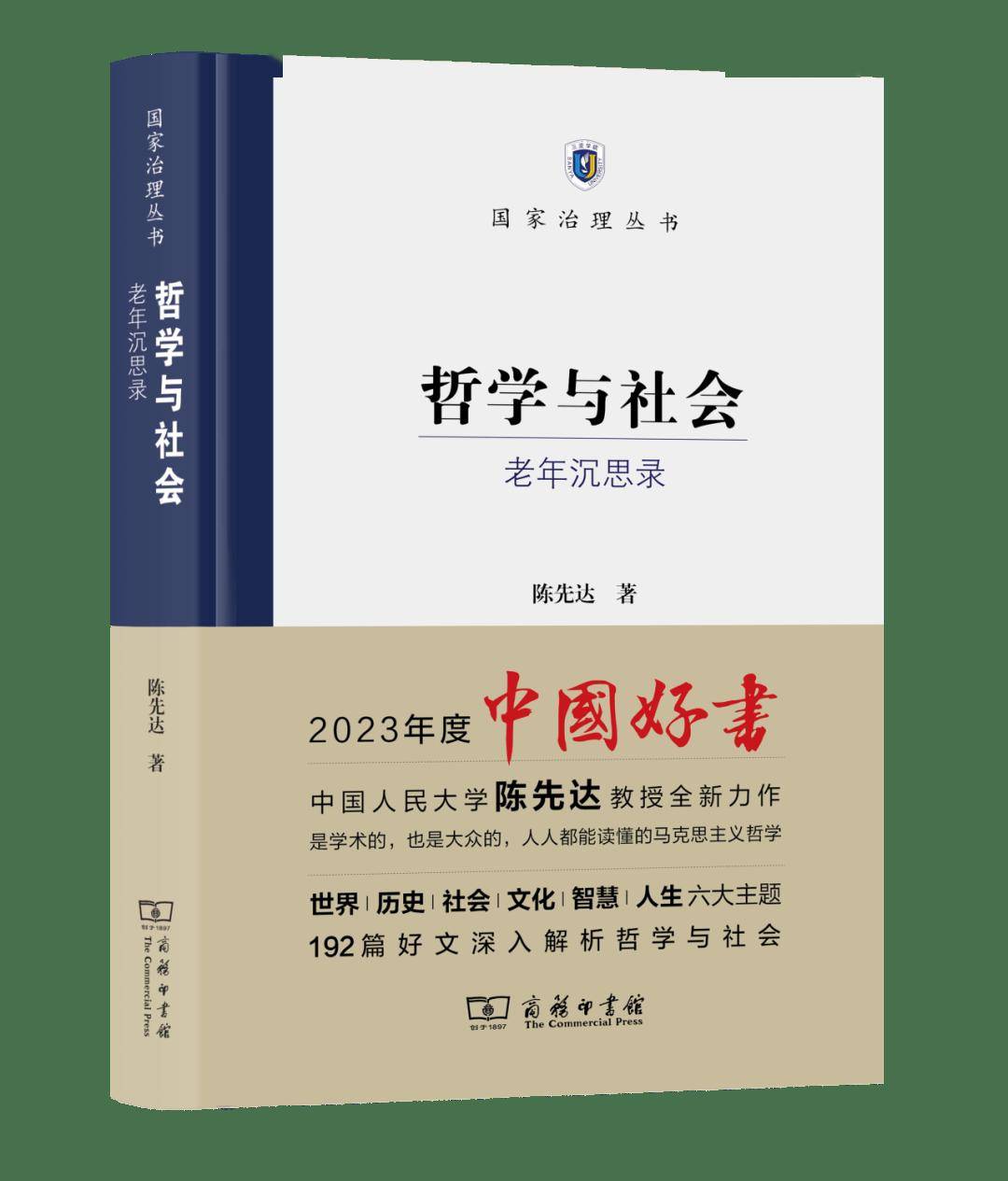
《哲學與社會——老年沉思錄》入選!13本「中國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