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一條獨家原創視頻

90後陳直,
曾是一名流水線上的農民工,
2021年,因為閱讀和翻譯哲學著作在網上「走紅」,
被稱為「工廠里的海德格爾」。
他的故事一度引髮網友的熱議:
農民工有沒有資格讀哲學?
這是不是一種逃避?
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評,
說他只顧自己,沒有擔負起養家的責任。
當代著名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
則對陳直的故事很感興趣,
稱他是「在中國的一個奇蹟」。
之後,陳直離開了流水線,
在石家莊的一所學校里獲得了一份辦公室工作。
他更加投身於哲學,
試圖釐清所有人都會困惑的問題:
人的本質是什麼?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今年5月,他翻譯的《海德格爾導論》出版,
一條在石家莊拜訪了他,
聊了聊離開工廠的三年後,
他在生活和思想上的變化。
編輯:魯雨涵
責編:倪楚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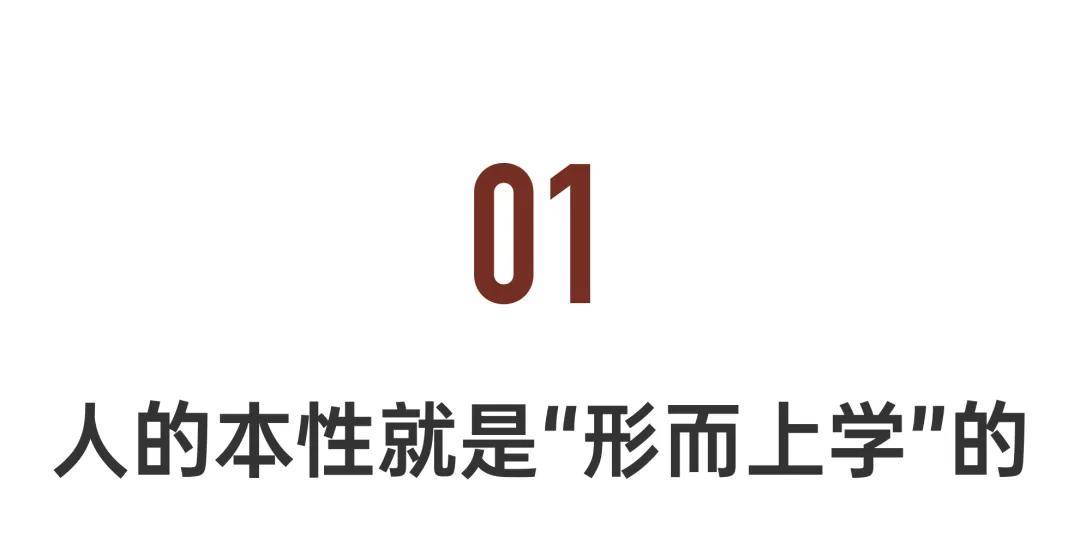

陳直很少接受視頻採訪
作為「讀海德格爾的農民工」受到關注,陳直的內心是矛盾的。
他感激自己的譯文因此得以出版,同時意識到自己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景觀」。
中國已經不缺勞動人民追求文學和藝術的勵志故事,但是投身於哲學的案例不多。媒體和大眾試圖窺探他的原生家庭、夫妻關係和工作收入,甚至將這件事看作階層固化之下、追求精神勝利法的結果。
陳直對這些視角的討論沒有很大的興趣:「雖然我的社會身份強烈引發了人們的獵奇心理,但是我自身並不從這些角度來閱讀哲學。」
他引用海德格爾的話:「形上學(哲學)屬於人的本性,……只要人活著,人就以某種方式進行哲思。」
「但不思考也是正常的,就像海德格爾經常說的,存在是自行遮蔽的,」陳直頓了一下,「很多人都遺忘了自己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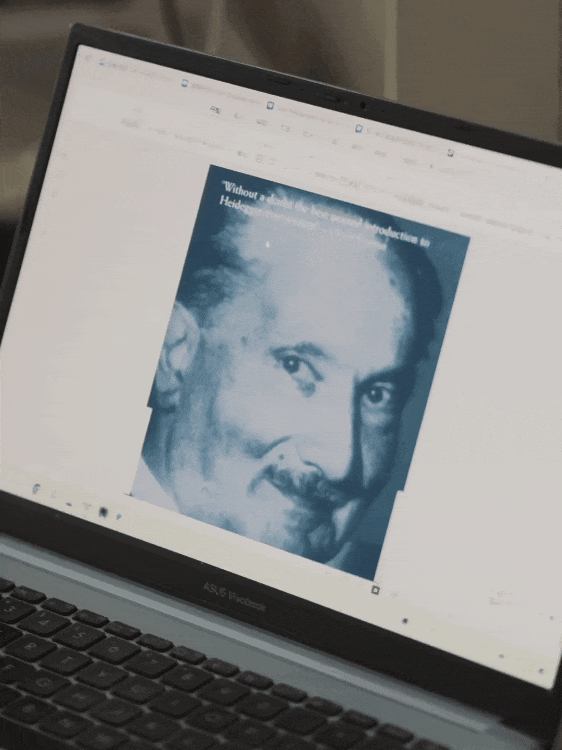
陳直和《海德格爾導論》
陳直在10歲左右第一次產生了某種哲學性的困惑。
亞里士多德說「哲學起源於驚奇」,大多是有閒階層在茶餘飯後的某些驚奇,比如驚奇為什麼鳥會飛。而陳直的「驚奇」更多是來自於焦慮、不安、惶恐。「我在想,如果生命或者活著對我來說是那麼的殘酷與無情,那麼死亡又意味著什麼,生命又意味著什麼?」
到了18歲,他的困惑越來越多,「我們的意識的本質是什麼,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情緒,這些東西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他短暫地上過一個二本學校,學的是數學,自然科學並不能解決他的困惑。他又想從心理學裡尋找答案,了解到心理學是從哲學中獨立出來的學科,最後才摸索進了哲學的世界。
最後,他因為沉迷哲學,被學校勸退。父母不讓他回老家,於是他只能出去打工,浙江、江蘇、北京、廣東、福建。作為「農民工」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廈門一家做手機攝像頭的工廠,負責維修組立機。
2021年8月,因為想出版自己翻譯的《海德格爾導論》,陳直在網上發帖求助,意外引起了媒體的關注。
最務實主義的社會身份,和公認的「無用之學」,巨大的反差引起了人們激烈的討論:「農民工能不能讀哲學?」「農民工有沒有資格讀哲學?」「農民工該不該讀哲學?」
陳直也會介意「農民工」的稱呼,但比起這個身份本身,他更想擺脫社會對農民工的普遍歧視和誤解。他也忐忑這種歧視會牽連到他的譯本,把這本書貶得一文不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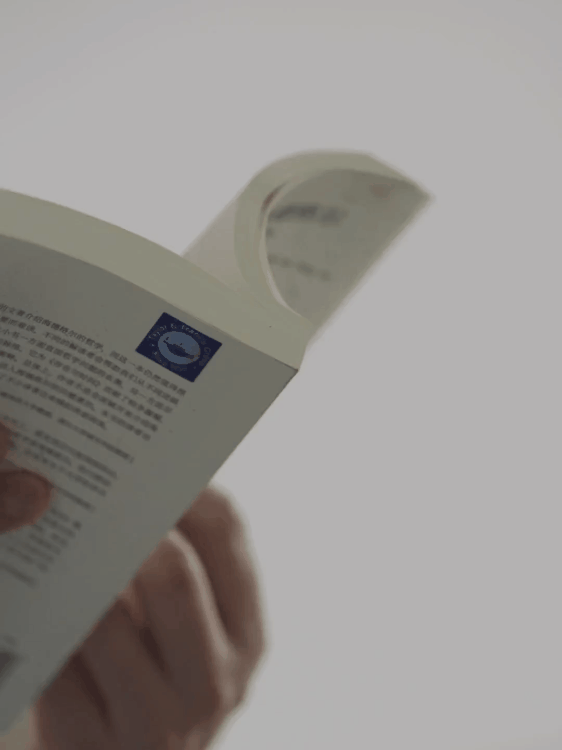
拿到譯本後,陳直反覆看了好幾次
今年5月, 陳直翻譯的《海德格爾導論》終於出版,期間經歷了好幾次的校對。拿到實體書後,陳直又反覆看了幾次,挑出了一些小錯誤,「但是總體上來說,還行吧。」
當代著名的哲學家齊澤克也參與了這場討論。 他說:「我們應該慶祝像陳直這樣的奇蹟——他們證明了哲學不僅僅是一門學科,哲學可以突然中斷我們日常生活的進程,讓我們產生困惑。」
這番話給了陳直很大的力量,讓他覺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對的」。
因此在某些「情調」之中,陳直非常樂意作為一個「讀哲學的農民工」而被人們所認識。
他想,人們或許可以從他的這種「現象」中意識到,一切社會身份,包括財富、權力、地位等等,和「人的本質」沒有任何關係。農民工、大老闆和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距離「人的本質」是平等的。
「我有時甚至會覺得,比起一些所謂的上層階層或者中產階層,無產階級可能可以更加呈現和綻開出人的本質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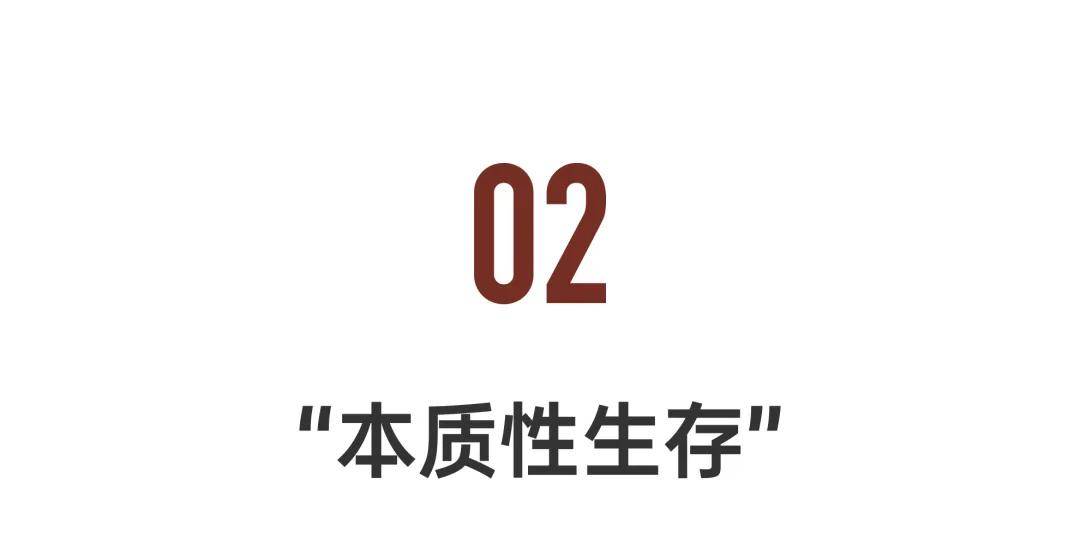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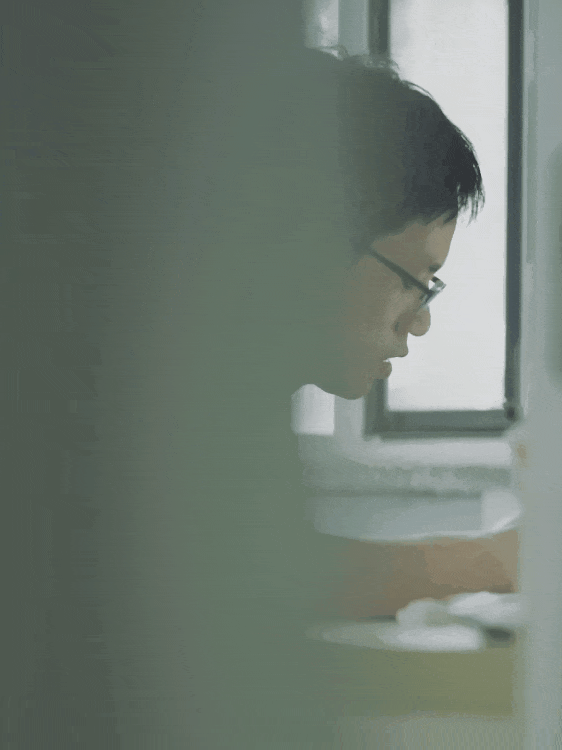
「出名」之前的十多年間,陳直在製造業的生產線上工作,包括快遞物流企業,印刷廠,以及人們很熟悉的富士康。
工廠做六休一,從早上8點干到晚上8點,甚至更長時間,「腦袋裡什麼都想不了」。陳直自認有「幽閉恐懼症」,被困在封閉、嘈雜的工廠和擁擠、骯髒的集體宿舍非常難熬。
他只能在生活的縫隙里閱讀哲學。在北京打工的時候,他住在通州租的六七平米的地下室,只放得下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他在這裡讀完了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在深圳富士康時,他每天要裝800個ipad螢幕,下了班就去旁邊的街道圖書館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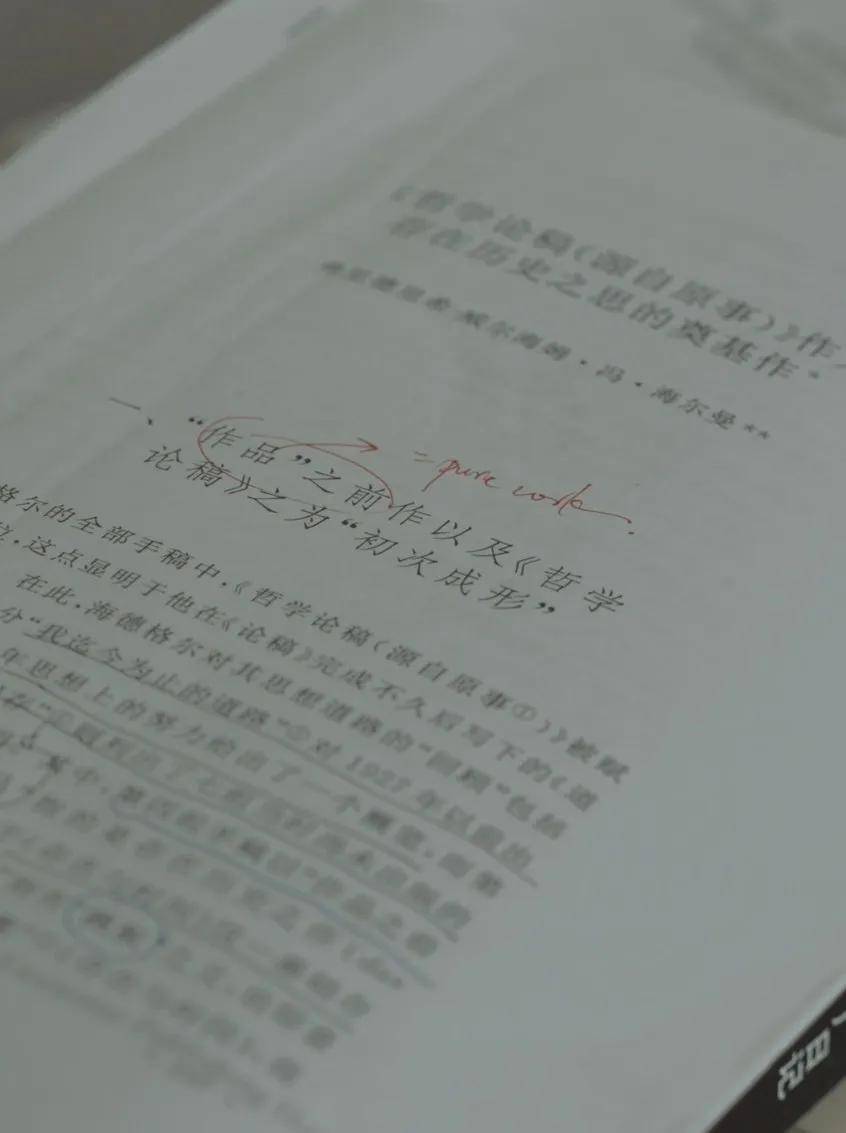
陳直列印了很多哲學論文進行研讀
為了翻譯《海德格爾導論》,陳直每星期請一天假,這意味著每個月會損失將近1000塊的收入。兩百頁左右的《海德格爾導論》,斷斷續續花了四個月才完成初譯。
陳直形容自己長期處於一種「非常非常壓抑」的狀態之中,「比如賺不到錢,讀不懂哲學,甚至在說話時開始有點結巴。」他很難長期待在一個工作場所,一個地方最多只能幹半年,就會或主動或被動地離開。
第一家媒體找上門的時候,他正處於工作變換期間的焦慮中,「坦白說,我當時很絕望,因為繼續找工作也會面臨同樣的境況,但是也沒有多少辦法。」
報道「爆」了,「工廠里的海德格爾」火了。河北一家職業學院的領導聯繫到陳直,願意給他提供一個文職工作,在雜誌編輯室擔任編輯和排版員。
他的新辦公室寬敞又明亮,有空調和暖氣,教職工食堂的自助餐只要五塊錢。學校提供的宿舍是兩室一廳,一間是帶陽台的臥室,另一間是陳直閱讀和寫作的空間。有時他也會睡在這裡,方便睡不著的時候隨時起來寫些什麼。

學校食堂

學校圖書館
學校嚴格遵守勞動法,陳直因此有了更多時間投入哲學,解決思想方面的種種困惑。
2023年11月,他自感獲得了初步的「頓悟」,即「本質性生存」。
這個概念是他從海德格爾的思想中延伸出來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根據人的更加深層的、更加核心的「本質」來生存。
與之相對的是身體性生活(物質性生活)和社會性生活(情感、友誼、一般社會性交際等)。
「本質性生存」,就是克服「身體性的生物本能」,逃離「社會性的工作生活」,為「人的本質」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落到現實生活里,陳直認為「本質性生存」和極簡主義、甚至苦行主義的生活方式比較相近。「作為普通人,我們依然可以在完成事務性工作後,進行某種意義的『本質性生活』,而不是在工作之外就去搞吃喝玩樂這些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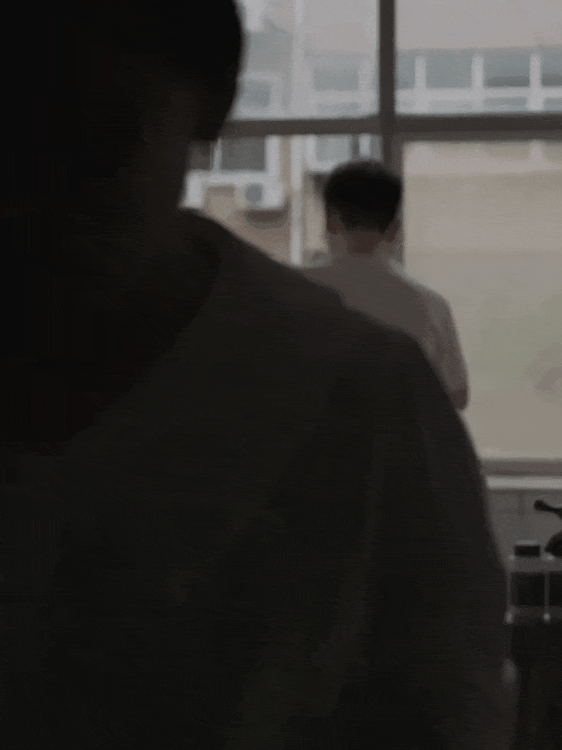
晚餐經常是煮方便麵
從去年12月開始,他嘗試進行了一種苦行的計劃,嚴格限制身體性感官的誘惑——比如吃從感官上「好吃」的食物,喝感官上「好喝」的東西。不過並沒有成功。
他也覺得應該儘可能地減少睡眠時間,「我認同一些佛教的理論,如果我們要覺悟的話,就要一直處在有意識的狀態之中。」
「幸福」和「快樂」這樣積極意義的情感,也不是他的目標。「我說我很高興這本書能得到出版,我是想了很久的,要不要加上很高興這兩個字。但是一般大家都會加,所以我就加上了。」
悟出「本質性生存」的時候,是他最近幾年少有稱得上是「喜悅」的時刻。他因此開始頻繁寫作,急切地想對此進行更多的闡釋和說明。

陳直很少去超市,習慣在網上買菜和日常用品
陳直的身邊很少有願意和他聊哲學的人,他並不介意。海德格爾說,人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的。
網絡給了他更大的分享空間,他幾乎每兩天就會在豆瓣上更新一篇長文,記錄自己的生活和哲思,大部分文章都沒有網友評論。他還重新開始接受採訪,一方面是為了新書宣傳,更重要的是表達自己對「本質性生存」的看法。
「但是在接受幾個媒體採訪後,我覺得也沒什麼意思。沒有多少人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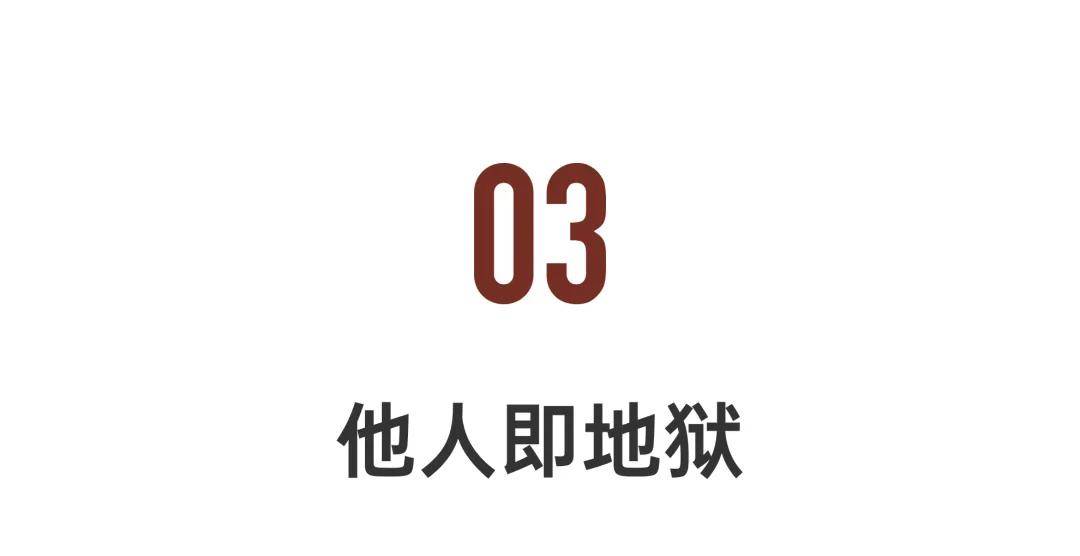

陳直和妻子小賴
陳直自認是一個「鬥爭的失敗者」。
在他的老家江西農村,大多數人二十歲就結婚了,他到三十歲才接受家裡安排的相親,以此表達對世俗之事的「拒絕」。甚至稱不上是「鬥爭」,但已經是他能做出的最大努力。
妻子小賴比他小兩歲,是一個溫吞、傳統的女人,在石家莊做一份電話客服的工作。上班的日子裡,她早上7點就要出門,騎一輛電動車去市區。工作強度大加上北方氣候乾燥,她的嗓子一直是啞的。

剛結婚的時候,小賴也覺得陳直只是一個「在農村裡待著、沒有賺錢能力的老實人」。陳直對她說,我可能比你所看到的更為不同,甚至可能比你所看到的更加「厲害」,她不以為然。
她慢慢見識到了陳直的「厲害」。她對「哲學」沒有概念,但英語是一種值得崇拜的「能力」。媒體爭相拜訪,陳直的名字被印在了書的封面上,因此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大幅改善了家庭的生活條件,這些都讓小賴感到驚訝、甚至不可思議。
如果之前她認為「搞哲學」是不務正業的話,現在她會認為陳直的確「在做事」,儘量不打擾他,比如在刷短視頻的時候戴上耳機。

小賴下班晚,陳直會承擔家務
第一篇報道發出後,陳直收到過不少網友的批評,說他「沒用」,「不負責任」,「只想著自己的事情」等等。
他確實盡到了作為兒子和丈夫的基礎職責。按母親的意願結婚生子,成為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給留守老家的兒子寄錢和買東西,也會負責做飯和承擔家務勞動……
陳直認為自己要儘量克服很多的物慾,但他會滿足小賴的要求。今年三月,兩個人難得同時有假期,小賴讓陳直帶自己去了濟南。我們拜訪的時候,陳直即將受邀去杭州參加新書分享會,小賴也請了三天假一起去,她難以掩飾對這次旅行的期待。
對於很多人喜歡的「旅遊」,陳直持懷疑態度。「就地球這樣的小地方,沒有必要這樣去折騰。」他更信仰康德所說的「頭上的星空」,比起在地球這個地方到處「旅遊」,「星空」對我們來說更有意義。
而小賴和大部分人的想法一樣,如果有條件,可以「環遊世界,體驗這世間的美好。」

陳直吃面,小賴吃飯,偶爾聊聊各自的一天
兩人很難達到靈魂的共鳴,但是家庭關係是很和諧的,「我們幾乎沒有什麼爭吵的地方,當然可能這主要是她對我的寬容。」陳直也意識到,如果不是當前的經濟狀況相對過得去的話,或許無法維持這種體面。
「坦白說,我不太會和人打交道。這個人,包括我的孩子,甚至包括我妻子。」薩特說,他人即地獄,陳直深有體會。
陳直不主動提自己的父親,我們從以前的採訪中知道,他的父親有「暴力傾向」,不僅是肢體暴力,也體現在言辭上,心情不好就會破口大罵。他曾在某次採訪里說:「我對他的感情並不複雜,那就是沒有感情。」
他的老家很貧困,讀小學的時候,他常常會欠學雜費。「有一次,早上』升國旗』後,校長在全校人面前通知我的學費還未交,讓我儘快催促我家長交錢。」這讓陳直感到羞辱。
在他「比較黑暗」的童年裡,只有和母親共同度過的時光是「比較快樂」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很難對母親的困境視若無睹。
結婚的時候,陳直借錢買了一輛車,幾萬塊錢。因為村裡所有人結婚都會買車,儘管這對在外地工作的他來說毫無意義。「主要是考慮到我媽的感受,她在那種環境中,處境非常艱難。」
陳直並沒有把自己的事情告訴母親,包括他讀哲學、翻譯、出書和接受採訪。這對大多數人來說已經是一種「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本可以成為母親在老家炫耀的資本。他覺得這種無止盡的攀比沒必要,「我想在她面前展示一個比較通常(普通)的人。」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寫道:「我實在是厭惡社會中各種意義的相互鬥爭,我想要的是』自我鬥爭』……我要克服自己的無明,讓自己『覺醒』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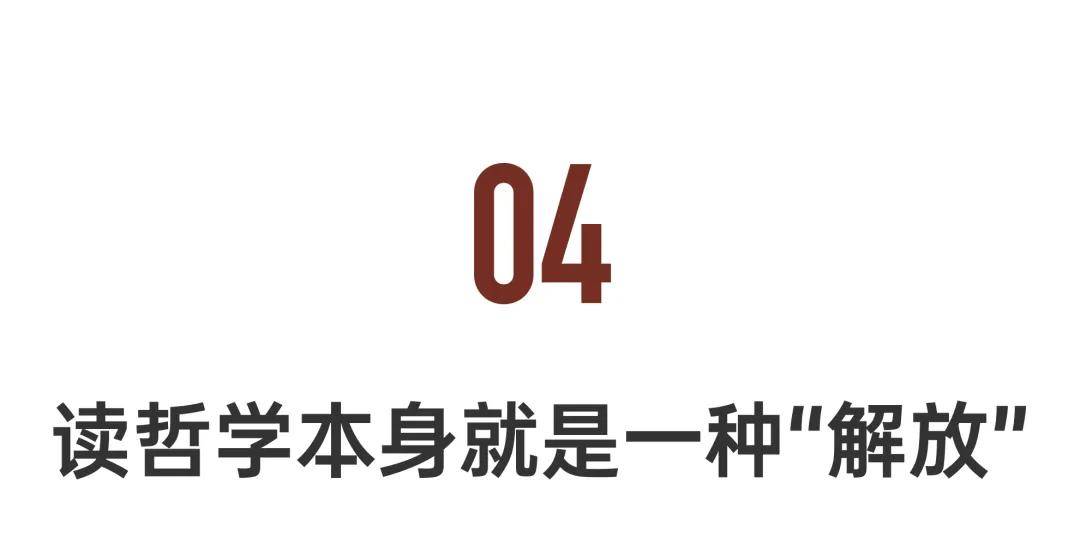

陳直經常一個人去公園
如果用一種積極的意義來使用「孤獨」這個詞,陳直是孤獨的。
他相信,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他避免和人發生這樣那樣的關係。他喜歡「植物比較多的場所」,比如森林和植物園。在石家莊,他最喜歡的是家附近一處沿河的小公園。
在這裡,和他糾纏的日常事務被「清除」或「懸置」了出去,更加「內在」、「深層」、「本質」的東西呈現出來。
於他而言,這裡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林中空地」,「萬物在之中顯現自身,敞明自身」。
但是在生活的大多數時候,他感受到的是悲傷,「和我的現實生存有很大的關係。很多事情沒有能力解決,沒有辦法解決,想到還有很多這樣的事情,我就感到一種悲傷的情緒。」
例如,小賴想和兒子一起生活,而陳直非常樂意兒子留在老家和母親一起生活,他自認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父親,擔心兒子受到自己不好的影響。
再例如,孩子常常生病,這讓他母親手足無措,陳直在去年夏天回去了一趟,帶著孩子去醫院檢查,有醫保的情況下花了接近1000元,「讓我感到很驚訝和難以承受,不過我不得不承受。」
我們問他:「你當下的矛盾就是這些問題是實際存在的,你需要去解決,但是你主觀上並不在乎嗎?」
他說:「我不太同意你說的主觀這個詞,應該說從原則上,我不是很想在意這些問題。一方面我確實缺乏這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我覺得如果整天去想這樣的事情的話,可能也沒有太多真正的意義和價值。」

家裡除了柴米油鹽,就是成摞的哲學書
哲學多少能消解一些他的焦慮。「對社會性的事物,我無能為力。既然如此,我就想想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主要讀一些個體主義的哲學家,海德格爾、克爾凱郭爾、薩特。
他一直對克爾凱郭爾說的「我要找到我可以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真理」這句話印象深刻。「之前我不知道我的主觀真理到底是什麼,現在我認為我已經找到了。」
他從不假設自己很有錢,實現所謂的「本質性生存」,本身就不需要太多錢。比如他關注的豆瓣「FIRE生活(窮版)」小組,人們試圖在沒錢的條件下,進行無更多「社會性生活」的生存方式,沒有「工作煩惱」的生活方式。
好在當下,陳直還處在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之中,這讓他有更多的時間來完成「更重要的事情」。
他對科技的發展是非常期待的。未來有一天,所有人都可以不用被迫去工作,就能夠獲得至少基本的生活保障。所有人都能把更多時間和情感放在自己所認可的事情上。

陳直無數次被問到,對哲學的投入,是不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逃避是一個比較負面或者比較否定性的詞彙,我選擇的詞是克服或者超越。」
在社會性哲學家看來,一位流水線工人的解藥(antidote)絕對不會是海德格爾,他們需要做的是改變自己悲慘的工作條件。
而陳直更認可齊澤克的觀點:讀哲學本身就是一種「解放」,是無產階級的解放。
他和我們朗讀齊澤克的語句:「今天,我們應該說:讓一百個陳直研究哲學——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擺脫我們不幸困境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