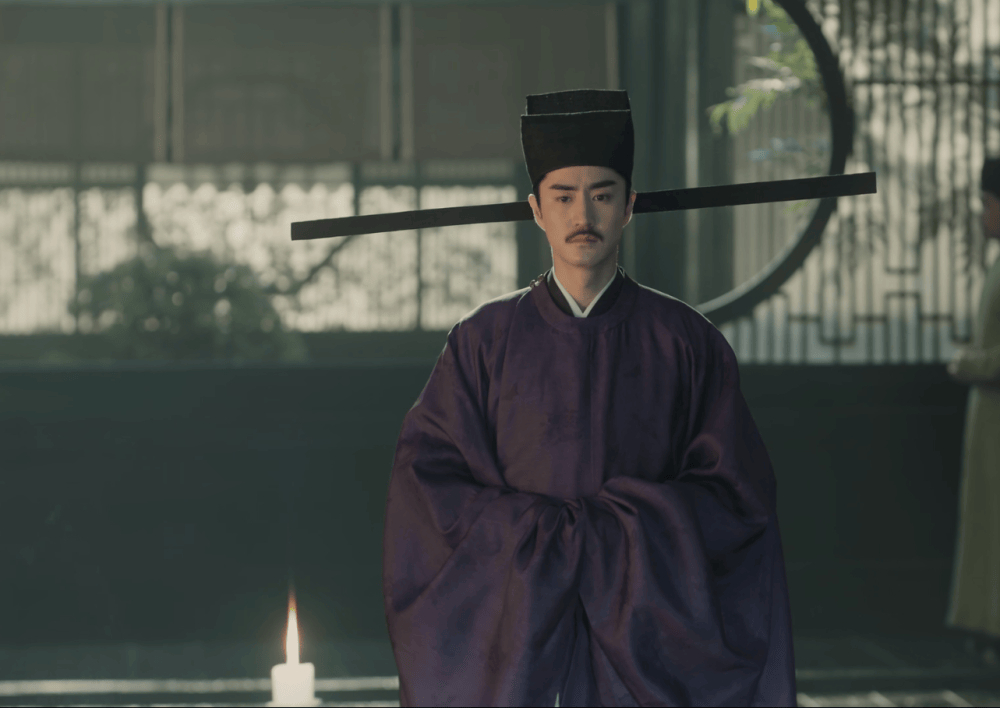
北宋在西北沿邊徵發內屬的党項、吐蕃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並依據族帳規模、所立戰功授予部落酋長各級軍職、武階,由其繼續統領本族丁壯作戰。這類普遍保留原有部落組織的蕃族軍隊就是在北宋中後期躋身四大兵種之列的「蕃兵」,獲授宋朝官職的部落酋長則被稱為「蕃官」。憑藉自身的軍事技能和部落的人力資源,西北蕃官不僅成為宋神宗以降拓邊的重要力量,更在南宋政權重建的過程中建立殊勛,學界討論相對集中的劉延慶、劉光世、李顯忠等名將都出身於這類世襲部落酋長的蕃官家族。
然而較少有學者注意到,宋朝特別是北宋中後期還存在另外一類蕃裔將領。他們同樣出身蕃族,但與其出身部落的關係難稱緊密,甚至可能已經逐漸脫離部落、走上編戶化的道路;與世襲本族巡檢、長期統領部落的蕃官不同,他們往往任職於西北沿邊駐屯禁軍、諸路帥司,升遷路徑、任用方式均更接近漢人軍官。著眼於蕃將與部落間的互動關係,或可借用唐史學界的分析框架,將他們稱作寒族蕃將,而將統領部落者稱為部酋蕃將。
在熙河開邊中居功甚偉的王君萬、王贍父子是研究上述群體的典型案例。一方面,常被誤認為漢將的他們實際出身蕃族,儘管由於學術旨趣的差異而未遑論證,但寧夏大學的研究團隊已注意到王君萬、王贍父子出身蕃族,這種蕃族屬性淡化的面貌正是寒族蕃將的典型形象。另一方面,王君萬、王贍父子二人的《宋史》本傳與王贍堂弟王賑的新出墓誌分別提供了迄今僅見的寒族蕃將的官方傳記和自我陳說,史料價值極高。本文擬結合傳世史料與出土文獻,在釐清王贍家族北宋晚期事跡的基礎上,嘗試討論北宋中後期寒族蕃將的社會基礎、文化轉型、發展軌跡等問題。
一、王贍家族的蕃族背景、社會基礎與文化特徵
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王君萬、王贍父子的蕃族族屬再稍作說明。最直接的證據來自曾布,他在指責首相章惇以私書指揮邊將時,即以「如折可適、王贍輩,皆蕃夷之人,何可與書」為口實。府州折氏子弟折可適自然出身蕃族,與其並列的王贍當亦如此。元豐年間擔任侍御史知雜事的何正臣以「況君萬邊豪,豈不傾動其類」為由反對朝廷發還王君萬籍沒家產、升遷王贍職任,亦可作為王君萬族屬的旁證。一方面,晚唐世居蔚州的沙陀系粟特人康君立,北宋前期統領「蕃族七百餘帳」、從時代和姓氏看很可能是吐谷渾後裔的遼朝要人白萬德以及宋神宗時期的西夏武將李崇貴均被稱作「邊豪」,可見這一以邊地豪傑為本意的稱謂在唐宋之際常與蕃胡人群發生關聯。另一方面,何正臣對蕃裔武將似懷敵意,他在次年負責鞫訊兵敗瀘州的韓存寶,在輿論反對中直接促使這位「本西羌熟戶」的高級武將被宋神宗下詔誅殺,他口中的「邊豪」「其類」,可在王君萬蕃族出身的語境中理解。再如李復供職熙河路經略司時致信章惇,談及「王贍本邊人弓箭手之子」,亦應暗指王君萬父子的蕃族背景。
《宋史》本傳並未直接透露王君萬的族屬,而僅以「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交代他的出身,作為附傳存在的《王贍傳》亦徑稱「贍始因李憲以進」。王贍堂弟王賑的墓志銘中,則以並無特別族屬指涉的「山西之將家」「世為成紀人」為辭。所謂「山西將家」,典出《漢書·趙充國傳》「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宋人常用此來形容西北將門;成紀即秦州治所成紀縣,此處或以治所代稱秦州,或王君萬先世確曾在成紀縣境活動。志文不僅刻意迴避王贍家族的蕃族背景,亦未提及其他蕃將傳狀碑銘中常見的隨從作戰的部落族眾。如果沒有時人留下的零星議論,甚至無法確定他們的族屬。
有學者認為這是宋朝國史中蕃將傳記的普遍現象,反映了宋人對蕃將部族背景的淡化處理態度。但是兩宋著名蕃將的公私傳記實際上並不諱言他們的蕃族出身。就國史列傳而言,李繼周「祖計都,父孝順,皆為金明鎮使,繼周嗣掌本族」;劉光世祖父劉紹能「保安軍人,世為諸族巡檢」;李顯忠家族「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高永年「河東蕃官也」。從私家傳狀來看,劉光世《家傳》記其靖康勤王事,有「就刷世襲部內未籍余丁」之語,李顯忠《行狀》雖然緣飾「其先唐諸公子也,世遠譜不存」,但亦承認「由唐至五季,逮我國朝,世為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因此,王君萬父子國史傳記中對蕃族背景的淡化,不能完全歸結於歷史書寫或文獻亡佚等因素。
從前揭「部酋—寒族」的二分框架出發,北宋著名蕃將大多可歸類為部酋蕃將,他們出身部落首領家庭,世襲本族巡檢一類的職位,平時負責維持本部落的日常秩序,戰時則率領部落族眾參戰。儘管北宋中後期以降逐漸成為陝西諸路高級將帥甚至入朝主管中央禁軍,他們仍與部落存在密切聯繫。以兩宋之際的劉光世、李顯忠為例,前者不僅在靖康年間徵發族眾組建勤王軍,南渡後的親軍部曲亦名為「部落」,後者在倉促反金、逃離鄉里之前的軍事活動亦以蘇尾九族的本部人馬為骨幹。與此社會基礎密切相關,晚至兩宋之際,部酋蕃將在文化和交遊上仍或多或少保留蕃族色彩,如李顯忠曾祖母野氏、祖母折氏、母親拓跋氏,顯然其家族世代通婚蕃族;他本人亦「不喜文飾」「未嘗學書」,並在楊存中死後「殺名馬以祭」,這種儀式並非漢俗,而應有北族源流。
王君萬、王贍父子的家族形態和社會基礎則與部酋蕃將差異顯著。他們確實同樣生活在蕃漢雜居甚至蕃族更強盛的地區,其世居之寧遠寨直到天禧三年(1019)才設置於深入吐蕃部族勢力範圍的洛門谷西部,並在此後的30多年間一直是北宋西北疆界最西端的寨堡之一。不難想見,寧遠寨進築之初,周邊民眾多系蕃族。直到熙河開邊頗有成效的元豐年間,管轄寧遠寨的鞏州全境主客戶共計仍僅有4700餘戶,崇寧戶數亦不過4800餘戶;而在治平末年,僅寧遠一寨就有7480人被登錄在蕃兵簿籍之上,顯示當地蕃族人口至少數倍於此。這組數據說明,直到北宋晚期,寧遠寨周邊蕃族勢力似仍占主流。但是,與部酋蕃將不同,王贍家族已脫離部落生活,逐漸走向編戶化的道路。
李復對王贍「本邊人弓箭手之子」的譏嘲透露出王贍來自一個先世曾投充弓箭手的蕃族家庭。所謂弓箭手,是宋朝在陝西、河東緣邊通過授田免租的方式所招募的蕃漢邊民,平日耕地務農、戰時從軍上陣,是北宋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日常多以寨堡為單位屯耕,故其招募往往伴隨著寨堡的設置。王君萬之先世也許以寧遠寨進築為契機應募為弓箭手。王賑「曾祖永和,隱德不仕。祖彥福,贈率府率」,大概仍是寧遠寨控制下的基層弓箭手。王君萬亦曾「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殿侍是小使臣以下的無品武階,所謂「秦鳳指揮使」或即弓箭手指揮使,也許暗示他起家之初仍未脫離弓箭手這一民兵組織。「指揮使」或為「指使」之衍,則王君萬當時在秦鳳經略司聽差,是並無固定職任、等候臨時派遣的低級軍官。無論如何,王君萬父祖兩輩應已被納入宋朝國家治理體系,家族形態大概更接近內地編戶而非邊疆部落,其生計方式中定居農業的比重亦應有所上升。這種迥異於部酋蕃將的社會基礎與出身背景,使得王贍家族的漢化進程格外迅速。
享年56歲的王賑卒於宣和二年(1120),知其生於治平二年(1065),那他的堂兄王贍生年自然更早。由此估算,元豐三年(1080)去世的王君萬可能在宋仁宗統治下度過他的少年時代,其家族長輩當時大概應募寧遠寨弓箭手不久,或許仍延續著部分部落時代的生活方式。受此影響,王君萬身上帶有強烈蕃族色彩,王韶拓邊熙河,「獨別羌新羅結不從」,王君萬「詐為獵者逐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撾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蕃族首領的信任並一同出行狩獵,可見他不僅精通蕃語,而且在形容舉止、生活習俗、騎射技藝等層面均保留著蕃族風貌。隨著地位上升,王君萬不僅負責管理熙河路新附蕃部,還受命招納董氈、木征等河湟吐蕃領袖,這些職任安排亦應與其蕃族特質有關。
與父輩相比,王贍、王賑的漢化程度大為加深。一方面,作為蕃裔邊將,王贍仍然具備溝通、招納吐蕃部族的能力。元符元年(1098),其「結約兩處蕃部」預謀攻討青唐;又是河湟蕃部在聯絡北宋時的首選對象,曾得蕃書暗報西夏監軍仁多保忠「有歸漢意」,溪巴溫親信籛羅結在勸誘宋朝介入唃廝囉政權內鬥時亦面見王贍陳說利害。另一方面,與其父不同,王贍不以個人武勇知名,又未留下親自衝鋒斗將的記錄;更重要的是,他頗為傾慕漢文化,熱衷效仿文人儒士,與其共事熙河的李復甚至譏其「妄作士人舉止」。未深度介入河湟開邊的王賑的蕃族因素更加淡化,他固然了解「山川險阻,羌虜強弱」等軍旅知識,又頗擅騎乘,但總體而言給人留下的印象和漢人將門子弟並無顯著差異。石州文學王概回憶他與王賑十餘年的交往經歷,稱其「恭而有禮,樽俎之間,談笑溫溫,和氣可掬」,並以「惟樂賢友,行己恭遜,與人信厚」的美譽概括王賑的品格,甚至寫出幾分忠厚溫良的儒生氣質。寫作意圖的不同當然會影響敘事重心,國史列傳強調王君萬的邊將形象,友人所作的王賑墓誌則突出志主居鄉耆宿的身份,儘管如此,兩代人間的文化變遷仍頗醒目。
像王贍兄弟這樣高度漢化的北宋寒族蕃將並非孤例。「本西羌熟戶」的韓存寶「少負才勇,喜功名」,又長期統領正兵、弓箭手而未見直屬部落兵部曲,出身似不甚高。他雅好結交士人,僅從蘇軾、蘇轍文集中搜檢,就可發現其與巢谷、家安國兩位文士關係密切。巢谷、家安國均舉進士不第,他們與韓存寶的交往並非源於職務關係上的接觸,而多少與韓存寶對士人的傾慕有關。總之,從寒族蕃將脫離部落組織、長期供職正規軍系統等因素來看,他們確實較部酋蕃將更有迅速漢化的可能;而傳世文獻中北宋寒族蕃將相關史料的匱乏,或許正是他們高度漢化的反映:如果不是同時代人偶然留下的隻言片語,甚至無從判斷哪些西北將官出身蕃族。
二、《王博施墓誌》所見北宋晚期王贍家族的仕途起伏
王贍以攻滅青唐、拓邊湟鄯的壯舉與甫建殊勛、旋遭貶死的結局為學界熟知。前人對他的早期仕履、攻滅青唐的軍事行動與宋朝最終放棄湟鄯地區的決策過程等問題已有討論,更指出王贍之不得令終,與宋徽宗即位初期帝位不穩、舊黨勢力回潮的政治形勢有關。隨著徽宗親政後政治風向的逆轉,特別是河湟拓邊的重新展開及接連勝利,王贍及其族人再次得到褒賞。下文將從《王博施墓誌》出發,梳理王贍家族在王贍得到平反後的發展軌跡,進而說明其家族仕途起伏與朝堂政局的密切關係。
自宋神宗朝以降,是否贊同拓邊西北逐漸成為新舊兩黨政治分野的標誌之一,新黨傾向開邊,舊黨則多持反對立場。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後,宋朝一度試圖恢復「元祐之政」,遂放棄湟、鄯二州並追責拓邊臣僚。作為前一年攻入青唐的首功之臣,王贍迅速被樹為反面典型,次年三月在流放海南途中「縊死」。不過從王贍去世當年的建中靖國元年(1101)九月起,徽宗開始通過一系列政事昭示自己斥元祐、崇熙豐的政治取向,並以崇寧元年(1102)六七月間曾布罷職、蔡京入相為標誌,全面推翻調和黨爭的「建中」國策,走向繼承神宗事業的「崇寧」之路。蔡京上任後「日以興復熙寧、元豐、紹聖為事,於是侍御史錢遹言,乞除雪贍、厚罪名」,王贍終於迎來平反之日。他在當年即追復供備庫副使,次年六月王厚領兵收復湟州,王贍又追贈保寧(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其子王珏亦得授通事舍人。
新見《王博施墓誌》透露,宋朝對王贍家族的恩賞並未就此止步。《墓誌》稱王博施:
中侍大夫、康州防禦使、熙河路鈐轄、知西寧州兼隴右都護博先之堂兄,襄武、安化軍節度使、檢校少師、開府儀同三司博文之堂弟。博施名位雖與二昆季相遼遠,然皆以字聞於時……博施諱賑……元祐四年秋,博文以明堂恩奏補三班借差。紹聖末,沿白草原之累,例被降黜……大觀二年,博文遺表授承信郎。三年,堂侄中亮大夫、忠州團練使珏用年勞回授保義郎,而博施亦莫入仕也。
志文並未點破王博文、王博先的全名,不過上文已從鄉里世系的角度指出王賑(字博施)是王贍堂弟,「以字聞於時」的王博文即為王贍。從官爵仕履的角度出發,可以進一步驗證上述結論。王賑在大觀二年(1108)以「博文遺表」得授承信郎,故王博文顯然先於王賑去世,「襄武、安化軍節度使、檢校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是他死後的贈官。在元豐改制後,節度使、檢校三少、開府儀同三司這樣的贈官組合僅稍遜於以節度使管軍三衙的苗授、姚麟,而勝過屢立戰功、出任陝西諸路帥臣的折可適、劉仲武,大致與靖康年間的抗金主將种師道一等。哀榮與頂尖武臣相侔的王博文絕非無名之輩,而必然是北宋晚期的重要軍事統帥,結合寧遠寨的鄉里與王姓「貝」旁的姓名,他只能是元符三年(1100)率軍攻占青唐、拓邊湟鄯的王贍。此外,宋制無襄武軍節度,故「襄武」是王博文的諡號。按蘇洵《諡法》,「襄」的含義是「闢土有德」「因事有功」,而「武」不僅多用以標示武臣身份,而且同樣指向「闢土斥境」,均與王贍相合。
王贍死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而王賑在大觀二年(1108)憑藉「博文遺表」遷官,這一看似矛盾的事實恰可以驗證上述推斷。宣和四年(1122)伐遼前夕,宋徽宗授意執政王安中撰文總結宋神宗以來征討西夏、青唐的成就,並親自賜名為《定功繼伐碑》。在這篇昭示宋朝對西北拓邊事業官方評價的碑文中,哲徽兩朝的青唐攻略有三個重要節點:第一個是元符年間王贍「畫取青唐」,第二個是崇寧二、三年王厚收復湟鄯諸州,第三個是大觀二年平定溪哥城西蕃王子臧征撲哥、置積石軍。在積石軍建立後,北宋「師逾青海,至節占城,草(黃)頭回紇族數萬,官其酋豪,通道于闐,底貢寶玉,而地辟青唐之外矣」,青唐攻略基本完成。作為取青唐的首功之臣,王贍在崇寧二年(1103)王厚收復湟州後追贈節度留後,大觀二年青唐攻略基本完成之際,應與「賜玉帶……官子孫一人」的蔡京,「加檢校司空,仍宣撫」的童貫和「進官一等」的諸執政一道,再次得到褒賞。他「襄武、安化軍節度使、檢校少師、開府儀同三司」的官爵諡號當在此時追贈。所謂大觀二年「博文遺表」,應為王贍子孫以其遺表恩名義上報朝廷的受官親屬名單。
仰賴王贍的恩蔭,其子王珏在崇寧二年得授通事舍人,這當非直接負責中央朝會、通進事務的閣門司屬官,應仍在西北特別是熙河路任職。大觀二年王贍因宋朝降臧征撲哥、建積石軍再次得到追贈,王珏當亦隨之遷轉官職。至晚到宣和二年(1120)王賑去世,王珏已升任中亮大夫、忠州團練使,寧遠王氏自王君萬以降連續三世仕至遙郡團練使以上武官。可能是王贍親弟的王博先(其名不詳)亦在宣和二年以遙郡防禦使終於熙河路鈐轄、知西寧州(即鄯州)、隴右都護任上。有必要指出,宋朝首任知鄯州、隴右緣邊安撫使正是王贍,宋朝棄鄯州後置隴右都護府於湟州,王贍又成為首任隴右都護。因此,王博先能夠出任河湟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多少與王贍的遺澤有關。王賑本人在元祐四年(1089)以王贍明堂恩入仕為三班借差,此後可能在熙河路軍中效力,紹聖末因熙河路虛報戰功的窩案而「例被降黜」,或即從此歸鄉,大觀二、三年兩次憑藉王贍父子的恩蔭遷轉武階,雖然再未出任實職,但仍憑藉家族威勢「怡然里居」「為歌酒之樂」。
被捲入北宋晚期激烈黨爭與詭譎政局的政治人物大多有著屢起屢落的仕宦生涯和搖擺不定的身後評價,青唐元勛王贍亦不例外。宋朝對其功過的定性與徽宗朝的政局變動密切相關,不僅他本人一生榮辱系之於此,親族仕途起伏亦深受影響。不過,王贍結局之酷烈,又與多數朝臣不同,而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北宋寒族蕃將這一出入蕃漢之間群體的宿命。下文將主要爬梳寒族蕃將在北宋中後期的遭際,嘗試分析背後的社會、政治、文化因素,並藉此觀察寒族蕃將在北宋國家體制中的位置。
三、北宋中後期寒族蕃將在國家體制中的位置
寧遠王氏本是沿邊寨堡控制下的弓箭手家庭,直到王君萬時才開始顯達。他在熙河開邊前只是下層軍官,但至晚在熙寧五年(1072)已成為熙河經略主持者王韶的心腹武將,並於此年和王韶一同因經濟問題受到反對派的集中攻訐。王韶正式出兵河湟後,王君萬參與了收復河州、迫降木征等重要戰役,並迅速躍升為熙河路都鈐轄、副總管,成為本路最高級武官。王安石回應神宗將帥難得的憂慮,甚至以「如王君萬,方其為指使時,孰謂其可使?因事立功,然後知其可使爾」為例進行勸解,由此不難看出王安石、王韶等開邊主導者對王君萬的青睞。王贍日後投靠熙河路經制使李憲,李憲不僅多次為王贍上奏請功,更曾請求減免王君萬死後其家拖欠朝廷的巨額債務,史官「始因李憲以進」的斷語不算偏頗。父子兩人均通過趨附邊帥的方式進身,隱約透露出缺乏部族支持的北宋寒族蕃將對國家體制的高度依附。
同樣在熙寧年間驟貴的韓存寶亦在熙河開邊中屢立戰功,「年未四十,為四方館使、涇原總管」。他與王君萬兩人長期配合作戰,熙寧八年(1075)熙河路推行將兵法時又分別以本路都鈐轄、鈐轄的身份兼任第一將、第二將的正將,元豐元年(1078)更一度同時任熙河、涇原兩路的最高統兵官。不考慮五代宋初普遍帶有禁軍背景的沙陀系武將,王君萬、韓存寶實際上是第一批成長為高級政區軍事長官的北宋蕃將。他們的順遂仕途不僅受益於熙河開邊的歷史機遇,亦與其寒族蕃將的出身有關:這種出身不僅使其高度依附國家體制,也使他們較部酋蕃將更受信任。
宋朝對蕃族官兵的歧視性政策是學界長期關注的議題,一般認為蕃官在虛銜敘位上不得與漢官均禮,「雖至大使臣,猶處漢官小使臣之下」,在實職任用上不得換授漢官差遣,權力限於所在部族地區,即便是銳意邊事的神宗、哲宗亦未能徹底突破這一原則。不過,「蕃官」實際不完全是族屬概念,反對蕃官「悉依漢官之法」者的理由,是其「職名雖高,只是管勾部族人馬,凡部族應有公事,並系須從漢官彈壓理斷」,「使自營處,官資雖高,見漢官用階墀禮,所任不過本部巡檢之類」,指向的是始終世襲部落首領、尚未徹底體制化的部酋蕃將。劉光世的曾祖父劉紹能被認為是第一個突破上述限制的蕃官,他在熙寧六年(1073)升任鄜延路都監,「舊制,內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入京朝見後亦「依漢官例衙謝」。不過他的部落由其子劉永年承襲,本人及家族的漢官化、編戶化均不徹底。即便在換授漢官差遣的八年後,鄜延路經略司與宋神宗在正式公文中均仍稱劉紹能為「蕃官」;晚至紹聖四年(1097),承襲部酋的劉紹能孫劉延慶在公文中亦作「蕃官巡檢」。與此不同,由弓箭手或正兵途徑進入北宋軍隊的蕃族武將在公文中一般不稱「蕃官」,如王君萬父子、韓存寶等人均系顯例。從稱呼推測,針對部酋蕃將的種種限制未必適用於寒族蕃將,王君萬、韓存寶能夠在熙豐之際仕至高位,或許部分得益於他們相對寒微又脫離部落的出身背景。
但是,北宋寒族蕃將常常又會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王君萬在元豐二年(1079)因「借請給糴邊儲錢,違法回易」左遷鳳翔府鈐轄的閒職,又「盡籍君萬家產以償所貸結糴錢,猶欠官本萬餘緡。君萬憤甚,不一歲遂死」。此案並非單純的貪腐案,而有熙河路草創期財政管理權的爭奪、制度規範的逐漸調適、熙河經略使高遵裕與措置熙河路財利孫迥的嚴重對立等背景。韓存寶在元豐四年(1081)因征瀘夷無功又擅自招撫夷人首領而被神宗下詔誅死,他的罪行不是特別嚴重,神宗在世時接替韓存寶征瀘夷的林廣即稱其「雖有罪,功亦多……不至於死」,並因此得到輿論讚賞。神宗日後試圖誅殺盜用經略司官印的文臣徐勛,在遭到輔臣阻止時亦感嘆「然則韓存寶何罪」。此外,不僅元祐年間的士大夫普遍同情韓存寶的遭遇,哲宗親政後曾布亦以此事作為前車之鑑,致書章惇勸其出面阻止哲宗誅折可適。元祐史官認為韓存寶之死是因為「時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從神宗御批「韓存寶出師逗撓,遇賊不擊,殺戮降附,招縱首惡,已正軍法」並專門抄送陝西沿邊諸路帥司來看,上述意見是有道理的。王贍被捲入哲宗死後舊黨反撲的浪潮,枉死流放途中。王君萬、韓存寶都是一路總管,王贍亦以正任團練使、熙河路鈐轄的身份都護隴右,掌握湟鄯軍政大權,地位不在尋常路總管之下。宋仁宗親政後,罕有其他因政治原因不得善終的高級武將,北宋中後期的寒族蕃將卻頻繁遭此厄運,不得不說其背後存在某種結構性因素。
同為蕃將,劉紹能被指責暗通西夏,本人又確有親屬在西夏境內居住,故一度被押赴御史台審查,但最終在神宗的直接授意下官復原職。世襲鄜延路小胡族巡檢的胡繼諤受到本路帥臣龐籍劾奏「誅剝蕃部,其下多怨讟」,因此被解送京師,旋因陝西轉運使卞咸「言邊人頗思繼諤」而不復加罪,本人調任虢州都監,另擇族人繼任本族巡檢。部酋蕃將常能得到從輕發落的優待,固然與其較少深入參與朝廷政爭、所犯多為事務性罪責有關,更關鍵的還是他們背後部落族眾的社會基礎,這一點在胡繼諤案中尤為明顯。一方面,宋朝刻意限制部酋蕃將的晉升渠道,又積極推行部族分化政策,瓦解內附蕃部勢力;另一方面,宋朝的防範措施恰恰透露出他們對部酋蕃將及其世襲部落的忌憚,在處置部酋蕃將時態度相對慎重。與此相反,高度依附國家體制、缺乏部落組織支持的寒族蕃將在晉升渠道較少受到限制的同時,卻也在面對政治風險時更為脆弱。
相較於部酋蕃將,寒族蕃將「蕃漢之間」的特質更為突出。從制度架構來看,他們的升遷渠道與漢人將官相仿,似乎不受朝廷對蕃官職任、階次等禁約的限制;從政治生態出發,在強調夷夏大防、文化氣質內向的北宋,他們又仍被士大夫攻訐為不可信賴的「蕃夷之人」,不被朝野上下所信任。在宋神宗以降的西北拓邊中,他們既憑藉自身的軍事技能在正規軍內部逐級晉升,又利用通曉蕃情的特長為宋朝撫納部族勢力、徵募蕃裔兵士,某種意義上成為宋朝與蕃族交往互動的中介,官位迅速升遷。從王贍、王博先兄弟的仕履來看,寒族蕃將在北宋晚期仍能仕至路級軍事長官或緣邊重鎮知州並統領蕃漢大軍。但是,他們的威勢又比部酋蕃將脆弱得多,這一點在兩宋之際表現得尤為明顯。
以劉光世、李顯忠為代表的部酋蕃將在兩宋之際大綻光芒,寒族蕃將卻相對暗淡。兩種蕃將的不同結局,關鍵在於他們權力來源與社會基礎的不同。部酋蕃將始終與其部落族眾保持密切聯繫,劉光世行至鄧州時仍可派單騎返鄉徵發部落內的未籍余丁;寒族蕃將的權力則建立在北宋軍隊中的科層制上下級關係以及宋朝邊疆治理體系正常運轉的基礎之上,隨著北宋正規軍的崩潰與南宋失去對西北邊疆地區的控制,寒族蕃將失去賴以為生的土壤,迅速淡出歷史舞台。出身「西蕃部落」的環州人楊惟忠長期在正規軍系統內晉升,北宋末仕至高陽關路馬步軍副總管,在靖康年間率河北兵勤王趙構並出任大元帥府五軍都統制,一度成為趙構麾下最高級的統兵官,但旋即失勢,被評為「官崇志滿,不肯盡力,聲譽日衰」。與以本族部眾為核心部曲的劉光世不同,部下多由河北潰兵盜匪整編而來的楊惟忠更可能出身寒族蕃將,其晚景或可作為該群體歷史結局的一個註腳。
結語
與唐代蕃將相仿,北宋蕃將亦可依據其與部落的關係分為部酋蕃將和寒族蕃將。作為北宋時期文獻記載最豐富的寒族蕃將世家,王贍家族無疑是理解北宋寒族蕃將特徵的典型案例。他們可能原系秦州洛門谷西部一帶的吐蕃部民,隨北宋西部邊境的拓展而以弓箭手的身份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在熙河開邊中屢立戰功的王君萬蕃族底色濃重,其子侄王贍、王賑則不僅崇文好禮,更刻意隱諱家族的蕃族出身,在繼承熟悉蕃情這一特長的同時,已經表現出較高的漢化程度。同始終控制世襲部落的部酋蕃將相比,傳世文獻從未記錄王氏家族存在長期控制的世襲部曲。他們往往憑邊帥的賞識而晉升,又常因捲入政治漩渦不得善終,被視為青唐首功的王贍更成為北宋晚期黨爭的風向標人物,其仕途起伏繫於朝堂政局之變幻。以上種種,從不同側面證明寒族蕃將由於脫離部落生活、依附國家體制,已經走上與部酋蕃將不同的發展道路。
文章來源:原刊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