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球的運動健兒陸續抵達巴黎時,這個夏天也因即將到來的奧運會而被「點燃」。隨著滑板、霹靂舞、攀岩和衝浪等新項目進入奧運大家庭,我們看到了更加多元、包容的運動文化。而對於許多觀眾而言,或許有的項目還稍顯陌生,比如離街頭「最近」的滑板。
通過與不久前獲得女子滑板街式項目奧運參賽資格的中國滑板隊隊員曾文蕙的對話,我們一起打開新的視角去了解這項運動,以及滑板女孩對自由、平衡的理解,對自己的認知蛻變和對未來的期待與激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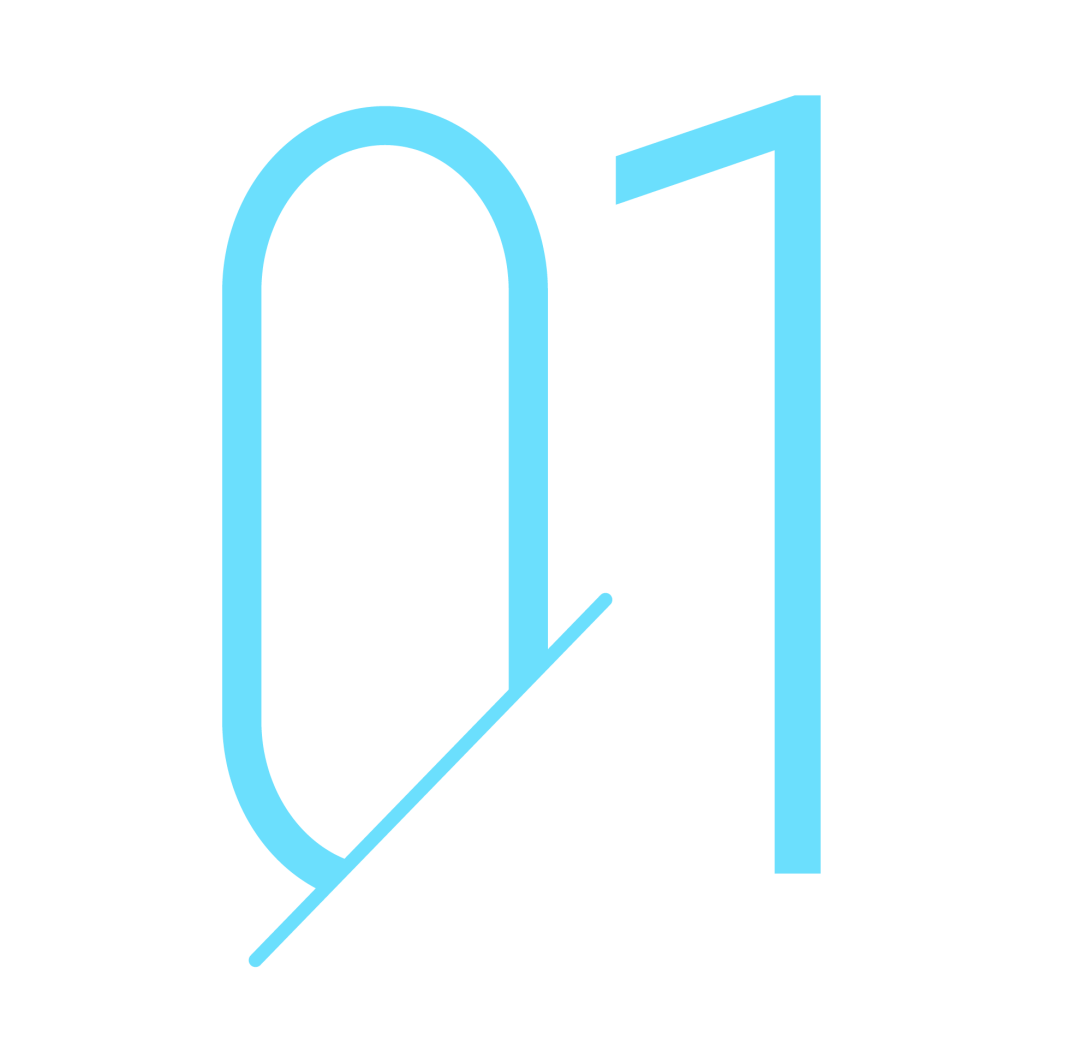
在城市裡「逐浪」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西海岸的加州街頭出現了一批「浪里白條」,他們將衝浪運動「搬」到了陸地上,給木板加上輪子,起名為Skateboarding(滑板)。正是這群「激進分子」的自發創造,開啟了滑板運動的無限可能。

在風平浪靜的時候,滑手們最初熱衷於將城市地表適合滑行的區域視為滑板道具,他們把未注水的泳池和一些管道型的設施當作陸地上的海浪,通過用身體的伸展和調整重心的方式,在場地里滑行蕩漾,尋找與衝浪相似的快感。
後來,不僅僅滿足於碗池的他們將創想延伸到街頭的一切地形,樓梯、長凳、手扶欄杆,甚至是石頭,都成了現成的滑板道具,街式滑板也由此誕生。
就這樣,滑板從衝浪運動中分離出來,與當地的城市風貌、生活方式、衣著風格以及音樂韻律共同「生長」,形成了一種以城市為主導的次生文化,街頭滑板也逐漸成為人們眼中活力帥氣的風景線。

滑板遇上奧運會
滑板比賽在巴黎奧運會中分為兩個項目:碗池和街式。運動員在完成他們最拿手的絕招同時還要保證動作的難度、速度和多樣性。
碗池賽在一個充滿各種曲線、弧面的凹槽場地中進行,運動員需要利用這些弧面來增加起跳高度,從而在空中完成各種動作。裁判組將根據選手空中動作的高度、速度以及利用弧面和障礙物的能力進行打分。每位選手需要進行三次表演,每次表演45秒,三輪最好成績記作最終成績。
街式賽則在一條筆直的「街道式」場地舉行,場地中包含樓梯、扶手和其他能夠重現街頭環境的障礙物。運動員要表演一系列花式技巧,控制滑板的能力將決定他們的得分。街式賽要進行兩輪表演,每輪表演45秒,包括五個技巧展示。比賽最終得分由兩輪最高分和兩個最高技巧分相加得出。

滑板的「奧運首秀」是在上一屆2020東京奧運會,隨它一起完成首秀的,還有來自全世界的頂級滑手們,其中就包括了當時只有16歲的曾文蕙,彼時她以第六名的成績創造了中國奧運滑板項目的歷史。
「東京奧運會之後,我才發現自己更熱愛滑板了。」這位即將第二次征戰奧運的女孩其實也才19歲,極限運動對於精英運動員的要求近乎苛刻,三年間也有很多天才型選手的湧現,「久經沙場」的曾文蕙意識到,自己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而且因為滑板,她去了更多地方,認識了更多人,也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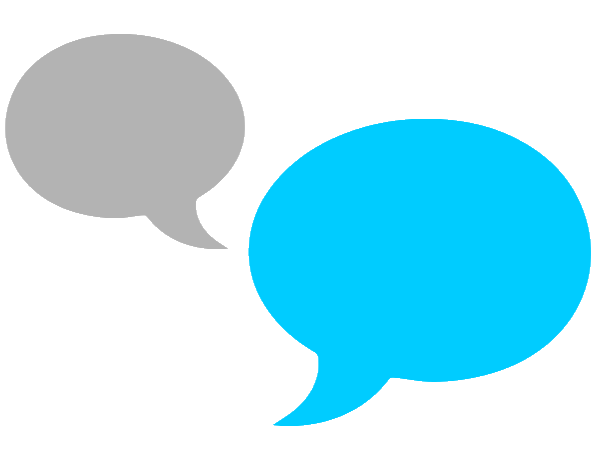
Talk with 曾文蕙

曾文蕙
中國滑板國家隊街式隊員
奧地利Red Bull簽約運動員
摔了就站起來
Q:你在滑板前還練過武術,是從幾歲開始練武術?又是怎麼接觸到滑板的?
A:我從一年級開始接觸武術,每天放學後會去武術館進行一小時的訓練。二年級時,省武術隊來挑選隊員,就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去參加了選拔,有幸被選中,就在武術隊待了四年。2017年,在六年級升初一的暑假,武術教練告訴我有一個跨界選才的機會,可以去北京訓練一個月,我決定去嘗試一下。到北京後,第一次見到了滑板,感覺很興奮。第一次上滑板課時,我上板的速度非常快,半天就能自如地滑行。後來我就開始在北京接受滑板訓練。一個月後,隊伍開始淘汰人,而我被留了下來。
Q:當時留下來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A:剛開始很難受,因為原本說好一個月後就回家,那時候還小,不喜歡離開家的感覺。之前去的武術學校離我家也很遠,交通也不發達,坐大巴需要一兩個小時,不能每天都回家,我還因此哭過一兩年。好不容易適應了,又從南方到了北方。但每當我哭著想回家,大家就會哄我留下來繼續滑板。後來認識了一些好朋友,幫我緩解了想家的情緒,自己也確實很喜歡這項運動,就一直滑到了現在。
Q:你覺得武術和滑板有什麼相同點和不同點?
A:相同點是它們都有很多轉體動作,都對身體素質有一定的要求。從小練習武術讓我對肌肉有更好的控制,在接觸滑板後上手更快。不同點在於武術更傳統,而滑板更自由。
Q:滑板會有跌倒的過程,練武術肯定也吃了不少苦。為什麼喜歡並堅持這項運動?
A:信念感這個東西確實很微妙。最初練武術的時候是被家裡人安排的,為了強身健體,我並沒有很喜歡,也沒有很享受。但接觸到滑板以後,就莫名地喜歡上了,就算摔倒了,我也不會覺得害怕。摔了就站起來,受傷了也沒事。我覺得這離不開熱愛。

去往更遠的街頭
Q:對你來說,滑板最大的魅力是什麼?
A:滑板很帥。學習新動作的過程很吸引人,從無到有去掌握一個動作的過程,會讓我很有成就感。
Q:從六年級開始接觸滑板到現在,有沒有遇到過想要放棄的時刻?遇到低谷期,或者狀態不佳的時候,你是如何調整自己,重新振作的?
A:我不會放棄滑板,因為真的很喜歡。至於低谷期,確實遇到過。但我很慶幸,每次想要放棄的時候,教練都會幫我調整心態。而且,我經常有機會去國外訓練、比賽,去感受不同的氛圍,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調節。
Q:在壓力很大的時候,你是如何放鬆自己的?
A:最近我發現跟朋友聊天對我來說是最有效的放鬆方式。


Q:現在你去的地方更遠了,還會想家嗎?
A:現在已經不太會想家了,但每周至少會打電話回家四次,確認家人身體都好。我不是那種會撒嬌的性格,但會和家人保持聯繫。現在通訊、交通也便利了很多,這兩年回家的次數比以前多了一些。去年我回了三四次,雖然每次都只有短短一兩天。今年因為全力備戰奧運,暫時還沒回家。
Q:你經常參加比賽和訓練營,去過很多地方,哪些城市給你印象最深?
A:加州,尤其是聖地亞哥,那裡是滑板的發源地,陽光特別好,總能讓人心情愉悅。今年我受邀去那裡參加了奧地利Red Bull Adapt訓練營,認識了很多滑板運動員,而且打破了我對大家原有的印象,大家在賽場上和生活里的性格和表現都會有些反差,在訓練營里很多人私下都很友好很親切,有一種家庭的感覺。我覺得多出去走走,接觸新的事物,能夠為生活帶來更多的希望和活力,心態也會變得更加開放。
Q:滑板代表了自由、不受約束,有著街頭文化的特質。現在隨著滑板運動逐漸受到大眾關注,比如成為奧運會項目,與街頭文化的原生內容與精神之間產生了一定的反差,你怎麼看待街頭文化與這一世界級的賽事的相遇?你會不會想要回到街頭?
A:關於滑板進入奧運會後引發的 「限制自由」 的討論,我個人認為並不矛盾。我本身就是從滑板文化中成長起來的,所以不會單純地認為這是一個壞事。相反,我認為這兩者可以並存甚至結合。滑板比賽並不會完全剝奪街頭的自由,如果你覺得比賽環境不適合你,你可以回到街頭,兩者並不衝突。而且,我認為奧運也能為滑板運動帶來積極的影響,比如吸引更多人的關注和支持,促進滑板場地的建設等等。所以在我看來,比賽和街頭文化是可以兼顧的。我以後即使參加了更多的比賽,也肯定會回到街頭,繼續在那裡創造屬於我自己的未來。

享受,突破自己
Q:還記得第一次參加滑板比賽是什麼時候嗎?比賽和日常訓練有什麼不同?你是屬於比賽型選手,還是更偏向踏實穩定的選手?
A:第一次參加正式滑板比賽是在我接觸滑板一段時間後,具體時間記不太清楚了。比賽和日常訓練確實有很大的不同,比賽時氛圍更加緊張刺激,需要更高的專注度和應變能力。我覺得自己還是屬於踏實穩定的選手,有很多人比我更有天賦和實力。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我比較求穩,更注重平時的訓練和積累。
Q:從開始滑板到現在,你一共經歷過多少任教練?有沒有哪位教練給你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或者你從每位教練身上都學到了什麼?
A:一共有八任教練吧。我的啟蒙教練是於教練,他帶了我很多年。之後我還接受過幾位外教的指導,每位教練都在我不同的階段給予了不一樣的幫助,我很尊重他們。現階段Dan和Rodrigo對我的影響很大。Dan帶我去了很多地方,讓我感受到了滑板的魅力。Rodrigo則更多地關注我的心理狀態,幫我調整心態,還帶我認識了很多全球厲害的滑手,打開了我的視野。(這兩位教練也是巴黎奧運會中國滑板隊的教練組成員:丹尼爾·彼得·維恩懷特、羅德里戈·彼得森·塞薩里奧)
Q:上屆東京奧運會上,是作為中國滑板隊唯一一位參賽選手,今年第二次即將參加奧運會,心情相比上一屆有什麼不同嗎?
A:我覺得更加興奮和激動了。第一次參加奧運會的記憶有些模糊,因為當時還太小,沒有帶手機去記錄那些瞬間。這次有了經驗,希望可以更加享受比賽的過程。我還打算多記錄一些比賽和日常生活的點滴。
Q:對自己有什麼期待嗎?
A:希望能夠突破自己上次的成績。我也非常期待巴黎奧運會的休息室和活動場所,感覺應該會很有趣。

在即將到來的巴黎奧運會,滑板將繼續作為正式比賽項目,在位於巴黎市中心的著名景點協和廣場進行。女子街式滑板的預賽和決賽時間為7月28日,屆時一起為中國滑板隊和曾文蕙加油!
編輯丨danz
採訪記錄丨Red Bull
圖丨Red Bull,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