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汤因比: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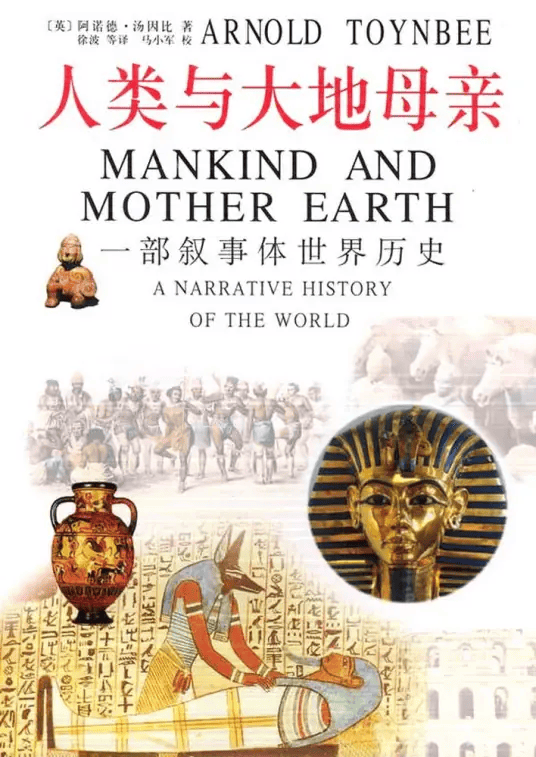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在其撰写的世界通史《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中,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特征和前景有着独到的论述,对于中国文明的未来做出了积极而乐观的展望;对于中国马拉战车、文字和青铜器的起源做了非实证性的假设。本书完成于1974年,英文版出版于1976年。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中国文明的起源
自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最早的地域性文明——苏美尔文明的早期以来,与之类型相似的文明社会来去匆匆。诸区域文明中最早的样本——苏美尔文明并没有长久、稳定地保持其独有地位。大约公元前三四千纪之交,法老文明诞生于埃及;公元前三千纪的下半叶,小亚细亚、克里特和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区域文明。其中,也有一些幸存至今,但即使它们中间最古老的幸存者——中国文明,也比它的苏美尔、法老埃及的文明先驱至少晚了近1500年。
中国的区域文明(被称为商朝,别名殷)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即龙山黑陶阶段)。与西南亚的肥沃新月地带和埃及不同,中国文明的兴起没有伴随着定居地的变动。如同地中海东部一样,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依赖于降雨对农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风化黄土地带,包括甘肃、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东部的黄河与汉水、淮河间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龙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开发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线1000年左右,苏美尔和埃及类型的治水方式才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东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像苏美尔文明及其前身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不过,两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新趋势。与苏美尔一样,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伴随着统治集团与臣民阶层财富和权利的严重分化。安阳(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乌尔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拥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在苏美尔,冲积地被开发成耕地推动了社会财富的不断集聚,也使得极少数统治者能够获得穷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在中国,也出现了同样邪恶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同步的增长。
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突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草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可能既细微难辨又比较间接。中国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文字的结构来自苏美尔语,这种结构(对表意符号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逻辑又显得笨拙)过于罕见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个不同的场合独立发展成形的。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项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铜器就像其文字一样,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青铜器皿设计精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青铜器或许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过这种原型在今天已无迹可寻。但是,这一假设仅能解释手工制作风格的源头,而冶金技术的突然获得则仍然是一个谜。
商代青铜器的构成元素中,锡的含量较高(17%)。距离黄河流域最近的锡、铜产地是马来亚和云南;但熔合锡铜和铸造合金制品的技术不可能由南方传入黄河流域。东南亚最早的青铜器文化(称之为“东山文化”,位于越南北方)也不会早于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后半期。暂且不论铜锡合铸技术来自何方,而此时的铜、锡却早已输入黄河流域为中国所用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商代的金属来源地。因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成分,具有经由欧亚草原传入中国北部的西方文化成分之外,还含有一定的热带文化源头。中国的商代主要种植小麦、谷子和水稻;饲养的畜类除了普通的家畜外,还有水牛;他们驯养的两种猪,其中的一种起源于南方。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植物最早是在一些热带沼泽地区驯化出来的;这一地区的文化与中国北部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似。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亚洲的热带地区到黄河流域的南部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类似的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距黄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不仅相距遥远,而且为崇山峻岭所隔绝。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到了印度那些现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此点至今无据可考。
因此,商文明进程中的热带渊源仍属不解之谜。根据中国的传说,如今地处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以南的地区,更不必说越南境内,都仅仅是通过被汉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国北方移民的渗透。不可否认,这一传说并非只是中国文化偏见的反映。公元19世纪,长江流域南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发现了一些幸存下来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从而证实了这个传说。此外,当代中国南疆与东南亚邻国的交界地区还发现了其他幸存下来的原始民族。不过,最早培育出水稻、驯化了水牛的地区依然无法确定。
中国文明的统一性和未来
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次大陆到直布罗陀海峡,在中国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广大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事件。与此相反,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划时代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统一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分界线。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却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那时,中国不时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但到公元前221年,在或短或长的分裂和混乱的插曲之后,它再次达到政治上的统一。
在中华帝国,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
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非必然互相排斥的社交表达方式。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彼此争战的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节选自[英]汤因比(A.Toynbee):《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