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公司针对拍品真伪瑕疵的免责声明是否有效?——翰海公司吴冠中作品《池塘》拍卖案始末
拍卖公司对拍品不保真,是艺术品行业的一个“行规”。但为什么实力更强,对艺术品收藏和流通更专业的拍卖机构,反而可以通过一纸“不保真”的声明就可以免责呢?免责的范围和效力又是什么呢?除了法律规定,一个与著名画家吴冠中的作品相关的案例,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这个案例,在我国艺术品拍卖市场重申了对拍卖法就拍卖人免责条款的确认效力,以及对于“买者自负”这一长期以来约定俗成形成的交易惯例的维护,固化了拍卖行和竞拍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我们再回顾一下此案的始末:
起诉和答辩
原告苏小罗(化名)起诉称:2005年11月,我在翰海公司网站上看到该公司将举办2005秋季油画雕塑拍卖会的公告信息,其中重点介绍了此次拍卖有吴冠中的油画作品《池塘》。为证明该画是吴冠中所作,翰海公司提供了一组由安徽美术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的《风景油画选辑(三)》明信片,其中第五张是《池塘》。翰海公司并在其印制的《拍卖图录》中对《池塘》作了详尽的介绍。
由于翰海公司是国内著名文物专业拍卖公司,其在拍卖公告、《拍卖图录》中对《池塘》的描述加入其主观意见,以肯定的口吻对该画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价,使我相信该画的真实性。2005年12月11日,我经竞价以2300000元拍得署名吴冠中的油画《池塘》,并向翰海公司支付佣金230000元。后我发现所拍得的《池塘》是假画,而该画是萧大元委托翰海公司拍卖的,故起诉请求:1、撤销我与翰海公司拍卖合同关系;2、萧大元(化名)、翰海公司连带返还拍卖款2300000元、佣金230000元;3、萧大元、翰海公司赔偿律师费100000元、调查取证差旅费20000元、证据保全费1000元,共计121000元,并由翰海公司、萧大元承担本案诉讼费。
萧大元在一审法院答辩称,其与苏小罗不存在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且苏小罗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撤销权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萧大元同时提出翰海公司在拍卖前发布了拍卖公告、展示了拍卖标的,苏小罗怠于行使查验权利,拍卖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同意苏小罗的诉讼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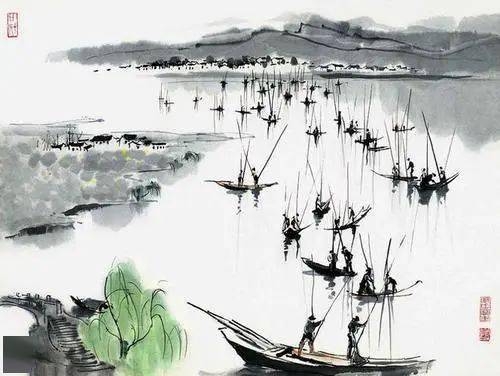
翰海公司在一审法院答辩认为,其履行了拍卖法所规定的全部义务,对委托人萧大元的身份及其对拍卖标的的所有权、处分权进行了审核。翰海公司在《拍卖图录》上刊登了《业务规则》,其中作出了免责声明,明确规定不对拍卖品真伪承担责任。苏小罗在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时,签名确认“买方已认真阅读《业务规则》……买方同意所有拍卖会成交之中国字画、瓷器等其他拍卖品均无需附带真确保证”。苏小罗起诉请求撤销双方合同于法无据,不同意苏小罗的诉讼请求。
一审事实和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2005年9月2日,萧大元与翰海公司签订《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委托拍卖合同书》(编号A0012708),约定萧大元将油画《池塘》委托翰海公司进行拍卖,注明作者为吴冠中,保留价2200000元,并备注“安徽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风景油画选辑》图五”。
萧大元称《池塘》系从张帆处以1200000元购得,但双方并未就此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原审诉讼中,萧大元提供2008年7月9日《北京青年报》,其中报道“张帆告诉记者当时一个新加坡的商人薛德光委托他们来卖这幅油画《池塘》……萧大元买了这幅画……张帆告诉记者,去年萧先生找过很多次,说画可能有问题,希望能不能退画……但薛德光一直没有再联系上。”萧大元并提供中国工商银行2005年9月2日、7日、17日、10月17日个人业务凭证4张,借方是萧大元、贷方是张帆,用以证明从张帆处以1200000元对价购买油画《池塘》。
翰海公司称拍卖公司只核实拍卖品的权利状况,没有义务核实真伪,也没有询问此画的来源,画的瑕疵应由萧大元保证。就诉争拍品在拍卖前的审核过程,翰海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
2005年12月11日,翰海公司在网上发布2005年秋季油画雕塑专场拍卖公告,其中重点拍品介绍有如下内容:“本场第二件‘双款拍品’是吴冠中油画作品《池塘》,画于1972年,时年53岁。十年后,他又将此画修改一下,并在画上题写‘抽暇改老画,好似故地重游。一九八二年’。画面以他下放的农村为题材,崇山峻岭,迎面而立,不乏中国北宋山水画的雄浑厚重;中景林木繁密,充分体现出他在欧洲所学到的绘画技艺;近处则是池塘澄明,显现出中西融合的艺术风格。该拍品评估1800000元至2500000元人民币”。
翰海公司在其印制的《拍卖图录》中对油画《池塘》有以下说明:“画于1972年,(吴冠中)时年53岁。十年后,他又将此画修改一下,并在画上题写‘抽暇改老画,好似故地重游。一九八二年’。画面以他下放的农村为题材,崇山峻岭,迎面而立,有中国北宋时期国画的崇高美感;中景是茂密的树林,充分体现出他在欧洲所学到的绘画技艺;近处是池塘,点明要有中西融合的艺术风格。吴冠中在1970年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之时,其妻子亦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长子可雨在内蒙牧羊,次子有宏于山西农村劳动。1972年,53岁的吴冠中被允许每周作画一天,因没有足够画具,只好画在纸板上,以农家柳条编成的粪筐作画箱,人们戏称他为‘粪筐画派’。画了一批油画,包括《瓜藤》《高粱与棉花》《房东家》等。他当时对自己的艺术要求是群众点头、专家鼓掌,由此形成他后来提出的‘风筝不断线’的目标。1977年起,吴冠中先后到广西南宁、浙江绍兴、福建厦门、鼓浪屿、武夷山、江西井冈山等地写生,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巨幅油画《长江三峡》,1979年,吴冠中被邀请到四川、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广东、广西、山西、辽宁等省巡回展出,名声大振大江南北”。以上内容也在翰海公司网页资料中出现。
《拍卖图录》中关于《池塘》的著录介绍中,载有:“1、《风景油画选辑二》,安徽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图版5。2、《吴冠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p197,吴冠中年表;1972年”。
关于著录1,苏小罗称翰海公司曾提供一套署名为安徽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1版的《风景油画选辑(三)》明信片,其中第5张为“吴冠中,池塘”。苏小罗庭审中提供的工商查询信息显示,安徽美术出版社成立于1986年9月25日。且该明信片的印刷企业也是伪造的,并不存在。原审诉讼中,翰海公司与萧大元均否认曾向苏小罗提供过该套明信片。翰海公司称其提供的是安徽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油画风景选辑二》明信片,在图版五上载有《池塘》。萧大元提供《篆刻浅谈》,该书载明是安徽美术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
关于著录2,《吴冠中》一书载明,吴冠中“1972年、53岁,年中,被军队领导调到邢台师部指导文艺兵作画,作油画《池塘》《西柏坡山村》等”。翰海公司称在《拍卖图录》中对诉争拍品的介绍内容来自该书,但关于诉争拍品的具体描述是翰海公司自己写的。
翰海公司在《拍卖图录》中印制的业务规则中,有如下规定:第八条,本公司在拍卖日前编印的图录或以其他形式对任何拍卖品的作者、来历、年代、尺寸、质地、装裱、归属、真实性、出处、保存情况、估价等方面的介绍,仅供买家参考,不表明本公司的任何担保;第二十一条,本公司任何人或代理人用任何方式对拍卖品所作的介绍、描述及评价属参考意见,不表示本公司对拍卖品的任何担保;第二十二条,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本公司可以考虑撤销交易并向买家悉数退款:1、从拍卖日起二十一日内,买家向本公司提出书面报告,指出该拍卖品为赝品;2、收到书面报告十四日内,本公司收回该拍卖品,该拍卖品必须保持拍卖当日原状;3、买家提出的依据能令本公司确信该拍卖品为赝品,同时买家拥有该物品无可置疑的所有权和转让权;4、该拍卖品确系本公司出售;第四十九条,本公司有权对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的任何物品摄影、摄像、进行图录出版、文告、展示和其他形式的影像作品,并拥有上述作品的著作权,但本公司及其职员或其代理人不对其意见的准确性(包括作品真伪)承担任何责任。
2005年12月11日,苏小罗作为竞买人签署了《竞投登记单》,其中载明:买方已认真阅读翰海公司的业务规则,并同意在拍卖交易中遵守上述业务规则中的一切条款;买方同意所有拍卖会成交之中国字画、瓷器等其他拍卖品均无需附带真确保证。
同日,在翰海公司举办的2005秋季拍卖会油画雕塑专场中,苏小罗现场拍得油画《池塘》一幅,支付落槌价2300000元和佣金230000元,并取得该拍品。
2007年11月19日,苏小罗委托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致函翰海公司((2007)金律函字第1115号律师函),表示《池塘》有伪作之嫌,该函显示:2007年8月,湖南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国家“十一五”重点文化出版项目之一的《吴冠中全集(9卷)》大型丛书,但未收录《池塘》;2007年8月以来,苏小罗几度委托多家国内知名拍卖行拍卖《池塘》,均被拒绝;2007年10月10日,雅昌艺术网发表了东南亚著名收藏家郭瑞腾的文章,题目为《提防利用拍卖活动“洗画”》,文章直指《池塘》系伪作,并非吴冠中真迹。
2008年7月1日,苏小罗携油画《池塘》到画家吴冠中家中请求确认真伪,吴冠中认定该画系伪作,并在该画外裱玻璃上书写“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2008年7月1日”。
上述事实,有委托拍卖合同、付款凭证、证书、拍卖图录、竞投登记单、拍卖成交确认书、网页资料、报纸书籍资料、函件、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证明。
一审判决和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在拍卖交易活动中,拍卖人对拍品的瑕疵担保责任,明显弱于一般的买卖合同交易,其有权就拍品瑕疵作出免责声明,因而拍卖活动中竞买人或买受人对拍品瑕疵的检查义务,将明显重于一般的买卖合同交易。
本案中,苏小罗通过竞买获得诉争拍品,其与翰海公司形成拍卖合同关系。萧大元虽非拍卖合同的直接当事人,但其作为诉争拍品的委托人,是本案拍卖交易活动中的当事人之一,系本案适格被告;关于诉争拍品的真伪问题,各方当事人各执一词。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苏小罗于起诉前的一年即应当知道诉争拍品是伪作,故萧大元关于苏小罗起诉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的抗辩意见不成立;就诉争拍品的来源问题,萧大元仅提供新闻报道及若干付款凭据为证,并未提供充分、翔实的证据材料。而翰海公司亦未就此进行必要的询问和审核。但仅凭萧大元的举证欠缺及翰海公司的核查欠缺,尚不足以证实翰海公司或萧大元在本次拍卖前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诉争拍品系伪作;翰海公司在拍卖过程中,对诉争拍品进行了一些以真实性为基础的文字描述。但从这些文字描述本身内容看,并无否定免责声明并对诉争拍品做出真确性保证之含义。
在不能证实翰海公司事前知道诉争拍品系伪作的前提下,翰海公司对诉争拍品适当地加以真确性描述,应属正常的交易活动范畴,其描述用语并无过分夸大之处,不构成虚假宣传;翰海公司针对诉争拍品真伪瑕疵所作出的免责声明具备我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之效力。而苏小罗在知晓该免责声明并且在竞买前能够充分了解诉争拍品实际状况的情况下,参与竞买系其自主决定的结果,其认为在拍卖交易中存在欺诈、重大误解且显失公平之事由,要求撤销拍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其要求的翰海公司及萧大元连带返还拍卖价款及佣金,并赔偿律师费、调查取证差旅费、证据保全费的诉讼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小罗诉讼请求。
二审诉辩主张
苏小罗上诉称:1、翰海公司不能享有《拍卖法》规定的“不保真”免责条款项下的权利。翰海公司未尽到对拍品真伪及拍品来源的审查义务;且翰海公司作虚假宣传,故意误导竞买人。2、萧大元提供伪作,并提供伪造的明信片用以证明伪作的真实性,即使免责条款适用于翰海公司,萧大元也不能因提供伪作享有免责权利。原审法院判决扩大了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加重了竞买人的义务,应予以撤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其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萧大元、翰海公司对原审判决无异议。
二审理由和判决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艺术品的鉴定工作在实践中更多依赖于鉴定者的个人经验和感受,目前尚无法律强制规定的审核方法以及市场经营自发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的鉴定标准。
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诉争拍品《池塘》的真伪存在很大争议,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对拍品《池塘》的真伪性做出足以令人信服的明确结论。但不可否认,《池塘》一画经拍卖过程指称的作者吴冠中本人指认为伪作,该拍品的经济价值已经受到极大影响,在无法明确拍品真伪的情况下,已客观形成该拍品存在较大瑕疵。
萧大元作为《池塘》的委托拍卖人,虽不能提供充分、翔实的证据证明该拍品的来源,但其作为《池塘》一画的持有人,在并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其作为拍品合法所有权人的事实应予确认。且萧大元虽未能提供拍品来源,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能因此推定其在拍卖前明知或应当知道拍品系伪作。
苏小罗提出萧大元经翰海公司向其提供的明信片是伪造的,但萧大元否认苏小罗持有的明信片即是其向翰海公司提交的明信片,对此双方各执一词,仅以苏小罗持有的明信片无法证明萧大元有提供伪造明信片以证明拍品真实性的事实。苏小罗上诉主张萧大元应对伪作承担赔偿责任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翰海公司所作免责声明是否有效一节,因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拍卖公司应负有对拍品进行鉴定的责任,且实践中由拍卖公司对所有拍品进行鉴定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
翰海公司在此次拍卖活动中履行了公告、展示、告知等义务,其对拍品《池塘》所做的宣传属于正常的商业运作,相关内容属于正常的介绍和对拍品的具体描述范畴,并未发现其中有主观上的夸大、诱导成分。
根据拍卖法相关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该内容也同时载入翰海公司业务规则,对此内容苏小罗在竞拍前已签字确认。作为竞买人,苏小罗在知晓免责声明并能够充分了解拍品现状的情况下参与竞拍,是其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苏小罗与翰海公司之间成立的拍卖合同关系是真实有效的,苏小罗应当自行承担拍品存在瑕疵的风险。
苏小罗上诉主张翰海公司不能享有拍卖法规定的“不保真”免责条款项下的权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苏小罗上诉请求撤销其与翰海公司的拍卖合同关系;由萧大元、翰海公司返还拍卖款及佣金、赔偿律师费等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据此,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判决的法律分析
艺术品是拍卖市场的常见拍品之一,但由于目前对艺术品的鉴定并未形成一套为大众广泛认可的鉴定标准,就拍品真伪也难达成共识。于是拍卖公司在拍卖规则中规定“瑕疵担保免责条款”便成为拍卖的行业惯例。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就在于瀚海公司是否做出了具有法定效力的免责声明。
一、拍卖标的物现状查验责任的分担
拍卖是一种公开竞买的交易活动,它采用卖方委托、公示拍品、当场竞价、落槌成交的一系列惯常固定做法来完成买卖交易。
我国《拍卖法》第三条对此亦加以明确规定,即:拍卖是以公开竞价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虽然在法学概念上拍卖合同属于买卖合同的一种,但与一般买卖合同相比,两者间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从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来看,拍卖合同是由拍卖公司和买受人达成的协议,拍品的真正权利人作为委托人并不与买受人直接构成合同关系,即拍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拍卖人和竞买人。
其次,从买卖的程序来看,拍卖的进行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这与一般买卖可以自由达成有所区别。
再次,从交易的过程来看,拍卖过程与一般买卖合同由标的物所有权人或处分权人与买受人之间直接进行洽谈磋商有所不同,拍卖是一种公开竞买的现货交易,采用买方事先看货,当场叫价,落槌成交的做法。
最后,从法律的适用来看,一般买卖合同适用《合同法》即可,拍卖有着特殊适用的法律,拍卖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以及拍卖程序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只有在《拍卖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能适用《合同法》。
从两种合同的比较差异可以看出,拍卖的实际交易过程与一般买卖合同中买方、卖方的交易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鉴于拍卖人并非拍品的实际所有权人或控制权人,只是接受权利人委托对拍品进行拍卖,加之拍卖交易过程的特殊性,拍卖人在客观上无法完全保证拍品毫无瑕疵。因而拍卖合同中拍卖人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故我国《拍卖法》在第十八条中规定“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和“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之际,在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又明确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由此可见,在拍卖交易活动中,拍卖人对拍品的瑕疵担保责任,明显弱于一般的买卖合同交易,其有权在拍卖交易中就拍品瑕疵作出免责声明,因而拍卖的竞买人或买受人对拍品瑕疵的查验义务,将明显重于一般的买卖合同交易。
正因如此,我国《拍卖法》在四十八条中强制性规定“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有关资料。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同时在三十五条中规定“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卖资料”,从而在程序及实体权利上保障参加拍卖的竞买人或买受人能够在拍卖交易完成前有效地全面了解拍品瑕疵情况,处于有备而来、充分了解拍卖标的物现状的地位,从而弥补立法规定中所弱化之拍卖人瑕疵担保责任和所强化之买受人查验义务,使各方当事人在拍卖交易过程中在权利义务上处于一种整体平衡状态。
二、拍卖人、委托人瑕疵担保责任免除要件
如前所述,《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明确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根据该规定,如果委托人和拍卖人事先并不知道拍卖标的的瑕疵,并且向竞买人声明其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和品质,就可以视为其已经将风险事先告知竞买人,一旦拍卖成交,买受人即使买受了有瑕疵的物品,也无权撤销合同,委托人和拍卖人对此也无须承担民事责任。结合该条规定,纵观整个《拍卖法》,瑕疵担保责任的免除要求满足两方面的要件,一是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之前确实不知晓拍品有瑕疵,二是在整个拍卖过程中,拍卖人本着诚实信用原则严格依照《拍卖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拍卖活动、履行了相应义务。
本案中,从苏小罗提供的证据及本案中各项证据链来看,并无证据显示翰海公司或萧大元在本次拍卖前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诉争拍品系伪作,即本案无充足证据证实委托人及拍卖人在拍卖前确实知晓或应当知晓拍卖标的物存在瑕疵。
从拍卖程序是否正当的角度来看,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本次拍卖活动的程序本身均无异议,可以确定翰海公司在就真伪瑕疵作出免责声明的同时,亦按照《拍卖法》的相关规定为作为竞买人之一的苏小罗行使查验标的物等权利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条件。
另外,本案中瀚海公司作为拍卖人并没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对拍品做出虚假描述或虚假宣传。翰海公司在拍卖过程中,对诉争拍品进行了一些以真实性为基础的文字描述。从这些文字描述本身内容的正常理解看,并没有否定瀚海公司在业务规则中做出的免责声明,也没有对诉争拍品作出真确性保证的含义。
在不能证实翰海公司事前知道诉争拍品系伪作的前提下,翰海公司基于受委托关系在拍卖过程中对诉争拍品适当地加以真确性描述,属于正常的交易活动范畴,其描述用语本身并无过分夸大诉争拍品真确性之处,因此这种描述本身尚不足以构成虚假宣传。
综上,瀚海公司作为拍卖人在案涉整个拍卖过程中体现出的行为特征已经满足《拍卖法》第六十一条关于瑕疵担保责任免除的要件,在无证据证明翰海公司或萧大元在本次拍卖前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诉争拍品系伪作的前提下,可以免除他们对拍卖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三、拍卖人做出免责声明的效力
本案涉及的拍卖活动进行过程中,瀚海公司在拍卖会前发布的《拍卖图录》中明确刊印了《业务规则》,并于该业务规则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及第四十九条明确做出了免责声明。另外,在拍卖前瀚海公司还与苏小罗签署了《竞投登记单》,以确定翰海公司在本次拍卖前已经就诉争拍品的真伪瑕疵作出了免责声明。
类似的免责声明在各类拍卖活动中作为一种交易惯例或行业惯例而普遍存在,这类条款或声明是否因其构成《合同法》上的格式条款而绝对无效,我们认为该类声明的效力还是要依据《拍卖法》的相关规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该声明以及拍卖人的实际行为能够符合《拍卖法》关于瑕疵担保责任免除的要件规定,即可认定此类免责声明有效。
本案中,翰海公司在业务规则中制定的对拍品真伪瑕疵的免责声明,虽然系单方预先拟定且事先未与竞买人协商的格式条款,但该免责声明系基于前述之《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具备法律根据,并为苏小罗在参与竞买前已经应当能够知晓并且理解。且如前所述,在整个拍卖交易中,翰海公司作为拍卖人虽然有权就诉争拍品的真伪瑕疵作出免责声明,但同时应当履行《拍卖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等规定,对拍品进行公开展示并为保障竞买人及买受人全面了解拍品现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
此外,在业务规则中,虽然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及第四十九条中规定了真伪瑕疵的免责,但第二十二条又规定一定条件下买受人有权选择撤销交易。因此,无论就本次拍卖翰海公司所制定的业务规则整体内容而言,还是就本次拍卖活动中苏小罗作为竞买人及最终买受人所享有并能够实际行使的权利而言,翰海公司针对拍品真伪瑕疵所作出的免责声明并不存在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故该条款应属合理,不因其系格式条款而无效。
综上所述,在不能证实翰海公司及萧大元事先应知晓诉争拍品系伪作的情况下,翰海公司在本次拍卖交易中就诉争拍品的真伪瑕疵作出苏小罗应当知晓的免责声明,并通过法律规定的拍卖展示程序有效保障了苏小罗能够在竞买前充分了解诉争拍品的现实状况,且在对诉争拍品的介绍中亦未采用足以推翻免责声明的真确性描述或虚假宣传,故本案中翰海公司针对诉争拍品真伪瑕疵所作出的免责声明应当具备我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效力。
而苏小罗在知晓该免责声明并且在竞买前能够充分了解诉争拍品实际状况的情况下,参与竞买并因最高叫价而成为诉争拍品的最终买受人,系其自主决定参与拍卖交易并自主作出选择所产生的结果,固然有可能因诉争拍品系伪作而遭受损失,但亦属艺术品拍卖所特有之现实正常交易风险,苏小罗在作出竞买选择之时亦应同时承担此种风险。所以,本案一审判决驳回苏小罗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亦判决维持。
艺法观点
法院认为,艺术品的真实性鉴定工作在实践中都更多地依赖于鉴定者的个人经验和感受,目前也没有法律强制规定的审核方法和市场经营自发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的鉴定标准。如果对真实性不能形成合法有效和准确的鉴定,则人民法院审理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或者案件指向的标的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就必然存在证明不能的可能,因此,在这样的案件中就更依靠于由其他证据组成的完整证据链,来综合证明当事人的诉求和主张。
从本案法院的立场可以看出,一方面对委托拍卖人或者画作的原持有人,在没有确实充分和相反的证据证明其对画作的来源明知存在赝品而进行售卖的,其作为合法所有人的事实可以得到确认。
在本案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一张由萧大元提供的伪造明信片,用以证明其存在故意的伪造和虚假陈述的情形,但法院认为仅以明信片无法证明画作持有人刻意证明拍品真实性的事实。这可以明显看出法院主要是以证据强弱来进行裁判,对当事人是否对画作来源有明确认知,以及对于赝品的流转是否存在主观伪造故意的判断,更倾向于支持和保护画作持有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就拍卖公司免责声明的效力,法院认为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拍卖公司应负有对拍品进行鉴定的责任,而且由拍卖公司对拍品进行鉴定,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拍卖公司履行了公告、展示、告知的义务,其宣传属于正常的商业运作,相关提供的内容是属于对拍品介绍的正常描述范畴,未发现有主观上的夸大、诱导成分,同时竞拍人在竞拍前已确认了解了拍卖公司的不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以及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业务规则,因此通过拍卖合同购买画作的合同关系真实有效,竞拍人应当自行承担拍品存在瑕疵的风险。
可以看出,在对于艺术品流转中因赝品买卖而发生的争议,主张权利的一方,必须提供完整的证据链和拥有强大的证明能力,作为维护权益最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支撑,否则即使画作被画家本人确定为赝品,仍然只能自吞苦果,承担损失和不利的诉讼后果。
参考资料:
一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初字第9088号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3093号判决书。
本文中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