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背叛者》:美國拉美裔緣何倒向極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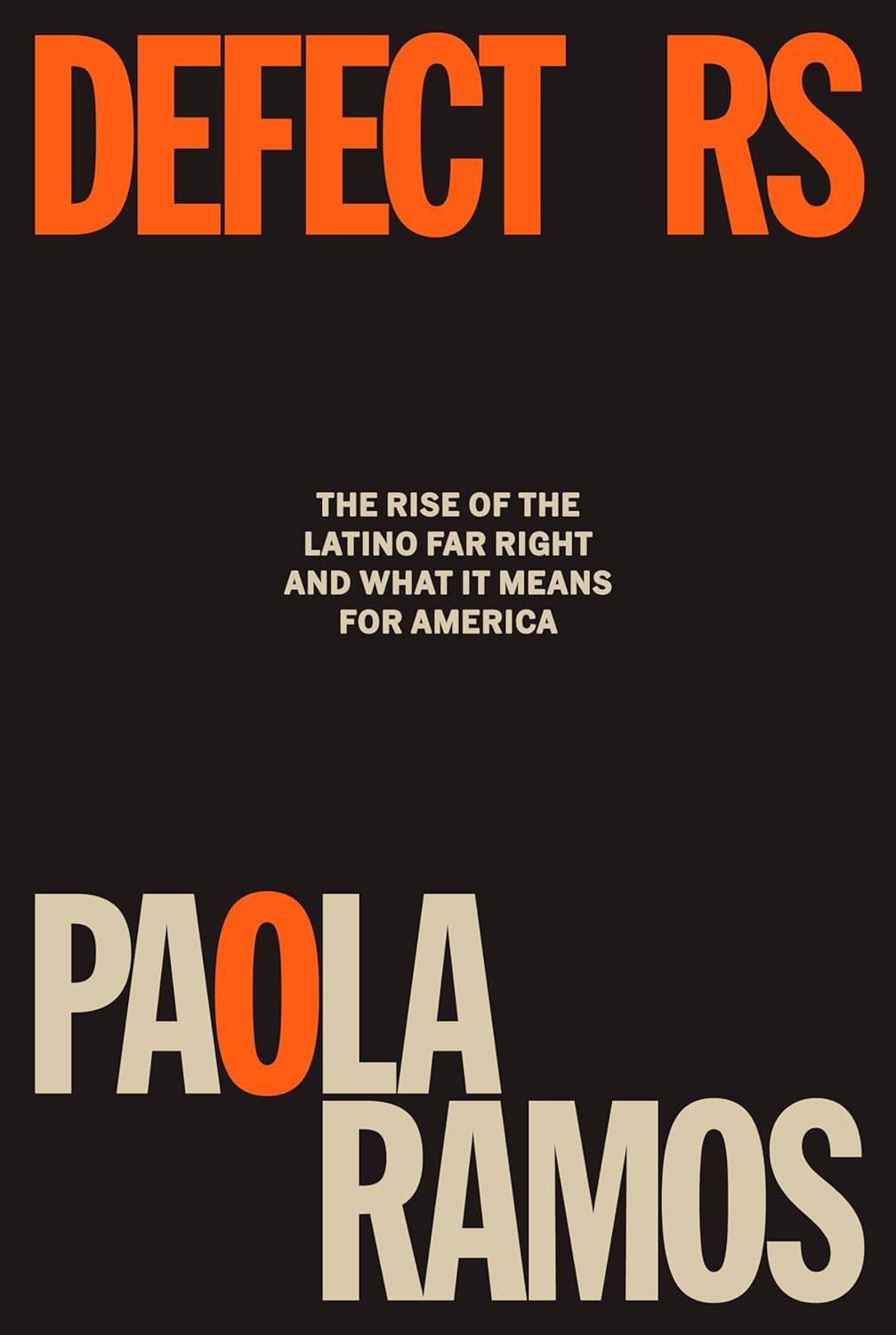
參考消息網10月17日報道美國《紐約時報》網站近日刊發題為《為什麼極右翼勢力在拉美裔美國人中能獲得支持?》的文章,作者是該報非小說類書評家珍妮弗·紹洛伊。全文摘編如下:
對於某些觀察人士來說,2020年大選中唐納德·特朗普在拉美裔選民中所獲得的支持說不通。特朗普難道不是在反覆談論在南部邊界修建「偉大的邊界牆」嗎?難道他沒有把墨西哥人稱為「強姦犯」、把移民稱作「動物」嗎?2020年,大多數拉美裔選民仍然支持民主黨,他們大多投票支持拜登,但特朗普仍令人吃驚地獲得一些有意義的支持,特別是在邊境州,以94%人口為西裔的德克薩斯州扎塔塔縣為例:特朗普成功地使其翻紅(指轉而投票支持共和黨——本網注)。
受三種因素驅動
記者葆拉·拉莫斯便是對此感到震驚的人之一。她適時推出的新書《背叛者》探討了拉美裔極右翼勢力的崛起。她解釋說,這場運動並不局限於痴迷於其歐洲血統的拉美裔白人;她還採訪了像極右組織「驕傲男孩」前領導人恩里克·塔里奧這樣的有非洲血統的拉美裔。塔里奧因參與組織1月6日襲擊國會大廈事件而被判22年監禁。拉莫斯寫道:「很顯然,拉美裔也可以成為白人至上主義者。」但同拉莫斯書中的其他一些極端人士一樣,塔里奧堅稱這是不可能的。他曾經說:「我的皮膚顏色很深,我是古巴人。白人至上主義者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拉莫斯把這種否認稱為「拉美的種族舞蹈」,稱這是利用「我們混雜的出身來掩蓋我們自己的種族主義」。拉莫斯說自己是一個有著淺色皮膚的拉美裔女同性戀者,母親是古巴裔,父親是墨西哥裔。她寫道,在成長過程中,「我崇拜我的西班牙血統留給我的白皙皮膚,同時有意抹去我所在社群的原住民過去」。現在,曾擔任維斯新聞節目記者、微軟—全國廣播公司撰稿人的拉莫斯是一個狂熱的自由主義者。《背叛者》一書顯然是一部以她的進步人士同僚為目標受眾的遊說性新聞作品,她的這些同僚長期以來認為民主黨可以把拉美裔選民(古巴裔美國人除外)視為理所當然的支持者。
她認為,有三種因素使得一些拉美裔美國人被極右翼極端主義所吸引,即「部落主義」「傳統主義」和「創傷」。部落主義表現為內在的種族主義和極度的歸屬渴望感。傳統主義指的是保守的基督教信仰和嚴格的性別行為規範。創傷來自以暴力動盪和由強人統治為標誌的那些國家的過去。她說,這三個因素都源自殖民歷史,這一歷史始於西班牙征服者,並在冷戰期間由於美國的干涉得以持續。
在受害與施害之間
拉莫斯在書中描述了她對一些與她持不同政見人士的尖銳採訪,儘管有些人精明地「給出所有正確回答」。她與一位保守的福音派牧師交談,牧師的會眾就站在附近,身穿印有「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本網注)字樣的T恤衫,把玩著帶套的槍枝。她承認,在剛遇到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古巴裔美國人加夫列爾·加西亞時她有些害怕。加西亞直播了他參與1月6日襲擊事件的過程。但拉莫斯對加西亞在一對一訪談時所表現出來的「膽小、緊張和極度煩躁」深感震驚。塔里奧私下裡似乎也表現得比他在公開場合魯莽的誇誇其談更冷靜、更深思熟慮。
拉莫斯明確表示,無論她的採訪對象動機如何,都不能為仇恨行為開脫。不過,有時她把採訪對象描繪成簡單的受害者。在拉莫斯的講述中,拉美裔被「裹挾著吸收」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本質,其「核心信條」被「刻」進「我們的心理意識之中」;他們「獨特的背景迫使他們中的許多人接受美國的個人主義,認為他們在與白人、資本主義和基督教相交時必須投票推進自己的特定利益」。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她選擇生硬動詞和寬泛概括的習慣卻會把一種糾結的動態簡化成一個條理清晰的因果故事。
拉莫斯最初問道:「在他們的旅途中,受害者是在什麼時候成為施害者?」這是一個別有用心的提問。正如她在其他場合所提到的,與她交談過的人認為自己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施害者,而是位於兩者之間。
並非「鐵板一塊」
拉莫斯堅持認為,大多數拉美裔美國人認同她的政治立場,她寫道:「我確信,在這個國家的近6400萬拉美裔美國人中,絕大多數人渴望社會公正和平等。作為拉美裔,我們的祖先來到美國的旅途雖各不相同,但都是為獲得更多自由而來。」也許吧。但如此全面的評估與事實不符,正如她後來所說的,「我們是有著複雜、痛苦過去的有缺陷的人」。
《背叛者》一書試圖在兩種相互矛盾的敘事之間穿梭:一種是固執地持樂觀態度,即「隱忍和需要不斷調整的過去,使得拉美裔美國人得以謙卑地放棄一切企圖壓迫和控制的本能」;另一種則是與那些其生活故事表明並非如此的個人的一系列交談。拉莫斯正確地駁斥了拉美裔是「鐵板一塊」的假定。但她卻一直在不斷回到那個大多數拉美裔是一個公正、自由主義的鐵板一塊的群體的願景。
在書的結尾,拉莫斯介紹了一些對右翼感到失望的男性。其中一人是一個名叫勞爾的邊防巡邏員,他2016年投票支持特朗普,但幾年後被解職。勞爾被發現是一名無證移民,小時候被帶到美國。
拉莫斯寫道:「一直以來,他只是體制的傀儡,而不是真正有發言權的人。」毫無疑問,可以輕鬆地認定勞爾「只是」結構性力量的產物,但正如拉莫斯自己肯定知道的那樣,她採訪的每個人都遠不止如此。(編譯/林朝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