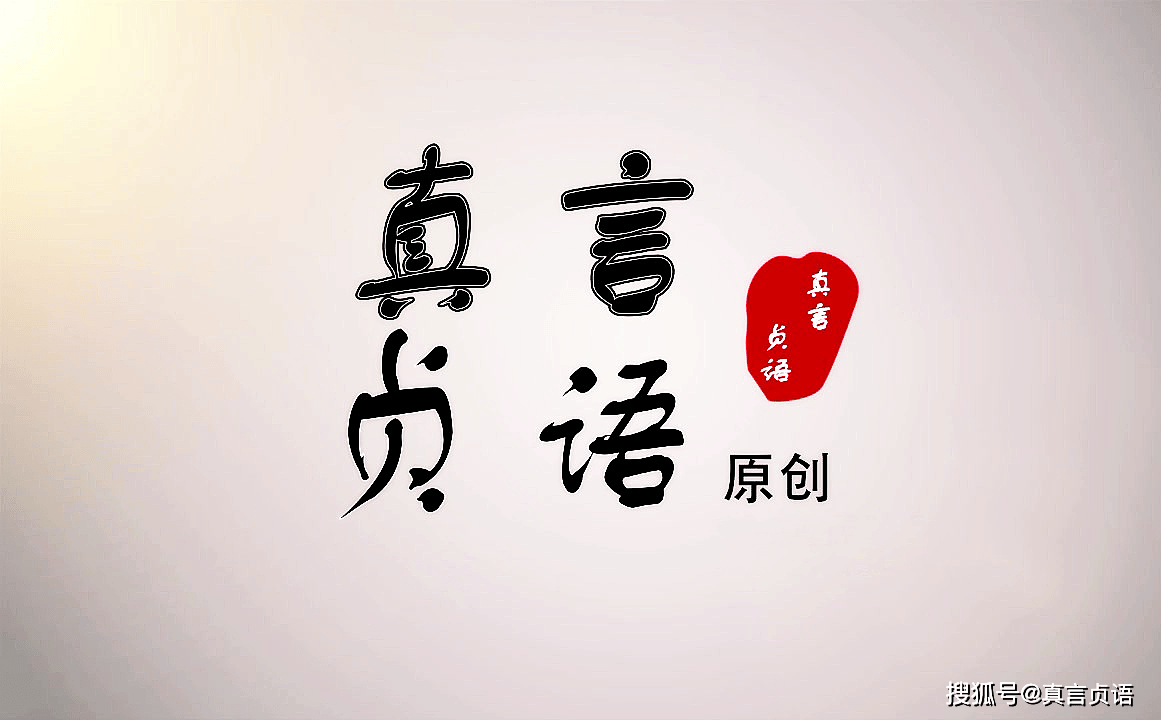
高考:命運分流的時刻
文/周長行
又是高考到來時。
每年每當此時,筆者都要寫點東西,五六年了,概莫能外。
然而,今年就想「例外」一下,不寫了,罷筆,歇歇哩。好朋友們也來湊熱鬧,竟然打賭道:你若果真不寫,我們請你吃大餐!(事後猜思,這是激將法也未可知)
不寫有何難?離開誰,地球照轉。何況一兩篇破文章,不寫又咋地!
於是,我既做好了堅決不寫的心理準備,也做了一點所謂的「鋪墊」和輿論,試試量量在圈裡轉發了往年寫的兩篇東西,算是以逸待勞,給天天等著我的讀者朋友一個不痛不癢的交代。
一篇是《我的高考記憶》,六十年前我考初中時的點滴回憶。一篇是《家長靈魂跟進考場》,無數家長站在考場外「陪考」,一篇觀察記,重點是寫家長靈魂的「站立」。這兩篇東西在百度上都能找到,縱橫都是說高考。
之所以重新轉發,我也是為了素素靜靜地避開今年的高考,不寫,不說,不激動,卻又重提高考相關的內容,掩人耳目的「小動作」,多少有點兒「糊弄」的味道,免得引起反彈。不然,就會有人咋咋呼呼地打電話囉囉我:嗷呦,老周,什麼情況?正好好的,怎麼不寫啦!
然而,「聰明」反被「聰明誤」,小心眼上不了大台面。萬沒想到,自己把自己送進了非寫不可的「泥淖」。
重新露臉的那兩篇東西,竟引發一石激起千層浪的「騷動」。閱讀者、點贊者和評論者比當時發表時還多,特別是評論者的態度和話語,讓我激動、感動,「拍案而起」的那股子衝動勁兒,也就是說「老毛病」發作,不說不寫點什麼,簡直是「這日子沒法過了」。
猶如一場遭遇,躲不開,就得直面上去。
事情出在三條評論上。
第一條是一位叫@自強不息的所謂網友,其實是我們一個村莊的弟兄,他在《我的高考記憶》的留言處寫道:寫的太真實了,沒有切身體會是寫不出這樣真實的好文章,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歷與現在的高考無法論比,一去不復返了!
這條評論,弄得我很難受,不由得想起當年考學的種種經歷,種種體會,與現在的高考相比之後的種種感慨。我那時考學,有兩大目的堅不可摧:一是為了逃離苦不堪言的農村;二是為了吃上供應糧。就這兩條相當明確。別的也想不到。一個只有12歲的孩子,哪能想那麼多。
第二條是一位叫@妙妙的網友,我猜測是一位女士,有可能是一位飽經滄桑的老年女士。她說她「拜讀」了我的大作。她說她哭了,哭得很傷心。她說,不管如何努力,人得靠命運。不管是高考,還是中考,都是人生命運的分流。
啊,人生命運的分流。
這話震撼了我,也震醒了我。社會紛紛議論的中考遺留問題,一半孩子按指標可以讀高中,一半孩子只好接受「分流」的命運,去讀職業學校,去讀「野雞」學校,大部分再無「大學緣」,一部分過早地走向社會,在撲朔迷離的命運波濤中任其顛簸。高考也是命運的分流。
在命運面前,請允我斗膽說一句:我們都是羔羊!
第三條是一位叫@姜承和的網友,是我地地道道的戰友,網上網下都叫「姜承和」,切切實實的「實名制」。他的留言短小,卻觸動了我那顆「不安分」的心。他寫道:無論你要維護什麼,你都需要力量,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依然保護不了你想保護的人。記住這個感受,然後拚命變成有力量的人。這話讓我唏噓不已。
我曾經認為自己是有點兒力量的人。但,在面對高考、中考這場命運「大決戰」的時候,我才頓然感到,我麼力量都沒有。我仍然在「我是誰?」的問題上,一文不值。
莫說是我,堂堂的教育部,面對人大代表提出的中考「分流」的問題,又有怎樣的作為呢?
畢竟我是沒有力量的人,說也白說,寫也白寫,但是 ,我還是拗不過自己的老毛病,寫寫吧。因為,命運的分流,無情無奈,也無解,讓我心痛!
寫作本就是自我「療愈」,僅此篇而言,應該是自我安慰吧。
(寫於6月6日高考的前夕)

【作者簡介】周長行(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高級記者、詩人。著有長篇紀實文學《鵾鵬騰飛的地方》《大山的呼喚》《大京九解說詞》《趙忠祥寫真》《喬羽戀歌》《不醉不說喬羽的大河之戀》《大國詞人喬羽傳》《偉大的我們》《大浪淘金》;中篇報告文學《岩石歲月》《悠悠玉蘭情》《巷道雪洞》。詩集《句子的隊伍》。作品曾獲《解放軍文藝》大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