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亲属关系-收养制度,谈元代收养制度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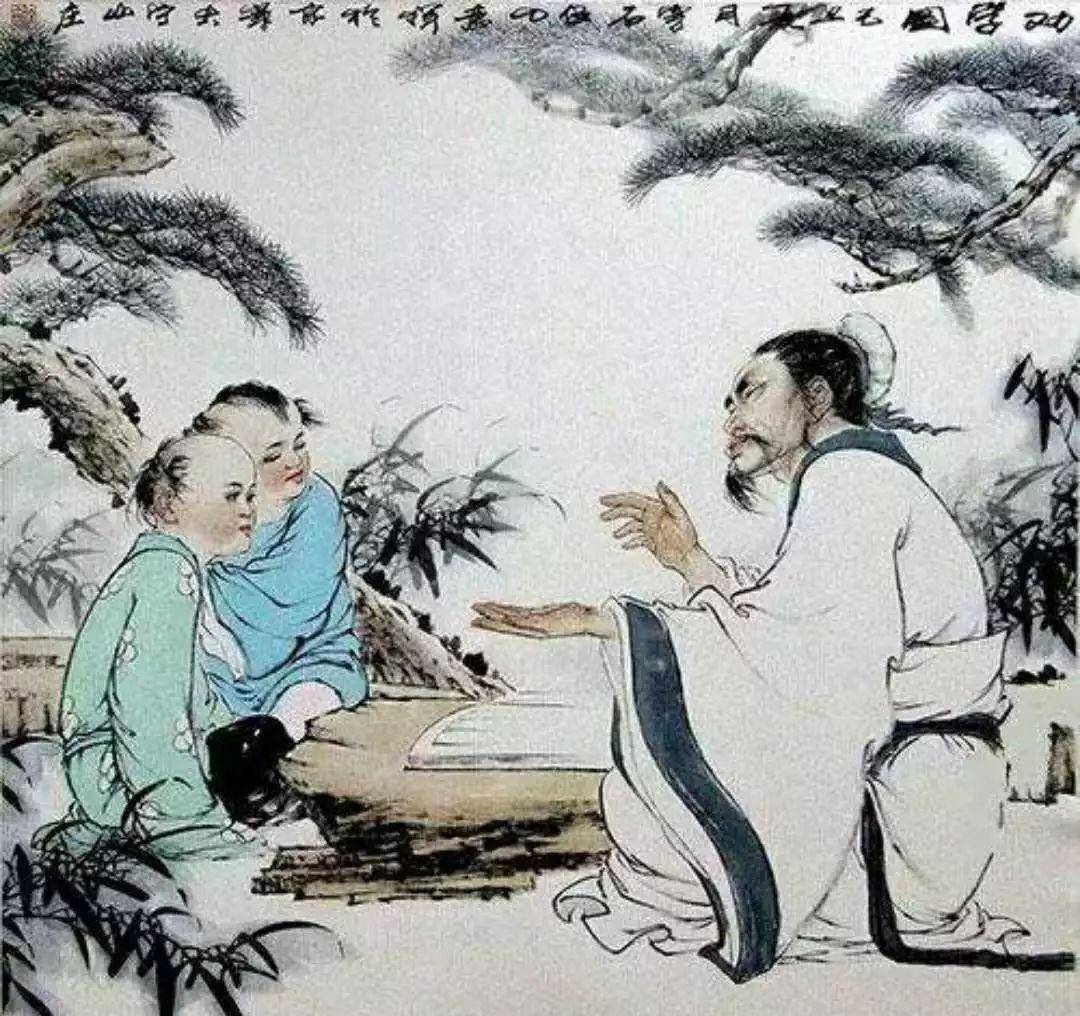
收养制度,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殊亲属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此基础上,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构成拟制亲属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收养制度主要是基于家本位、族本位和父系本位而产生,故其目的、范围与基本原则等称与现代收养制度迥异。进入元朝,鉴于当时民间收养关系所发生的一系列与传统礼教严重不符的情况,元朝政府曾经相维出台了一些针对收养制度的法律规定,从而对被收养人、收养人、送养人、以及收养行为的程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限制,但这些规定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民间流行的收养方式。
一、古代社会的收养制度
1、收养规则
中国古代社会的收养,主要是出于立嗣的考虑。传统礼教非常注重立嗣,在宗祧继承制度下,对于无子者,往往须立他人之子为“嗣子”, 以传宗继祀。这决定了其收养对象主要以男性为主。此外,传统礼教在收养关系方面一直遵循着“异姓不养”的原则,该原则在历代王朝的立法实践中被普遍采用。
当然,对于立嗣以外的收养关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也不是完全禁止的。这主要是基于儒家的仁本思想,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另外,因为女性不能传宗接嗣,对宗祧制度不构成威胁,故而法律对收养女性没有限制。不过,社会生活纷纭复杂,中国历代王朝包括元代的民间收养实际上往往突破传统礼法所设置的种种框架。且法律与社会实际之间的冲突叉集中体现在收养男性方面。

2、元代收养情况
元代基于立嗣目的的收养,除了遵循传统礼教所规定的同宗昭穆相当原则之外,实际上始终存在着其他情况,且为数不少。进入成宗以后,元代收养制度的法律规定开始放宽,更加助长了这种凤气,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使元朝政府困扰的社会问题。
二、元代收养制度的规定及其发辗变化
元朝的收养制度,直接继承于金朝,金朝法律规定:
“诸人无子,听养同宗昭穆相当者为子。如无,听养同姓。皆经本属官司告给公据,于各户籍内一附一除。养异姓子者有罪”。
也就是说,如果同宗没有合适人选的话,也可以过继同姓之人为子,同唐、宋法律相比,该规定所允许的收养范围显然有所扩大。但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像在收养制度方面与唐朝有着相同原则规定的南宋王朝,实际上已经存在大量收养异姓子的例子。面对这些与法律原则冲突的情况,元朝先后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以对民间收养行为进行限制。
1、对被收养人资格的限制
即禁止收养异姓为子。 被收养人的资格顺序为“听养同宗昭穆相当者为子。如无,听养同姓”。元朝初年继承了金朝的法律制度,故也作出了此类规定,但该项规定被以后的判例所推翻。像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的一件案例,大致是萧千八生前立异性嗣子谢颜孙为嗣,改名萧九福,死后伯母萧阿谢状告其私立为嗣。但官府却确认萧福九(谢颜孙)的养子身份有效。

而且从大德四年的另外两件类似案例来看,实际上对于那些事实上已经过继收养,并已经登记近官府户籍者,虽然过继收养的是异姓子,官府也承认其合法有效。有资格过继者,即所消同宗昭穆相当之人不得以过继非法为理由,向官府要求承继门户。从《通制条格》卷四《户令过房男女》中已无关于被收养人资格的限制,以及《元史》卷《刑法志二户婚》“诸乞养过房男女者,听”的规定来看,至少自元朝中期开始,在立法中已经取消了禁养异姓子的限制性规定。
2、对收养人资格的限制
即“年及四十、无子之人,方听养子”,“不得年小预先抱子”。收养人必须年龄超过四十岁的规定,仅见于元朝。但由于该法律文书只是江浙行省的谕文,且在《通制条格》与《元史刑法志》中并无类似规定,所以认为这恐怕只是当时江浙行省的权宜规定,并不通行于全国。此外,驱口过房良民由于会导致养子良民身份发生实质性改变,元代法律也是严格禁止的。
3、对送养人资格的限制
元朝把送养人的资格仅限定在父母范围之内。在大德三年的一件案例中,御史台议得:“民间风俗浇薄,昆弟不睦,比比有之。且兄弟同气比肩,共有财分之人,与父母尊卑不侔。又兼止有许准父母将亲生男女乞养过房体例,别无兄得过房弟妹明文,若令兄将弟妹过房与人,以为通例,其间有争分家财,或因妯娌不睦,便将弟妹过房与人,弃绝大义”。
意思就是为了防止兄弟妯娌之间为争夺家产不和睦,就恶意卖了自家的亲戚儿童。这一建议,得到了中书省的批准,并载于《通制条格户令过房男女》与《元史刑法志》中,显然是通行于全国的法律规定。
4、规定收养行为成立的程序要件
江浙行省的谕文在规定收养行为时,曾要求“明立文字,两家并说合俱各画字,仍须经官告给公据"。虽然这一规定在《通制条格》中没有记载,似乎没有升格为全国性的法律规定,但社会生活实践中往往有这样的做法。
《新编事文类要启礼青钱》外集卷一保存有双方当事人所立文书的格式,一式两份,由养子的养父母与本生父母分别保存。一份是觅子书式,大致意思是说自己没有子嗣,遂托得某人为媒,因而收养一个孩子以为嗣续,且某如同嫡子看承,不敢嫌弃,幼训以诗书,长教其手艺。如违此约,甘罚中统钞若干贯文入官公用。

另一份是弃子书式。大致意思是自己与妻子生下的男子过多,被生活所添累,所以自愿将自己的一个孩子交给他人收养,且无退悔之心,向后长成,亦无鼓诱归宗之意。如违此约,甘罚钞若干贯文入官公用。而且,从“如违此约,甘罚钞若干贯文入官公用”来看,此类契约要由官府监督执行,如有一方违反契约,所罚款项即被充官使用。文书交由官府受理,经调查属实后,即给双方当事人发给公据,给被收养人重新过户,将其从本生父母户头下转入养父母户头下。至此,收养关系始产生法律效力。
5、元代收养关系的解除
在特定情况下,收养关系是可以解除的。收养关系的解除,按照传统惯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协议解除,一种是强制解除。前者是指由于养子的养父母又生有子女等原因,而与本生父母协商,双方协议解除养子与养父母关系的场合。《唐律》疏义曰:“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元朝法律对此虽未作出规定,但此类情况在元朝实际上很多,像“辰之沅陵民文甲无子,育其甥雷己,后乃生两子而出乙”。
后者是指经官府判决,强制解除养父母与养子的关系。这种情形一般发生在养子不孝,败坏家产,以及养父母虐待养子,告官审理的场合。《元典章》中记载有三宗涉及因养父虐待养子而被官府强行解除父子关系的案例,在这三宗案例中,官府的处理结果都是断令养子归宗,对于后果严重的,不但“人价不追”,有的还要追加经济赔偿。此外,如果违反法律对收养关系要件的规定,当然也会发生被官府强制解除的结果。
三、元代养子的权利义务
1、养子权利地位
养子,如果是因为无嗣而过房承维门户,即为立嗣性质的话,他们在财产继承等权利方面无疑等同于亲子,即遵循所谓的“继绝亦同”原则。这可以说是养子的基本法律地位。但如前所述,立嗣可以分为生前立嗣与死后立嗣两种情况。死后立嗣自然是由于没有继承人所致,因而没有纠纷。重点在于生前立嗣。
生前立嗣常常出现养父在立嗣以后又生有亲子的情况,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养子与亲子在财产继承方面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如果养子不归宗的话,一般要保护养子的继承权利,其应得财产的份额,在元代司法实践中,一般按照亲子中的庶生子处理。元朝对诸子间的财产分配原则为“妻之子各肆分,妾之子各叁分,奸良人及幸婢子各壹分”。养子参与财产分配,即参照此原则进行处理。

2、养子所应尽的义务
养子过维之后,与养父母结成拟制中的父子、母子关系,其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亦随之转移,但他同本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没有完全消灭,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实际形成双重亲属关系。拿服制问题来说,按中国传统礼制,养子一旦过房之后,其服制关系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他要同亲子一样,为养父母服斩衰三年,但对于自己的本生父母,他也要遵循“不贰斩”的原则,需服齐衰期年。元朝与此原则相同
四、元代收养体制的不利影响
元朝收养制度的不健全,即从元朝初年的养“同宗昭穆相当者”及“同姓”,转变为以后的“乞养过房男女者听”。此项重大变化,使当时社会上收养关系的复杂现象得以加剧,从而也造成了一些比较棘手的社会问题。像当时有许多人以已子过房他人,主要是为了贪图他人的钱财,“今世以田宅、财物争为后",而收养关系的多样化,使这一问题趋于复杂,相关的民事财产纠纷层出不穷。
1、养子养女遭受折磨
在实际生活中,养子与养女倍受领养人摧残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元典章》中记载了三宗与虑待养子有关的案件,其中有一宗案件的当事人,为了自己升官发财,竟然将自己的养子“亲手用刀,割囊去肾,欲作行求之物"。有许多养女,则被逼良为娼,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为生,“又有典买良妇,养为义女,三四群聚,扇诱客官,日饮夜宿,自异娼户,名曰‘坐子人家’”。
2、人口贩卖问题严重
人口贩卖为元代的一大社会问题,此风当时极为盛行。虽然人口贩卖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元代的收养政策的放任,无疑为其提供了便利途径。成为这一现象泛滥的催化剂。许多人口贩子往往钻收养制度的空子,规避法律规定,假借收养行为而行人口贩卖之实,当时“虽有抑良买休之条例,而转卖者则易其名曰‘过房’, 实为驱口”。这种情况在江南地区尤其普遍,“中原江南州郡,近年以来,良家子女,假以乞养过房为名,恃有通例,公然辗转贩卖,致使往往陷为驱奴”。

五、总结
纵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同前朝相比,元朝对社会生活中的收养关系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比较放任的态度,各种类型的收养关系大量公开存在,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元代收养制度的本身不完善无疑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为人口贩卖创造了一定条件,对后者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元代收养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