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到7日,第十二屆世界和平論壇在北京舉行。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是6日到7日舉行的三場大會討論的主持人。此外,在7日上午的大會之前,他特別參加了一場小組討論並致辭。這場討論的主題是「在武裝衝突中遵守人道規範」。
2023年10月新一輪加沙危機爆發以來,閻學通多次強調,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趨勢已經從經濟領域蔓延到政治領域,以色列軍隊在加薩走廊大規模違反戰爭法的行為,就是一個例證。「不論是看國家數量還是人口數量,絕大多數國家或民眾都是反對以色列的行為的。」7月6日下午,閻學通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指出,「問題是,基數大並不意味著反對者有能力阻止以色列政府的行為。目前來看,也還沒有國家有能力阻止美國為以色列提供軍事裝備。」
在7日上午的大會討論中,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美國國務院前亞太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學術主任科爾圖諾夫、法國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所創始所長博尼法斯共議「展現大國維護和平與安全的責任擔當」。面對逆全球化加速、衝突局勢加劇的現狀,「大國責任」是這屆世界和平論壇的熱點話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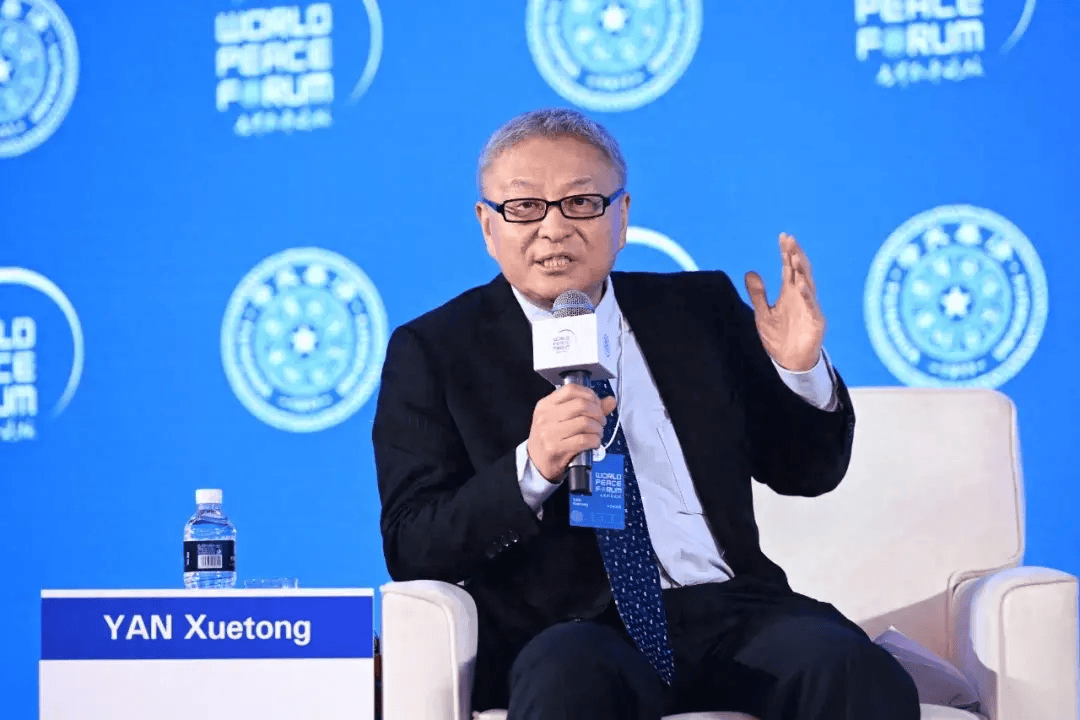
閻學通在第十二屆世界和平論壇上。圖/世界和平論壇
逆全球化的深層原因是價值觀變化
中國新聞周刊:近年來,國際社會關於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討論越來越多。你最近也多次從西方「自由市場倒退」和「人權倒退」兩個角度闡述逆全球化趨勢,其典型事例分別是「脫鉤斷鏈」和加薩走廊的人道危機。但對這個議題,歐美西方世界內部也還存在比較大的爭議。我們應當如何理解當前逆全球化趨勢的嚴峻程度?
閻學通:首先,我們要區分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這三個概念。反全球化是一種民眾層面的行為,一些人認為全球化使得社會兩極分化,反對富人更富、窮人更窮或窮人不受益。反全球化的代表性運動是「占領華爾街」,這顯然沒有成功。為什麼?因為這是一個不掌握權力的大眾群體。去全球化是一種政府政策,即政府利用手中的國家主權,減少國際社會交流交往和各類合作。逆全球化指的是和冷戰後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相反的潮流。
目前,逆全球化的趨勢逐漸嚴重。從2018年前後開始,逆全球化主要是經濟領域的倒退,比如「脫鉤斷鏈」和貿易保護主義,這使得經濟、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有效配置無法實現。
但是,2023年10月新一輪加沙危機爆發後,逆全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在政治領域。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占領、對巴勒斯坦人的鎮壓,是長期存在的現象。但過去的行為沒有像現在這樣在短期內這麼大規模、這麼集中地剝奪加沙地區的平民人權。戰爭法明確規定,不得強迫遷徙或驅逐衝突地區的平民,而以色列軍方公開要求加沙城超過150萬民眾離開家園。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冷戰後的幾十年里,這樣大規模的違反人權的行為,還是很少有的。
冷戰後的政治民主化,在國際層面,主要就體現在對人權的重視。總體上,各國對於人權和人道規則的尊重程度是在上升的。國際社會就此達成了基本共識。但現在,最基本的人道主義規則也不再得到尊重和執行。而且,這些當下反對將加薩走廊平民人權放在首位的政府,不是發展中國家政府,而是一些西方國家政府。當然,這不是全部西方國家,但至少有一部分西方國家目前依然在支持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戰爭中違反國際法、違反人權的行為。
中國新聞周刊:就像你提到的,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也反對以色列政府的行動。這種情況下,逆全球化趨勢是否會因為國際社會對於加沙危機這一災難性事件的強烈反應而得到遏制,還是說仍將加劇?
閻學通:首先,歐洲國家內部,不同的政府對待加沙問題的立場是不一樣的。例如愛爾蘭、比利時、西班牙等國家的政府,從一開始就反對以色列違反人權的行為。還有一些國家,比如英國曾持續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出口,英國和德國直到最近才開始調整其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
如果從全球範圍看,不論是看國家數量還是人口數量,絕大多數國家或民眾是反對以色列的行為的,包括50多個伊斯蘭國家、占全球人口約四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口。不過,基數大並不意味著反對者有能力阻止這種行為的發生。目前來看,還沒有國家有能力阻止美國政府為以色列提供軍事裝備。而美國政府缺乏扭轉以色列軍事行為的動因,也無意改變逆全球化趨勢。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麼誰也改變不了逆全球化趨勢,是因為大國競爭在加劇嗎?
閻學通:可以說是大國競爭導致逆全球化的加劇,也可以說是全球化的倒退加劇了大國間的競爭。我認為,大國競爭只是逆全球化所產生的一個現象,逆全球化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價值觀的變化,即西方社會的民粹主義壓倒了自由主義,經濟上的貿易保護主義、政治上的孤立主義政策取代了自由主義推動的全球化政策。
進一步說,一種新價值觀興起,在一個歷史時期能夠被很多人接受,一定是因為有很多人對當前生活及社會現象感到不滿。民粹主義價值觀對社會問題給出了一種解釋,而這種解釋恰符合很多人的認知。比如在不少國家,包括一些西方國家,現在很多人認為自己國家裡的所有社會矛盾和經濟問題都是外部因素導致的,於是出現仇外、恐外的心理。民粹主義提倡減少同外部的往來,保護國內市場,把外部影響全部切斷,這被很多人認為是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
中國新聞周刊:最近歐洲部分國家也出現了一些「左翼回潮」的現象。一位英國工黨高層人士對我說,這說明當民眾發現右翼政府的這一套保護主義政策也不能改善生活時,民眾還是會回歸理性。你同意這種判斷嗎?
閻學通:我覺得不一定。歐洲社會公眾轉向何方,我不知道,他們有可能轉向其他的政治思潮、其他的右翼思想,不必然回歸自由主義。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很多歐洲人認為此前的自由主義政策是錯誤的,必須更換。至於更換後的政策有沒有效果,那是另一回事。但自由主義的這套理念,他們已經「不想再聊了」。

閻學通、李君如、董雲裳、科爾圖諾夫、博尼法斯(從左至右)在世界和平論壇上。
數字化時代國際競爭的核心是技術創新
中國新聞周刊:聽起來,逆全球化趨勢將是一個長期過程,現在也有觀點認為世界已經「回到冷戰」。能進行這樣的歷史對比嗎?歷史上的逆全球化進程存在規律性嗎?
閻學通:將當下的進程和以往歷史事件進行對比不一定是合適的,就像我們今天沒法將二戰和春秋戰國、楚漢相爭進行對比一樣。但從近代以來的情況看,我們可以區分數字化時代的國際政治和非數字化時代國際政治的不同。這兩者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之處是,在數字化時代,國際競爭的核心是技術創新。
比如,從歷史上看,每一次大國競爭的動因是不同的,但性質總是相同的,其本質都是要爭奪權力。動因不同,就是它們爭奪權力的具體內容不同。在農業社會,大國競爭的關鍵動因是占領更多的可以使用的土地。到了海洋擴張時代,大國競爭開始更加關注控制更多的海域、港口、航道。冷戰期間,大國競爭的動因是擴大各自的意識形態影響。進入數字化時代,我認為,大國競爭的關鍵,在轉向爭奪標準制定權,也就是說,要競爭誰的技術標準能成為國際社會通行的標準。美國組建「6G聯盟」的目的,就是如此。
中國新聞周刊:能否說這一輪大國競爭和逆全球化已經遠離了全球性戰爭的風險?如何才能讓各國意識到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閻學通:目前,大國競爭還不至於引發全球性戰爭,主要因素還是核武器。因為大國擔心核戰爭,核戰爭能消滅全人類,使戰爭變得沒有意義、沒有贏家。所以,到目前為止,只要核武器的這種政治功能還存在,避免世界大戰仍然是可能的。
至於其他類型的災難,則取決於大家對於這種災難危害大小的判斷。新冠疫情對全人類構成了共同威脅,但大國間關於全球公共衛生的合作遇到了諸多阻力,這是因為一些國家並不認為新冠會導致人類的滅亡。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就人工智慧全球治理進行合作,核心原因是人們擔心,如果AI統治世界,人類有可能面臨被消滅的風險。
所以,什麼樣的威脅能扭轉大國競爭的態勢,能實質性地推動大國間的進一步合作?一定是可能導致全人類滅絕的威脅。如果這種共同威脅只危及部分人類的生命、不危及全人類的存亡,那麼這種安全威脅促進大國合作的力度可能就不那麼大。
「中等國家」的政治空間會越來越大
中國新聞周刊:俄烏衝突在逆全球化趨勢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對於經歷戰爭後的俄羅斯是否依舊屬於「大國」,外界爭議很多。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俄羅斯在當前大國競爭中所處的位置?
閻學通:首先,俄烏衝突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趨勢。俄烏衝突發生帶來的一個結果,是讓歐洲國家形成了「經濟安全」的強烈概念。當歐洲從「沒有戰爭」走向「發生戰爭」,歐洲的安全秩序就已經改變了。歐洲國家出於對衝突局勢導致產業鏈中斷的恐懼心理,開始大搞「去風險」政策,這會導致更多的產業鏈中斷,進一步推動了逆全球化的發展。
就戰爭本身來說,沒有任何一方通過戰爭使自己變得更強大。參戰各方的絕對實力的增長速度都明顯放緩,沒有一方通過戰爭加快了實力增長。
中國新聞周刊:未來,歐洲還可能形成一個相對共識性的安全秩序嗎?你覺得西方是否依然希望俄羅斯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夥伴,還是說希望它成為「失敗國家」?
閻學通:戰爭的雙方肯定都希望對方失敗,但問題是,現在任何一方有沒有能力讓對方失敗。要是有能力,這個目標早就實現了。戰爭持續到今天已經兩年多了都沒有決出勝負,說明短期內任何一方都沒有取勝的能力。
本屆世界和平論壇上,有不少歐洲代表在發言中談到,歐洲沒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我認為這裡存在一個誤解,就是歐洲並不僅僅在這場戰爭中沒有能力維持自己的安全秩序,冷戰後歐洲一直都沒有維護自己安全的能力。冷戰後,歐洲已經經歷了科索沃戰爭、俄羅斯-喬治亞戰爭、亞美尼亞-亞塞拜然間的兩場納卡戰爭等一系列衝突。現在我們應當意識到,歐洲國家在冷戰後沒有能力維護地區安全,是一個基本事實。作為一個地區組織,歐盟維繫和平的能力遠不如東協。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世界和平論壇期間也多次提到,當年「歐盟是老師,東協是學生」,現在歐洲可能要向亞洲學習一下管控安全風險的經驗。這種「亞洲經驗」到底是什麼?如果真的遇到大國介入的地區衝突局勢,東協真正能做得比歐盟更好嗎?
閻學通: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東協在處理衝突時能不能做得比歐盟更好,而是在於為什麼東協能有如此好的「運氣」,避免大國在東南亞進行戰爭。誰也不可能永遠避免戰爭,但只要這種地區總體和平的局面還能在東南亞持續下去,就值得歐洲羨慕了。
至於東協為何能有這種「運氣」,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話題,很難用幾句話解釋清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如果秉承一種「堅持和平共處,不輕易讓矛盾升級為軍事衝突,不讓已發生的衝突升級為戰爭」的觀念,地區和平就更可能得到維持。
此外,隨著大國競爭的加劇,東協這樣的力量,採取中間、靈活的對外政策和安全戰略的機會是越來越多的。大國競爭越加劇,「中等國家」的國際政治空間就越大,因為大國都需要爭取它們的支持,它們就有更大的機會發揮作用,更多的空間和大國討價還價。
作者:曹然 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