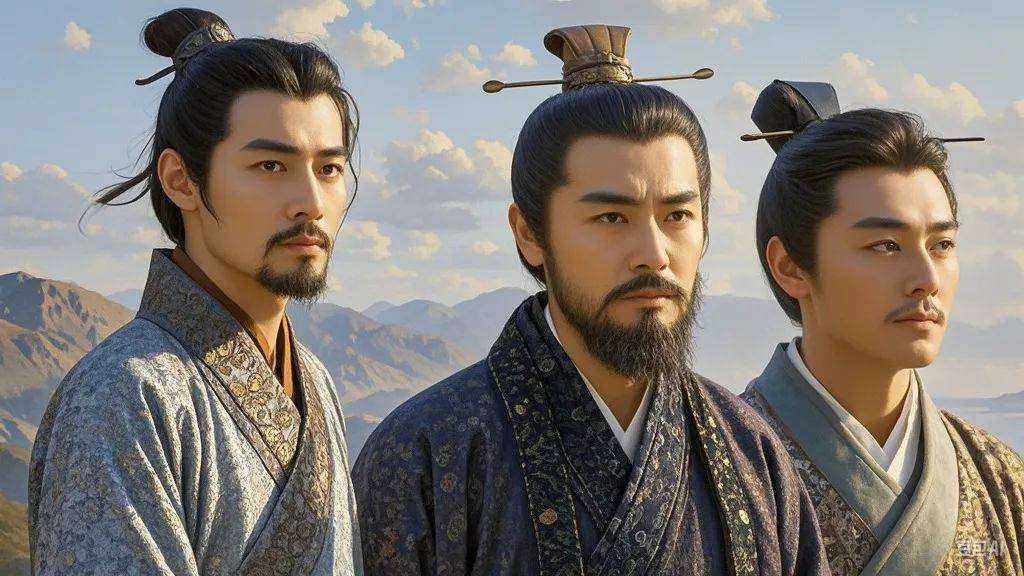
曹操考察曹植及曹丕的情況,備載於曹植本傳注引《世語》,內容包括兩個方面:其一,作教令提問,由曹植作答;其二,令曹丕、曹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吏不讓出城,以考驗兩人的臨機決斷能力。當時,楊修和賈逵、王凌皆任丞相主簿,他們暗中幫助曹植,「豫作答教」,但痕跡太露,被曹操「推問」而泄底;第二項考察也出現了類似情況。其實,優秀的文人學士,並非必然就是志才雙修的政治家,有時甚至相反,曹植即是這樣:他文采橫溢,卻囿於傳統觀念,對漢室心存眷戀;書生氣重,拙於權術矯飾。因此,考察的結果,曹植的政治抱負和才能終究不能令曹操放心。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其他一些因素才顯得重要起來,並影響了立嗣問題的結局。
除前述曹操徵求臣屬的意見外,與之相關,立嗣問題牽涉到一些重要的人事關係,它直接關係到後嗣的地位和權威,甚至更深層次的問題,曹操不能不慎重對待。
支持曹植最得力的丁氏兄弟,是曹操的舊友丁沖之子。丁沖與曹操同籍,曾建議曹操「匡佐」漢獻帝,兩人情誼深厚。丁儀號稱「令士」,丁廙也頗有才學,是「譙沛人」中難得的文官之才,因而受到曹操的培植和寵信。丁氏兄弟對「大魏」的忠心,曹操自然深信不疑。然而,丁儀頗有報復妒忌之性格,他支持曹植而反對曹丕,即因為曹操打算將愛女許配給他,卻被曹丕勸止。據史載,丁儀任西曹掾,曾多次讒間毛玠、徐奕、何夔等;崔琰被殺,毛玠被廢,也是由他密告而引致。這種排斥異己的做法,使丁氏兄弟與眾多臣僚構成了敵對形勢,侍中桓階、和洽、尚書傅巽等都是其反對派。丁氏兄弟入仕較晚,除了仗恃曹操的寵信,本身並無政治根基。若由曹植繼嗣,丁氏兄弟必然充任輔弼,如此怎能保證不出內亂?
曹植的另一個主要支持者楊修,是漢太尉楊彪之子、袁術之甥。楊彪曾構嫌於曹操,時值袁術在淮南稱帝,「操托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楊彪在獄中頗受折辱,但終被放免。後來,他見「漢祚將終」,便採取與曹氏不合作的態度。楊修本人任丞相主簿期間,恃才自負,也頗遭曹操猜忌。《曹植傳》稱:「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裴注引《典略》亦稱:
至二十四年秋,公(曹操)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
綜合兩段記述,楊修的死因可概括為:曹操「慮終始之變」,即顧忌楊修「才策」高深,又是死敵袁氏之甥,深恐後嗣難制而有顛覆之變,因而要置他於死地。這是曹操出於深層考慮而作出的根本決斷。所謂「以罪誅修」,是具體運用手段的方面,即藉口楊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將他誅殺。雖然楊修死於建安二十四年(219)秋,上距曹操正式立嗣已近兩年,但他致死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在立嗣問題上暗中幫助曹植,他臨死前的話即證實了這一點;胡三省稱「以修豫作答教謂之『漏泄』,與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甚是。總之,以楊修的政治背景,他與曹植關係密切,對曹植爭嗣實是一個障礙因素。
進一步考察,我們還可發現,曹植、曹丕在結交政治人物尤其是名士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曹植封平原侯時,曹操選拔邢顒為其家丞,並下令說:「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邢顒是冀州名士,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讓他侍從曹植,就是要讓曹植接受禮法薰陶。然而,曹植與邢顒頗不相合,為此,庶子劉楨特意致書曹植加以勸諫。《晉書》卷三七《司馬孚傳》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也反映出曹植恃才任性,不善結交人物。相比之下,曹丕要高明得多。前面提到的崔琰、涼茂、邴原、程昱等人,曹丕都與之有較好的合作關係,而前三人是享有盛名的大名士。不僅如此,對荀彧、賈詡等關鍵人物,他也加意籠絡。我們不能忽視這種人事關係,因為它實質上是政治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曹操的一生中,充滿著與各種名士的複雜關係,或投靠,或打擊,或聯合,或利用,貫穿著他畢生事業的始終,但總的來說,聯合、利用才是最終目標。以此來衡量曹丕、曹植結交名士的表現,高下立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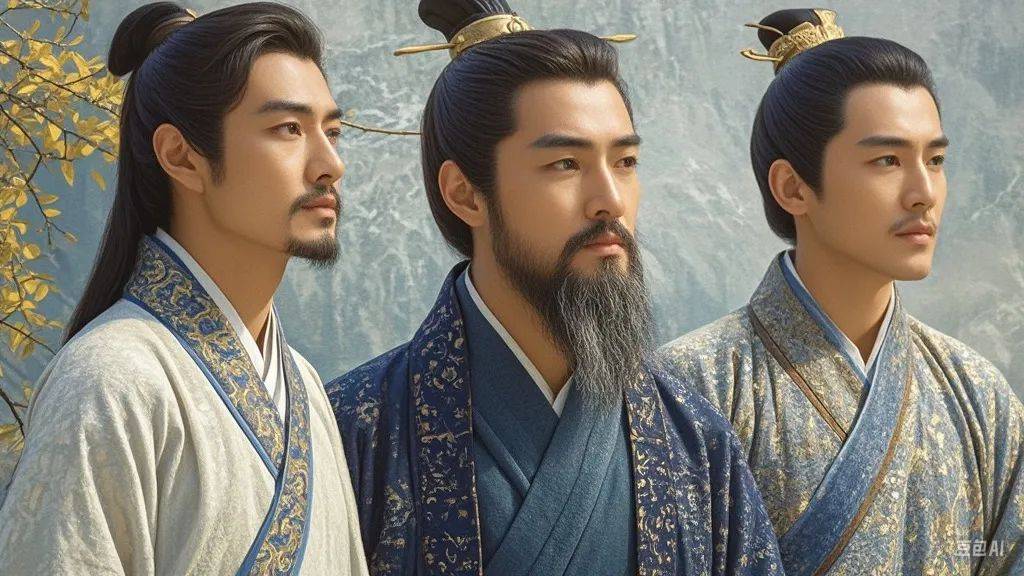
曹操立嗣,是一件最重要的「家事」,因而也充滿了感情因素。這是與「國事」對應的另一個方面。《曹植傳》稱植:「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表明曹植的性情、習尚與曹操相投合,言辭對答也令其愜意,因而深受寵愛。在聯絡父子感情方面,曹植捷足先登。又《賈詡傳》稱:「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賈詡不愧為「論智計者」之宗主,他提出的上述建議,正是看似平凡、實則高明的「自固之術」,對於聯絡父子感情,極具針對性。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史籍中的下列記述。《三國志》卷二一《吳質傳》注引《世語》載:曹操出征,曹丕、曹植送於路側。曹植稱述功德,出口成章。曹丕受吳質啟發,臨別時哭泣而拜,「王(曹操)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前引《曹植傳》載:「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三國志》卷二《趙王干傳》載:「干母(王昭儀)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干母有力。」概括而言,曹丕「深自砥礪」,或「御之以術,矯情自飾」,收到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曹操對曹植的眷愛之情。
通過以上考察,我們可獲得兩點認識。首先,曹操一生愛才惜才,對己子尤其如此。他因曹植之才而特加寵愛,以致欲立為嗣,其中情感因素實居主導方面。但是,通過多方調查,發現曹植的政治抱負和才能都不能令人滿意,而曹丕及其支持者的政治勢力卻相當強大,為避免不測之變,於是鄭重地決定立曹丕為嗣。其間,曹操經歷了以理性思考澄清感性認識的過程。不以感情用事,而是正確地審度時勢,正是曹操在立嗣這類重大決策方面的英明之處。順便提及,前引《三國志·魏書·曹植傳》,尤其是《賈詡傳》關於立嗣問題的結論性記述,把握住了該問題的最突出現象,其豐富內涵則需要我們依據史實加以闡述。
其次,擇立繼嗣的過程實際上是篡漢建魏的一次預演,因為無論支持曹丕或支持曹植,都是以承認「大魏」為前提條件的。曹操力圖以魏代漢,臣僚們自然清楚,因此,對「大魏」立嗣關心,即顯示了一種明確的支持態度,而持反對態度者,則不預於立嗣議論。我們判斷崔琰並非真正要反對曹操晉封魏王,這也是根據之一。總之,立嗣問題超出了其本身,意義重大。

綜合以上論述,可得出如下結論。
一、曹丕、曹植爭嗣起於建安十七至十九年間,原因是曹植的文才引起了曹操注意,同時,曹操在立嗣觀念上重視政治才能,頗為輕視「立子以長」的宗法制傳統和原則。在此之前,曹丕的世子身份和實際政治地位,曹植無法比擬。
二、曹操有立曹植為嗣的想法,卻對其政治抱負和才能不敢確信。就才能而言,曹植所表現出來的主要是一種文才和論說之才,能否轉化為實際政治能力尚屬疑問。因此,曹操對曹植及曹丕進行了考察。結果,曹植的政治抱負和才能終究不能令曹操放心。
三、於是,曹操轉而徵求各下屬機構中僚屬的意見。一方面,崔琰、賈詡等人支持曹丕的意見影響了曹操的判斷,尤其是舍長立幼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迫使他放棄了立曹植為嗣的想法。另一方面,曹植的支持者丁儀的政治表現,楊修的複雜背景,以及曹植本人結交名士的態度等,都對曹植爭嗣造成了不利影響。
四、立嗣是一件最重要的「家事」,其中充滿了感情因素。曹植本來在這方面占有絕對優勢,但經過曹丕的種種努力,這種優勢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
本文節選自柳春新《漢末晉初之際政治研究(增訂本)》上篇第五章「曹操立嗣問題考辨」,注釋從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