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重成績,將經濟邏輯內化,年輕人將陷入「意義貧困」 | 專訪
采寫 | 實習記者 李彥慧
編輯 | 黃月
恢復高考47年後,2024年高考報名人數高達1342萬人,相比2023年增加了51萬。
提起高考你會想起什麼?是六月悶熱的天氣,英語聽力前下過的大雨,送考的家長老師們一聲聲「加油」,還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考定終身」、「一分打倒幾千人」?如果說前者代表個體關於高考的回憶,那後者就顯露出它作為選拔性考試的殘酷面向。
當下,結束了高考的年輕人正面臨著進入高校的「第一道門檻」:填報志願。從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流行的說法「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近兩年來直言「孩子學新聞就拖走」的張雪峰,考生的專業選擇並不總是與分數、個人特長與愛好密切關聯,還與就業前景或未來人生「牢牢綁定」。
教育社會學學者謝愛磊從2013年起在全國四所重點高校對農村籍學子展開相關研究,十年間他對約2000名重點高校學生做了追蹤研究,並與其中的百餘位農村籍學生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深入訪談。他們進到大學,然後經歷了什麼?那些贏得了高考搏殺,從農村或小鎮「逆襲」進入全國重點高校的的學生們,在這裡面臨著哪些此前未有、同齡人也未必感受得到的挑戰?

謝愛磊,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圖為講座現場。(圖片由本人提供)
在日前出版的《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與象牙塔》中,謝愛磊發現,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學生進入重點高校後變得孤獨、迷茫,「當舊的考試節奏消失殆盡,自我也就失去了坐標。」先是失去了具體的題目和考試,畢業後又失去了邊界清晰的校園,做題家們如何面對生活?介面文化對謝愛磊進行了專訪。
沒有誰是天生的做題家
介面文化:最早為什麼想做關於精英大學農村籍大學生的研究?為什麼選擇做一個長達十年的追蹤研究?
謝愛磊:研究是從2013年開始的。我自己一直做農村教育研究,持續關注農村學生的發展。還有一個更直接的背景:當時精英大學裡農村籍大學生的比例有一點下降,2012年起國家出台了一些政策來應對這一現象,例如面向貧困和農村地區的專項計劃。政策出台之後,精英大學裡的農村籍大學生比例確實逐年在增加。
我更關注的是這些學生進入精英大學之後的學習生活。這也是我們做教育社會學研究的人特別關心的事:當一個人擁有在精英大學受教育的機會的時候,到底能不能利用好這個機會,順利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
另外,當時一些面向貧困和農村地區學生的舉措實際上是一種「優惠政策」,大眾想當然地覺得,這批進入到精英大學的農村籍大學生會不會存在學業上的問題,一些極端個案被報道出來,比如有個別學生在大學裡沉迷遊戲、學習困難甚至輟學。如果故意把這些負面印象放大,可能會造成我們對這一群體認識的偏差,甚至是對他們的污名化,以至於我們不能夠看到他們在大學裡真正面臨的是什麼樣的挑戰。
介面文化:在調查過程中,會有學生稱自己「小鎮做題家」嗎?
謝愛磊:「小鎮做題家」這個詞大概2020年才火起來,我的研究開始於2013年,那個時候學生們不會叫自己「小鎮做題家」,但他們的敘述里的確有很多和「做題」有關,一種比較普遍的說法是叫自己「做題機器人」。這一方面代表他們的苦惱,在應試教育模式下人生好像只有一條賽道,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反擊」,他們反思自己過去接受的教育是在培養「做題機器人」,沒有發展他們的個性、獨立性和其他素養。

《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象牙塔》
謝愛磊 著
北京貝貝特·上海三聯書店 2024年5月
不僅他們不會自稱「小鎮做題家」,我也不太願意把他們叫做「小鎮做題家」。我之所以用這個詞,甚至作為書的標題,是在某種對話的意義上使用的。我想和那個時代的學生的聲音、遭遇,以及「貼」在他們身上的標籤進行對話,讓人們知道當學生們自嘲「小鎮做題家」的時候到底在自嘲些什麼。
我總覺得下定義或者貼標籤可能會讓某個群體「動彈不得」,讓人誤以為他們是一成不變的。我想提供的是一個理解這群學生的框架,從「遊戲感」、心態、反身性去理解他們,再理解背後宏觀的歷史和結構性原因。
不管被叫做「小鎮做題家」還是「讀書的料」,如果要通過某種特殊的群體「標籤」才能獲得力量,那這種力量很可能是假的。真正的力量要從自己身上去尋找,而不是通過被貼在身上的標籤中去尋找。書里的不少學生通過分析自己、分析社會逐漸改變,在思考過程中逐步發掘屬於自己的個體的獨特性,而不是沉迷於從標籤里尋找自己。
介面文化:書里不少學生說「教育是我們唯一的出路」,你怎麼看待教育對於農村學生的重要意義?
謝愛磊:教育有它的重要性,但不能誇大它的作用,影響個體社會流動的因素有很多。他們大概的意思是,對於自己來說,教育是他們比較依賴的一條路,他們的主觀判斷也是這樣,但這不意味著教育是他們擅長的路。
沒有誰是天生的做題家,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學生在求學路上有很多客觀條件限制,他們更難遇到好的師資和教育資源,這些學生本來就更難成為客觀意義上的「做題家」。
教育只是社會的一小環
不該過於理想化
介面文化:像是「做題機器人」或者「機器人」這樣的自嘲,是否體現了農村籍大學生適應精英大學過程中的困難?
謝愛磊:我的研究對象長期生活在農村或者小鎮,早期的家庭學校教育經歷使得他們很可能沒有經歷過豐富的文化活動,他們的家庭也可能很少有主流社會認可的文化資本投資,學生到大學之後很自然會產生茫然失措的感覺。
學業上的困難也是存在的。談到學業,學生們會用「搞定」來描述,就是說到期末考試時我突擊一下,提前問問學長學姐記一記重點,也能拿到一個很好的分數,畢竟考試的套路是老的。「做題」的確可以幫學生在大學裡獲得分數,但學到真東西和考試拿到分數是兩回事。我之前評閱論文的時候看到一個觀點,大致是說今天國內頂尖大學的大學生在「假學習」,學生可以為了高分認真在課堂上互動、和老師討論,他們好像投入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卻沒有賦予這件事多少意義。
那麼當學生說自己是「做題機器人」的時候,還可能意味著:我在大學裡考試沒問題,但「學到知識、增進對某些問題的理解、對將來的工作有所幫助、對自己的人生產生思考」和「考得好」是兩回事。學生也會反思只培養做題技能的高中教育反思,也反思大學教育,比如有些課程是不是有點「水」?有意義的學習是不是少了一些?學生和老師的互動是不是少了一些?

還有一層反思體現在高中和大學教育之間的差異上。高中老師是把課內的東西「嚼爛」教給學生,課內的東西學好就行,但大學老師課上講的只是皮毛;很多學生原先的教育經歷里自主學習的成分非常少,合作學習的嘗試也很少,但是大學課堂常常有小組合作、自主學習。也就是說,過去的學習經驗沒有辦法讓學生為自己大學的學習做好準備,兩者之間有天然的鴻溝。
我寫這本書的初衷,部分是希望能夠反擊某些針對「小鎮做題家」的刻板印象,另外也想說明有一些影響年輕人大學體驗的因素,與城鄉有關,但不是被城鄉所決定的。不少並非來自農村或小鎮的學生也跟我反覆提到,他們也有同樣深刻的感受,我說,那是因為我們面臨共同的結構。
介面文化:這個結構具體是什麼樣的?
謝愛磊:這個結構首先指的是教育系統:眼下,高中教育越來越強調對單純的學習環境的營造,學習主要是高強度的「灌輸」、機械的學術訓練還有無休止的競爭和篩選。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個結構主要是收入不均衡。兩個方面其實是相互影響的,教育有雙重功能——社會化和篩選——在收入不均衡加劇的情況下,它的社會化功能就比篩選功能得到了更多的強調和重視。大家越強調教育的篩選功能,就會越強調應試能力,不讓自己被篩掉。這其實關涉到社會分層的問題,教育是很被動的。
經濟學家馬賽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在《愛、金錢和孩子》提到過,當一個社會越不平等,尤其當教育能對一個人未來收入發揮重要作用的時候,教育內部的競爭就會越激烈,甚至個體遇到的教育模式也會不同,比如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家長可能會傾向於權威式的教養模式,而不是民主型的教養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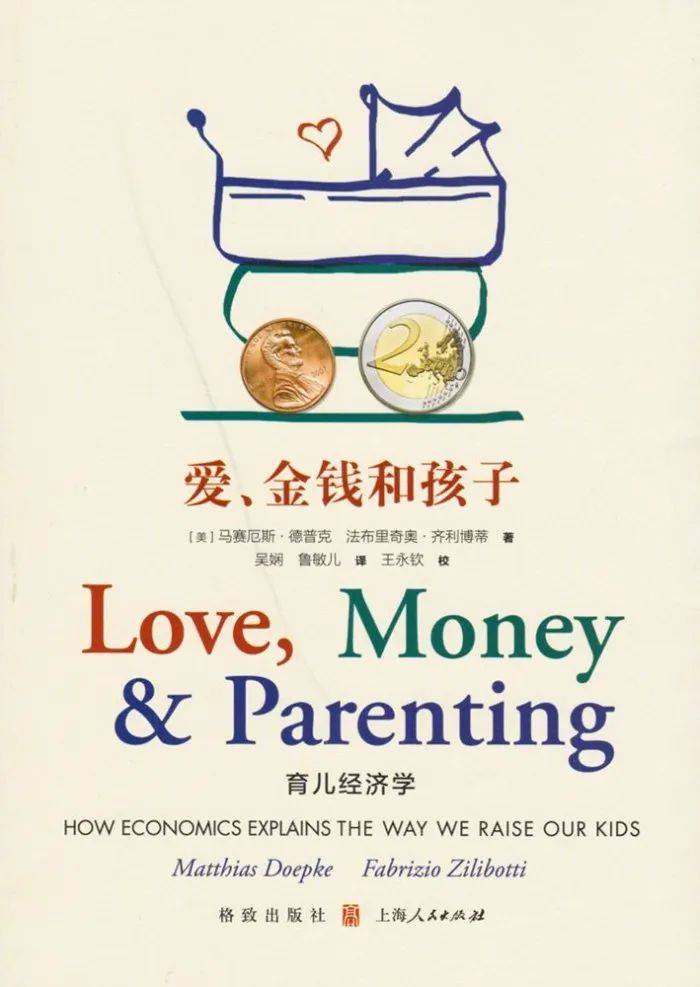
《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
[美] 馬賽厄斯·德普克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著 吳嫻 譯
格致出版社 2019-06
「教育/知識改變命運」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有著無可厚非的正當性,但在做研究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有太多因素在影響社會流動的機會。既然教育只是社會系統里的一小環,那麼我們對教育的認識就不該過於理想化。教育有改變命運的潛能,但是這種潛能的發揮比較有賴於我們整個社會共同做一點事,比如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更高質量的就業......如果我們想要讓教育發揮更好的作用,就必須創造出這些條件。
不是對教育悲觀
而是對文憑價值下降擔憂
介面文化:在今年的高考月,很多人發現這種「無可厚非」的正當性似乎正在動搖。一些家長和年輕人似乎在重新審視高考和教育的意義。你怎麼看社會下行期人們對教育的悲觀?
謝愛磊:從客觀上來說,無論社會發展到什麼程度,教育對個體的作用很大程度上還是正向的。我是做教育工作的,總相信教育的力量。但是我們現在處在特殊的經濟周期里,大學生就業確實遇到了挑戰,而高等教育本身又進入了普及化的階段。2023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了60.2%,說明我們處在一個「大部分人都能上大學」的時期,那麼這個時候大學文憑帶來的回報很難直接用學曆本身來衡量。教育又常常被視為一種投資,當投資的回報不充分的時候,大家對它感到疑慮是正常的。此時就會越來越強調教育內部的分層:要不要上一本大學?能不能上985、211?再進一步,能不能讀C9大學或者海外名校呢?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討論得更多的不是「教育能不能改變命運」,而是「什麼樣的教育有助於改變你的命運」。我想人們也許不是對教育悲觀,而是對文憑價值下降的擔憂。

介面文化:「什麼樣的教育有助於改變你的命運」讓我想到近期引起熱議的「中專學生入圍全球數學大賽決賽」。不少人非常惋惜這樣天才般的人物沒能去普高、沒法去更好的大學深造等等,我們怎麼理解大眾對中專的「偏見」?
謝愛磊:這件事引起我的思考,當我們發現一個特殊人才的時候,整個社會好像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一種教育優績主義的思路里去,用學校的等級來衡量人的能力、價值和尊嚴。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文憑社會裡,總習慣用學校的層次和文憑的等級來衡量人的價值,衡量人的能力和他們應當的尊嚴。
好的教育是另一種思路。在中專里學習又怎麼樣了呢?中專里的孩子同樣是值得我們珍惜的孩子。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認為,其實所有在中專的孩子都有優秀的可能,優秀不一定要表現為在競賽里拔得頭籌,表現為沒有進入「頂級大學」,是不是也可以是在他們自己專長的領域發揮才智、自得其樂。
我知道這有點理想化,但個體接受的教育不應該被簡單地作為標準用來衡量學生的智商、區分學生的努力程度,我們更不能依據它來判斷一個人的全貌,尤其不能把它與學業之外的東西掛鉤,比如品行、道德。否則會帶來很多問題,比如讓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教育與社會地位的分配有關,先入為主地認為身處在某些教育機構中孩子就具備某些特質。其實,這也是公眾較難接受職業教育的重要原因。
介面文化:現在高校生中出現了「考公」、「考編」熱,但也有人會認為年輕應該闖一闖,而不是逐大流去追求鐵飯碗,我們怎麼理解這種現象?
謝愛磊:在充滿機會的年代願意大膽嘗試,這是理性判斷。在外部風險加大、經濟環境變化的時代選擇穩定,同樣是一種理性判斷。我之前寫過一篇關於農村家長教育觀念的文章《「讀書無用」還是 「讀書無望」——對農村底層居民教育觀念的再認識》,當時有部分人認為農村家長的觀點就是「讀書無用論」,是不理性的,但我觀察發現,實際上他們對現在的教育機會、社會流動有一些理性的觀察和新的思考,這就是農村家長的一種理性的態度。只是批評農村家長的態度無法解決問題,更應該從入學機會、學校適應等結構性的問題入手,幫助農村學生更順利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
過度重視智育
學生陷入「意義貧困」
介面文化:你在書中提到,精英高校農村籍大學生認為自己在大學生活中「缺乏遊戲感」,他們的「自卑」其實是「自我低估」。具體來說這種遊戲感是什麼,怎麼理解他們出現這種自我低估的傾向?
謝愛磊:「遊戲感」第一是要「看見」,能「看到」大學裡有些什麼東西。對於很多農村籍大學生來說,他們的早期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經歷使得他們去到大學之後首先看到的還是和學習相關的東西,看不到學校還有學習之外的社會生活領域,也不知道這些生活領域裡有哪些內容,所以他們會自嘲說:「我就是做題機器。」
「看見」其實很重要,其次就是「喜歡」。當你看到這些東西之後,願不願意探索嘗試,這也很重要。訪談中有學生表示願意去試試,也有部分人不那麼喜歡,會覺得這些和他們原來的生活模式不太一致。很多學生會提到一個詞「功利」。比方說,他們可能會覺得某些學生組織或者社會活動和自己原來的價值觀有衝突,但是參加卻可以在綜合評定里加分。
第三個方面就是有準備,可能得有一些技能儲備、知識儲備,更重要的還有文化方面的儲備。社交的時候別人跟你聊籃球、聊歌星、怎麼追星怎麼搶票,如果你對這些事情沒有概念,那麼難免會在社交場合感到侷促。
介面文化:「看見」、「喜歡」和「有準備」三者缺少任何一個都會出現「缺乏遊戲感」的體驗嗎?
謝愛磊:是的,但我更想強調的是「遊戲感」是一種主觀感受,缺乏遊戲感不一定會導致什麼很不好的後果。也沒有誰是100%缺乏遊戲感,只是有些人遊戲感多一點、有些人少一點,重點在於這是一種個人的感受。
缺乏遊戲感不是一種病,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我們在做「病理化」分析,把一個可能的由社會結構造成的問題,看成是專屬於個體和群體的性格缺陷,好像生病了一定要用藥去治。我就認為「遊戲感」是一種心態,是可以通過探索、嘗試改變的,心態會影響後面的行為,行為也會反過來影響心態。
介面文化:你提到擔心「病理化」的分析,這讓我聯想到,很多年輕人試圖超越主流標準(比如成績)的「遊戲」,最後好像都成了一種新的卷法、一種新的競爭。比如卷運動、卷外貌,連在社交平台曬「躺平」的博主也要卷粉絲量。這些本意是玩耍、遊戲、取悅自我的東西,到最後都變成了一種可能消耗和傷害自我的大型競賽。你是怎麼看這種「卷」的泛化?
謝愛磊:這確實很有意思:跑到另一個賽道的人最後又「卷回去」了。因為我們處在一個「社會嵌入市場」的時代里,就是說社會的各個領域都被經濟活動影響,經濟活動的邏輯向外無限擴散到了其他生活領域,而個體不可避免地被捲入競爭性的經濟邏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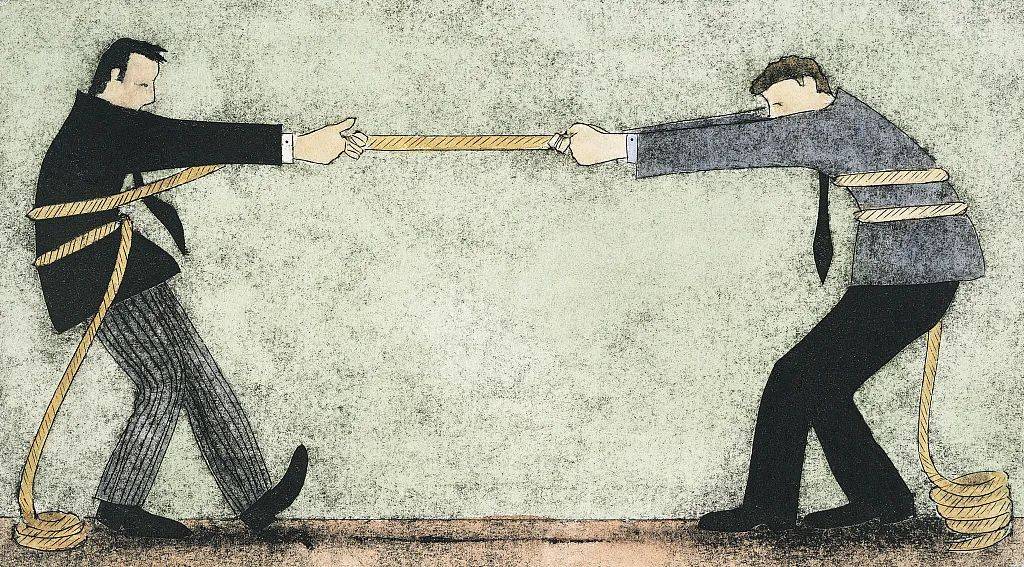
但我認為「開闢另一個賽道又捲起來」這件事本身也許無可厚非,因為退一步講,它畢竟展示了多元的選擇,結果也許並不盡如人意。我其實比較看重他們在非經濟意義上單純做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這種嘗試,它可能也許反映了普通人在價值觀層面的一些深度思考,比方說,我們可不可以有超越經濟邏輯和現實利益的生活意義、理想、信仰與終極關懷。
介面文化:即使順利畢業,很多人在工作中會自嘲又變成了「大廠做題家」。在你看來,為什麼這種狀態延續到成年人的工作甚至情感生活(985相親群等)中?
謝愛磊:我把這種狀態稱作「意義貧困」,指人好像被困在了什麼地方,比如教室、考場或者公司的格子間,生活里的其他東西好像得不到關照,自己總覺得很迷茫。前面提到這個時代經濟邏輯泛化到生活的其他領域,而很多人又把這套邏輯內化,從單向度的經濟意義上追求自己的價值。那麼在遇到挫折的時候,難免會懷疑此前自己相信的東西。
但是此時,除了經濟意義,好像一時之間又找不到別的坐標來衡量。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當我們試圖理解自己的人生意義、思考我們是誰的時候,我們竟然找不到另一套非經濟意義上的話語,在人文向度上思考人還可以是什麼樣的。好的教育應該提供給我們這些思考的話語和工具,教育不能只是技能訓練,它應當直指心靈。
我們常常說教育追求人「德智體美勞」的全面發展,但我們在教育實踐中感受到的是對智育的過度重視,強調學業成績。當教育的重心被放在如何通過機械訓練幫助學生進入大學,他們在面臨學業之外的社會生活的時候,自然會覺得「我的人生怎麼被限定了」、「我怎麼這麼狹隘」,而教育本應該為學生能擁有更廣闊的人生做準備。
就像教育家魯潔曾說過的,教育要實現兩種目的:有限目的和無限目的。有限目的指的是使我們的孩子具有謀取生存的手段,能夠為經濟生活做準備,但無限目的其實是更重要的,它意味著讓我們的孩子能夠思考「為何而生」,能夠自我創造、自我發展、自我實現。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實習記者 李彥慧,編輯:黃月,除書封外本文圖片均來自視覺中國,未經介面文化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