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宗忠
淘來的這些二手書,有的書裡面有藏書票,有的書寫著購買日期和書店名,有的書畫著重點段落,有的書標註著拼音,有的書寫了感想和注釋,還有的書折著頁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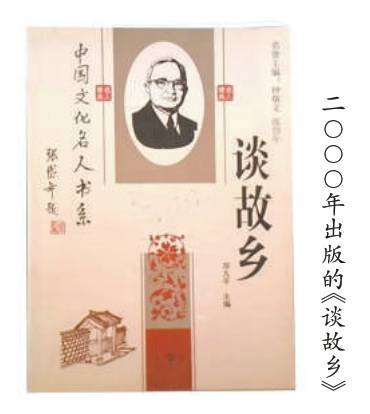
時值晚秋,宜人的天氣,給人秋高氣爽的感覺。出行恰巧要在中關園公交站轉車,車站正對著北京大學的東門,門口陸續有遊人登記進校去參觀,那是讓人充滿嚮往的地方。忽然想到以前出入北大校園的日子,好像一切很遠,又很近:在未名湖畔散步,在北大圖書館讀書,在校園內外淘書……仿佛幻燈里的照片,一幕幕投影出來。
二十八年前,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讀書,那時的白石橋路兩邊、路中間都種著高大的楊樹,濃密的樹蔭遮住了整條道路,形成一條南北貫穿的景觀大道。騎上弟弟當年給我買的一輛永久自行車,來到北大校園,看看三角地幾個廣告牌上貼著的各種通知,裡面有電影、戲劇展演,有文學社的詩歌朗誦會,有文學、歷史、經濟、哲學、國際等講座,還有大課、小課和各種交流活動,你喜歡什麼,就去禮堂、教室,找個地方坐下來聽課。不論你來自哪個院校,北大都一視同仁,課堂上大家聽得認真,老師講得精彩。誰去得早誰就有座位,沒座位就坐在台階上,台階上坐不下時就靠牆邊站著,人多但不喧鬧。那樣的年代知識充盈,人們通過各種方式學習。本校大學生、借讀生、走讀生,其他大學的學生,遊學的人,還有社會青年等,都能在大學教室、階梯教室、禮堂里像海綿吸水一樣汲取知識,大家都有一顆渴望知識的心。通過串走各個大學,能學到很多其他學科的知識。我在這裡認識了不少「學友」。每當得知哪個大學有名人來講座時,大家都會奔走相告,可以一起去聽一堂真才實學的講座。那時候各大學飯堂里的飯菜很便宜,幾塊錢就能吃飽吃好。
那時的周六周日,北大校園裡有一個舊書市場,許多「老學究」將家裡裝不下的書、閒置多年的書都拿出來擺賣。只要花一兩塊錢,甚至幾毛錢,就能買到心儀的書。我曾經在舊書攤位上,集齊了一套1959年中華書局第一版的繁體字《史記》。書買到手時,那種驚喜也許是只有愛書的人才能體會。還買到了繁體字的《庾子山集注》,也是難得的珍品。大半天時間我都穿梭在書攤前,為了買書不吃午飯,用節省下來的錢,再多買兩三本書。
不僅校園裡有舊書市場,在北大東門外還有一個擺地攤的舊書市場。這箇舊書市場裡書的品相,要比北大校園裡的書稍微差一些。那時,中關村北大街還沒有貫通,中間的「城中村」里還有個萬聖書園。我在那裡買過一些書,還記得有一本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旅行記》。除了北大舊書市場,舊書商也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擺攤。他們每周六日把書運到圖書館門前或者西邊的路邊,搭上攤位,擺上書。我還記得在那裡買過一套中國文化名人書系《談故鄉》,還有《菜根譚》的大開本書,至今還珍存在書櫃里,常常翻閱,受益匪淺。每當翻看這些書時,似乎又回到那些淘書的時光,回到大楊樹下淘書的情景里。
淘來的這些二手書,有的書裡面有藏書票,有的書寫著購買日期和書店名,有的書畫著重點段落,有的書標註著拼音,有的書寫了感想和注釋,還有的書折著頁碼……那個折了頁的藏書人,也許讀到這一頁就去忙其他事了,再也沒讀完這本書,留下了遺憾。如今這本書流落到書攤上,又開始尋覓知音,等待有人接著讀完書中的故事。
隨著城市的規劃,不少書市、書攤逐漸退出了校園和路邊,像地壇書市這樣有規模的書市逐漸多了起來,吸引愛書人前去淘書。書市更多的是展賣出版社或者書店的新書,而曾經在舊書攤的書中發現的書籤、簽名、便箋等意外收穫再也沒有了,也看不到藏書人在書里寫下的讀書筆記和隨感,那些二手書里的溫暖情懷已不再。
今天,再次走過北大門口,突然回憶起那些有書攤可以逛的周末時光,那時候沒有手機的干擾,沉浸在一本書中和淘到喜歡書的快樂心情,是一種無以言表的富足和快樂。(作者為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mo/8d60b86aecae4a21f70275639b3d26a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