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园与晴庐事件:末路还是曙光?
美丽园小区事件将带给物业管理什么?
《华夏时报》9月4日报道:鸿铭物业公司撤离海淀美丽园小区已经3天了,3日下午3点,小区200多名业主自发成立了业主临时大会,欲罢免业委会,并签名决定召回鸿铭物业还是选择新物业。1378户业主中,已经有近600人签名。
9月3日下午6点,正在国宾酒店参加《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三周年,回顾业主团结互助及申请成立业委会协会座谈会的律师秦兵,在得知美丽园业主和业委会发生冲突后,立即号召会场50余人到美丽园小区声援业委会。在当天举行的座谈会上,业委会负责人发表了致北京市物业行业的一封公开信,并宣布申请成立“北京市业主委员会协会”,200多名各小区业委会的负责人签名响应。
点评:美丽园小区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用一位资深社区管理人士的话说:它让我们见证了一次“业主拿自己财产进行的民主试验”,它是发生在今天的北京版的法国大革命,昨天的激进派很快被更加激进的人物所取代,前者被批判为“保守者”,而被清洗出社区管理的舞台;直到人们渴望安宁的时候,革命者也将受到清算。
无论如何,这种“业主维权”已经表明出了和以前的物业管理纠纷种种不同的特征,它所形成的决裂将是巨大的、完全的、决定性的,而这种彻底性包含有一切未来发展的萌芽。——中国物业管理的革命,不过是才刚刚开始。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物业管理企业,也应当警醒和感同身受:鸿铭物业与我们每一个同行同质同源,她的困惑与悲哀,这种对待业主“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情结,与我们绝大多数人同样并无二致,假如我们没有能力进行自我改革,即使业主处在分歧当中,原来的物业公司也不会得到宽恕。
——深圳《住宅与房地产》2006年10月“时事点评”梁晓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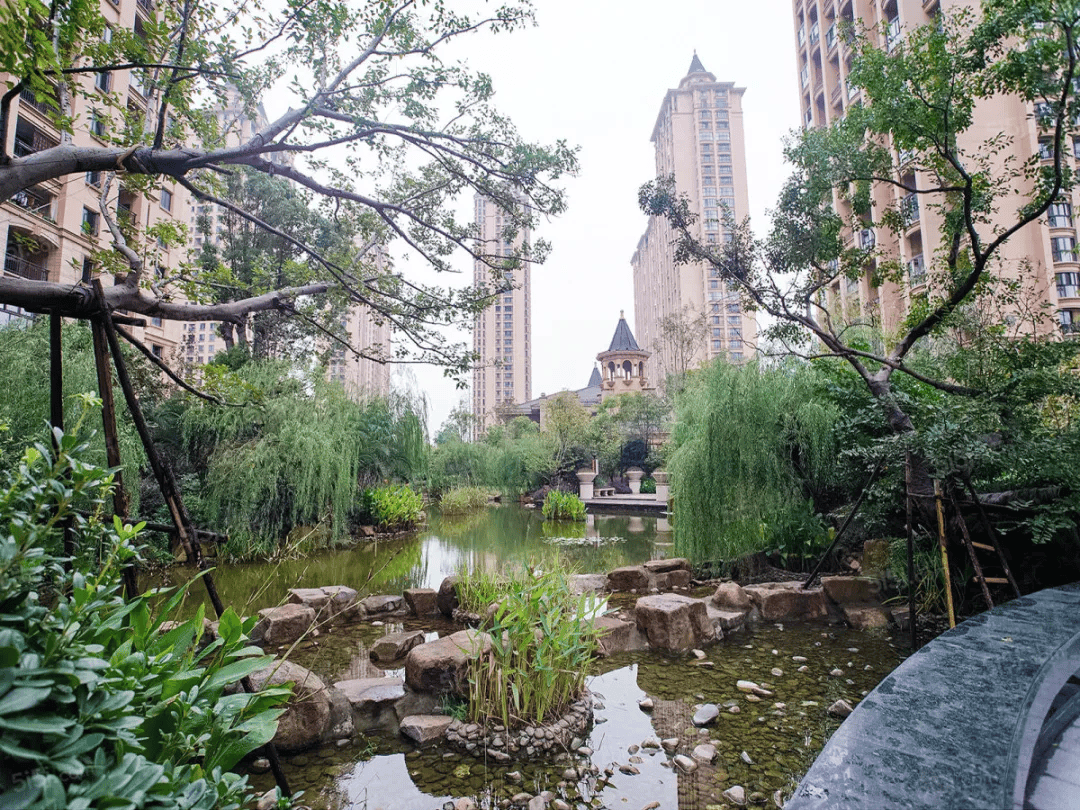
昨天听过一段录音,当业委会主任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表达出他自己个人面临的危机时,在另一方表现出一阵哄笑,这令我内心浮现出强烈的感受:尽管谈不上光明一片,而我从不认为中国社区的民主探索漆黑一团,历史经常重复两次,第一次以悲剧呈现,第二次则会喜剧呈现,至少今天来看,曙光已经呈现,在这种时机我有一些独特的思考,虽然不失片面,但我依然认为有其可操作性和值得尝试之处。我们需要一点一点地去梳理问题,然后找到解决之道。
第一个问题:业委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他们更容易受到来自于业主内部的质疑?
答:业委会存在的制度背景是民主政权亦即“开放社会”,它的潜台词是“每个人都并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正确的”、“每一个人都能对政策发挥影响,即使不能改变政策,至少我们能够评说政策”,然而与之相对应的“专制政权”或“封闭社会”首先的任务是消灭反对者。
容忍一个强大的在野党存在,是民主社会的基本条件,而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家长式社会就必须首先取消掉一部分人的话语权,独裁更是如此,中国古时的“言官”经常是制度开明的体现——魏征这样的人让唐太宗都非常恼火,甚至经常想干掉他,——而所有业主均有权质疑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是业委会制度体系的优越性所在,这是优点而不是缺陷,所以碰到的难题在于与这个民主制度相关的人,民主本身并不能提供制度理性。我们经常还去说“乌合之众”,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尊重过乌合之众。
所以,因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缺陷就责备“制度失灵”是大错特错,我们更应把责任归于自己,即这个社会的成员,特别是我们在某个阶段上成为管理者时更应找到自己的问题。业主自身在智识上的成熟和道德上的完满,也是一个过程,通过和谐社区发展中心早期举办的几次研讨会都可以看出,人与人的平等沟通极为困难,中国人的民主修养还需要从“开会”、“议事”做起,这是一个基础建设。从事业委会工作的人,最初也许都抱有种种私欲和不同的目的,但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应当说无论是智识还是道德层面,都不再会和那些“事不关己”、“胡搅蛮缠”的人同日而语。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最好的物业管理公司也能引起业主不满,为什么他们总是“管不好”?
AI的回答:物业管理公司引起业主不满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
1. 沟通不畅: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之间的沟通不畅,导致信息传递不及时或者存在误解,造成业主不满。
2. 服务质量不佳: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不符合业主的期望,可能存在态度恶劣、服务不及时、处理问题效率低等情况。
3. 缺乏透明度: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方式缺乏透明度,业主无法了解物业费用的使用情况,或者对管理决策不清楚,导致不满情绪。
4. 管理混乱: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不当,导致物业设施维护不及时、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处理等问题,引起业主的不满。
5. 利益冲突:物业管理公司可能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导致其在处理业主事务时存在偏向或不公正的情况,进而引起业主的不满。
总的来说,物业管理公司引起业主不满可能是由于管理不善、服务质量低下、沟通不畅、透明度不足等多个方面的原因所致。要解决这一问题,物业管理公司需要加强管理能力、提升服务质量、加强与业主的沟通等方面的努力。
我的回答:物业公司们为什么管不好,除了缺乏工匠精神之外,我们不能将之简单归咎于乙方责任。现在可以提出一些对现实的描述性假设:物业管理费支出不透明,有被浪费和侵占的危机或倾向。公共区域产权归属的界定不明,其收益的去向受到业主质疑。(前两项一般是业委会炒物业的理由)政府部门对社区内的纠纷处理进行推诿,不作为(这是北野先生经常强调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较多摊派,增加了物业管理成本。单个业主强大的谈判能力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交易成本,他们可以采取拒缴费用的方式实施单个业主的抵制,物业管理收费太难了。(这两项是物业管理人士的苦衷)“业主满意度”和“物业完好率”不能够以相同房价档次的深圳、上海来比较和参照。
朱宪辰教授的答案:1、多边合约达成与实施的集体行动困境+双边交易信息不对称的模糊合约纠纷。
2、共享事务治理——非市场、非政府的“共享事务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s)”的自主治理。奥斯特罗姆夫妇将此称为CPRs。
3、行为理论启发:大多数人大多数场景的简单信息认知特征,即他们只愿意接受非常简单的信息,并依此作出利弊的估计判断;多边、双边互动中投入精力者主要受情绪道德直觉支配。
第三个问题:原先开发商手中的香饽饽,为什么传到业主手里就变成了臭狗屎或烫手山芋?
为什么前期物业管理开发商还能管得好,到了业委会成立之后,物业怎么都反而管理不好了?原因在于这个行业其生存背景就是一种制度环境高度冲突的产物,政府和开发商,业主和社会,其中的利益诉求错综复杂,对开发商或者说大物业而言,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压根不是问题。但今天更大程度上是业主们和干预者的诉求冲突,业委会指望倚靠着铁板一块的业主阵营其实是天方夜谭,他的责任、权力和法律上的定位(业主大会召集人和决议实施执行人)其实完全不匹配,甚至存在角色对立。
这里各相关主体忽视了一点:民主社会的特点在于,谈判主体的资格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当年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创立国联,但是国联成立后美国自身却没有加入,因为被美国国会给否决了,美国国会同样也否决了威尔逊主持下的《凡尔赛条约》,年轻的凯恩斯写过《和约的经济后果》。如果威尔逊是业委会主任,他就总是这样被搁置在尴尬境地——业委会的所谓物业管理招标,对老物业而言,它除了“威胁”以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承诺”;对新物业而言,其实兜售的无非是一张空白支票,许诺的这个管理费标准业委会并不帮他收,但投入的钱却真金白银要打进“共管账户”,这个承上启下的环节大可质疑。假若冲突是必须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业委会成立之后,老物业公司马上丧失了或被打乱了与业主之间的正常沟通渠道。一个敲诈者也许因为主人不在家,而失去敲诈的机会。绑架犯也是一样。你可以把物业公司认为是一个敲诈者和绑架犯,但是他们的难题在于压根找不到威胁的对象,或对应的业主或业委会成员向物业公司提出的每一个要求,物业公司如继续在社区中生存的话似乎只能无条件满足,否则就是业绩越来越差,怨隙越来越深。所以业主们一边声称“取消物业”、“赖着不走”,一边还在援引《民法典》要求物业企业不能擅自撤出。这拉扯之中的痛苦自非常人所能承受和领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六日
- END -
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公众号后台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
本文不代表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