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時代母職的境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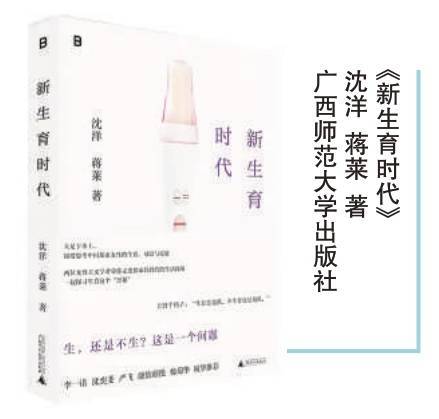
蔣萊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述明,家庭的功能圍繞財產傳遞給血緣後代展開。在當代話語體系中,它呈現為婚禮上「早生貴子」的賀詞和婚禮後順理成章的期待。在這套敘事體系中,生育被定義成女人不假思索、無可迴避的一項任務,至於生育之後會遭遇什麼,幾乎無人問津。很長時間裡,我都愛套用香港作家亦舒的「婚姻猶如黑社會」論來描述生育後的感受:「沒有加入的人總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處,故此內幕永不為外人所知。」事實上,一朝分娩,這項「任務」便再無完成的那一天,回顧育兒一路上的奶粉、就醫、玩耍、入托、上學種種,是無窮無盡的思慮操心;而自我的探尋、職業與家庭的關聯和多個身份的平衡,也是自己必須面對的人生課題。某種意義上,我認為生娃的「黑社會」性質更甚婚姻——孩子固然是增強夫妻關係的紐帶,卻在更多時候成為兩性間的矛盾來源和離婚障礙,沒有孩子的婚姻脆弱易碎得堪比戀愛分手,而有了孩子之後呢?即使不幸(或有幸)分開,因為這個承載兩人基因的生命體在世間的存在,你永遠都不可能與前任重返陌路了。
把我和沈洋聯繫在一起的,是從個人經歷引發出的研究旨趣,以學術為工具,探究「生,還是不生?」這個每位育齡女性都不得不以實際行動作出回應的問題,如何改變了她們的生活、職業、家庭、自我,以及對整個世界的認識。
我的研究興趣來自「二孩時代」開啟後對中國社會和中國女性的新認識。一方面,過去三十餘年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最強烈、實施「一孩制」最嚴格的家庭基本上局限在城市、良好受教育背景、公有制單位、體面就業這幾個標籤下的育齡女性,在更廣大範圍的農村地區,二孩乃至多孩媽媽並不鮮見。另一方面,性別平等的提升並不總是與經濟增長同步發展。城市中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女性可能會發現,她們在校園裡的成功並未能順利轉化為職場上的成就。社會政策和福利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將育兒責任視為家庭私事,而女性則無償承擔了其中大部分的照料工作。
細細數來,我們調查和研究過的家庭,已經達到四十餘個,訪談超過六十次。在一次次碰撞交流中,我們與受訪者一起討論了生育的動因和時機、生育前後的期待和失望、初為人母的挑戰和壓力。每一次生育經歷,都伴隨著和工作、父母、配偶、孩子(們)的關係變化,分享這一路上的成就與缺憾、欣慰與辛酸、痛苦與成長,以及對未來的想像、對孩子們的期盼,都是對後來者的誠懇建議。
英國作家蕾切爾·卡斯克在《成為母親:一名知識女性的自白》中說,「母性是一座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的圍城」,「孩子的出生不僅將女人和男人區分開來,也將女人和女人區分開來」。當中國社會鄭重宣告三孩時代的來臨,或許是時候打開圍城,讓更多人領略其中各色姿態、雜陳五味。生?不生?生幾個?對這些問題不同的回答,固然會通往相異的人生,但作為占據人口半數的女性群體,我們相信思想交匯、情感交融是身為命運共同體建立聯結的最好方式,也是家庭中與孩子爸爸互動和溝通、理解與體諒的攜手並進之路。
在這本書中,我倆憑藉研究者的敏感性和使命感,力圖對新時代下的母職做立體而充分的探討。我們的研究聚焦於媽媽們如何理解和實踐母親角色,包括職場媽媽在工作與家庭間尋求平衡、全職媽媽的家庭回歸之路,以及二孩媽媽再次成為母親的故事等等。但我們也注意到,書中的媽媽們多來自城市中產或富裕階層,擁有高學歷和房產,這限制了我們對更廣泛母親群體的覆蓋。我們遺憾未能展現更多普通母親的境遇,同時意識到,當今母職的履行對我們筆下的媽媽都如此不易,那麼對於更多不具備這些「優勢」的女性來說,她們所面臨的生命之重更是何其嚴峻。(作者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