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後玩家》:一半天使,一半魔鬼?蘇富比拍賣大師為你揭秘藝術背後的秘密!
〔英〕菲利普·胡克 著
陳瑤 譯
國內第一本聚焦傳奇畫商的藝術史,世界著名拍賣行蘇富比董事力作,獲《紐約時報》《衛報》《每日郵報》等媒體力薦!
一場從古典到現代的藝術盛宴,為你揭秘藝術品交易與創作、拍賣、藝術流派興起等前所未知的幕後故事!
與眾不同:幽默的語言、專業的知識、新奇的趣聞、先鋒的設計
20世紀20年代的傳奇畫商約瑟夫·杜維恩敏銳地觀察著有關藝術品銷售的所有細枝末節,他通過收集小道消息,買通了那些富有客戶的僕人,從而獲得他們主人的有效信息。通過這種方法,他發現男爵莫里斯·德·羅斯柴爾德,這個臭名昭著的獨裁者和壞脾氣的收藏家總是被慢性便秘折磨。於是,杜維恩在與他進行任何生意往來之前都會先明智地給他的貼身男僕打電話,以便了解男爵今天通便是否順暢。
約瑟夫·杜維恩,「當他在場時,每個人都像是喝了酒似的」。
所有偉大的畫商都無比關注細節。他們的堅持和謀略有一種英雄主義的情結,他們是開拓者。他們「行動如征服者、判斷如批評家、激情如傳教士」,這一狂熱的論斷是阿塞納·亞歷山大對印象派的藝術捍衛者杜蘭德·魯埃爾的評價;另一方面,馬塞爾·杜尚對畫商的評價則簡潔得多——「他們是藝術家們後背的虱子」。不過無論他們是征服者還是寄生蟲,或是介於兩者之間, 若沒有畫商,藝術的歷史將會迥然不同,也會乏味許多。他們職業的喜與悲都源於他們交易的這一商品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特性。
保羅·杜蘭德-魯埃爾,一個矛盾的男人。
藝術並沒有什麼實際用途。我想在最危急的時刻,一幅羅伊·利希滕斯坦的畫作可能會被水平掛在四根柱子上遮光擋雨,而一件亨利·摩爾的雕塑模型也會被當作一個門擋。我有一個朋友,當他沒有線捆住煮沸的平底鍋里正在烹飪的蘆筍時,便解開一旁伯納德·巴菲特畫框背後用來固定畫框的線來捆蘆筍,這是藝術品具有(間接的)實用性和精神性的罕見例子。但這並不是一件藝術品賣給一個買家的目的,哪怕是一件巴菲特的作品。不, 藝術的價值存在於一些難以量化的領域,它是由諸如美、品質和稀有這樣的概念所支配的。由於決定藝術品價值的往往是精神、智識和美學的東西,偶爾還混雜著社交和欣賞的目的,這也使藝術品成了有著令人困惑的彈性價值的一種商品。
羅莎·博納爾,《馬市》:甘巴特宣傳推廣的最成功的作品, 維多利亞女王也曾觀賞此畫。
因此,藝術品的銷售就落在了一個華麗而自由的疆域,在那裡,幻想為王。在某一條件下售價10萬美金的作品可能在第二天升至20萬美金(有時也可能會令人失望地跌至5萬美金),這都取決於誰在銷售它以及他們的銷售技巧具有怎樣的說服力。
畫商是幻想的宣傳者。我說的並不是在某種程度上不真實的幻想,而是那種可以刺激想像翱翔、讓精神振奮和撩撥高利潤投資的幻想。 畫商的版圖是一片至福樂土,它的一端是藝術品購買的價格,另一端是藝術品再出售的價格,這兩端的距離越大,畫商就越開心。當德拉克羅瓦將畫商描述為「神秘的金融家」時,他就認為每一件藝術品的成功出售都伴隨著幻想。我們都創造著屬於自己的神話,而畫商尤其深諳此道,他們在市場上提供了一個熱情大過理性、充滿誘惑力的幻想品牌。幻想無孔不入,有時它也經藝術品滲透到賣家自身,使他開始相信自己編織的神話。的確如此,那些最成功的畫商往往也最篤信他們自己的幻想。
小弗蘭斯·弗蘭肯,《造訪畫商》:17世紀早期像這樣的一間佛蘭德畫廊,已 經在為他們的客戶群提供一種結合豪華場景和藝術專長的「零售體驗」。
藝術品銷售就是說服人們去購買他們想要,但不需要的東西。當然,這是整個奢侈品行業都面臨的挑戰。但藝術與眾不同的是,你所經營的是一種超越技藝的、不可觸碰的、無法計量卻令人極其渴望的東西——天賦。這是一個神秘的要素,自文藝復興以來就在藝術的認知中傳承,只不過第一次被提出並被廣泛加以利用開始於浪漫主義時期。 藝術自19世紀以來就被公然視為天才之作,此時也恰好是畫商這一職業開始興盛的時期,這並不是一個偶然,因為天才是最閃耀,卻也最難以量化的價格附加值。
布尚司令收藏的普桑的《牧羊人的崇拜》,1956年在蘇富比高額保證金的前提下以2.9萬英鎊被拍賣。彼得·威爾森因此損失了6000英鎊,但他認為贏在宣傳。
羅伯特·休斯曾經寫道:「 一件藝術品的價值是非理性的、純粹的慾望指數。而慾望是最容易被操縱的。」曾經在1958年蘇富比的戈爾德施密特藏品拍賣上以破紀錄的價格拍到塞尚《穿紅背心的少年》的買家後來被證實是美國著名收藏家保羅·梅隆。當被詢問到他購買這件作品是否出價過高時,他的回答異常堅定:「當你站在這樣一件畫作面前時,錢又算什麼呢?」從字面上看,偉大的藝術作品已經被認為是無價的,這是一種虔誠的隱喻延展。藝術是21世紀的新宗教,購買藝術品猶如宗教信仰:它關乎的是一種信仰的行為。試圖對一件偉大藝術品的成交價進行客觀分析,就如同用科學推理的方法對宗教體驗進行分析一樣無效,這也就是保羅·梅隆所聲稱的無關聯性。這種無關聯性得到了保羅·梅隆這個在世界財富頂端中的重要且值得尊敬的參與者的肯定,成了畫商們為最出色的作品自行定價的絕佳辯護。
正如藝術市場史學家傑拉爾德·瑞特靈格所觀察到的:「只有在出現流動資本的情況下,人們才能將價值附加在純粹的天才上。」佳士得和蘇富比拍賣行也許可以把「當你站在這樣一件畫作面前時,錢又算什麼呢」這句話印在他們畫冊中待拍的任何一件佳作旁,這足以取代拍賣前的估價。
塞尚,《穿紅背心的少年》:1958年蘇富比的戈爾德施密特藏品拍賣中,該畫作以高價售出,英國作家毛姆、邱吉爾夫人親臨現場觀摩。
藝術品交易的歷史與藝術市場的歷史不同,畫商的個性是我們考察這一行業歷史重要的元素以及藝術品交易的關鍵,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一群魅力十足的男男女女投入他們的想像,以足智多謀和強大的說服力銷售著藝術品。藝術品交易的歷史也不同於藝術品收藏的歷史,不過如果對後者一無所知的話也是無法研究前者的。收藏家是畫商的顧客,如果對那些追求藝術的人的動機不了解的話,也就無法理解畫商所面臨的挑戰。有些收藏家主要是受投資利益的驅使,而另一些收藏家則把思想和美學價值放在首位。 我們或許可以用一個標尺來定義畫商,它的一端是謀利的商人,而另一端是學者,後者若不是為自己的收藏籌措資金的話是斷斷不會沾染生意的。所有的畫商都站在這一條線的某個位置上。之後的畫商們還被分為銷售老作品(由故去的藝術家們創作的)和經手並推動在世藝術家作品兩種,這也正是杜維恩和坎魏勒或卡斯特里的區別。
安德烈·德朗,《泰晤士河的風景》:畫家於1905年創作的最前衛的倫敦風景 系列就是聽取了安布魯瓦茲·沃拉爾的意見。
一個畫商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一個收藏家所購買的作品和當代趣味呢?畫商又能如何影響一個藝術家的實際創作呢?當他們在宣傳一個藝術家或一場藝術運動時,畫商究竟能如何左右藝術史,特別是現代藝術呢?本書試圖回答這些問題。儘管我已努力將著眼點聚焦於曾在這一領域做出過卓越貢獻的畫商,還是要對在這一研究篇幅里難以避免的錯誤和遺漏提前說聲抱歉。這裡敘述的都是這一領域中重要的畫商,由於我十分珍惜與藝術圈中同行的良好關係,因此我儘可能避免涉及依然健在的畫商。儘管如此,我依然希望這一關於藝術品交易演變的分析能夠為你們理解藝術史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
作者:[英] 菲利普·胡克
譯者:陳瑤
國內第一本聚焦傳奇畫商的藝術史
世界著名拍賣行蘇富比董事力作
獲《紐約時報》《衛報》《每日郵報》等媒體力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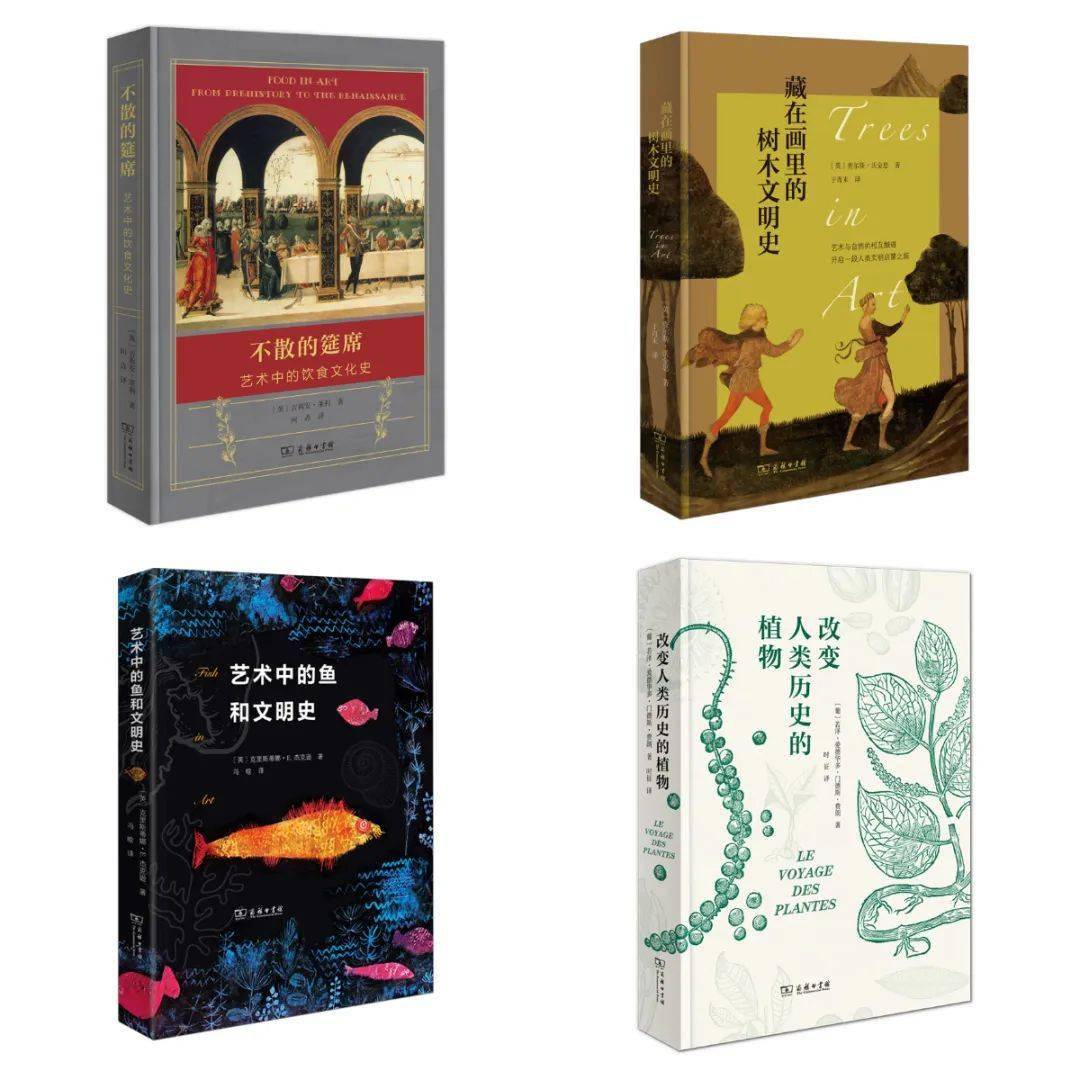
掃描上方二維碼
進入店鋪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