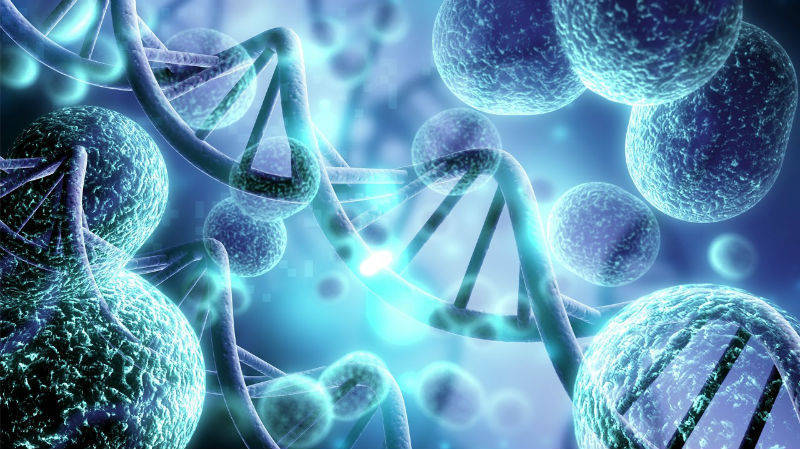
編者按:現在,讓我們把聚光燈對準中國基礎學科的研究者——數學家、化學家或者人類基因的研究者。
我們希望能夠拋開科技報道對巨頭公司和創始人個人生活事無巨細的關注,回歸到科研最基本的單元:科研者。
我們稱之為「賽先生說」,我們將以系列報道的形式展現他們的工作、生活和面臨的環境。
這些研究者是誰?在幹什麼?在擔憂什麼?面臨什麼?他們所做的事情,在世界範圍內又處在什麼樣的序列?
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構成中國科研的底色,並成為一個龐大經濟體未來前進的動力。
經濟觀察網 記者 張鈴 2024年7月底,在華人生命科學大會上,一位著名科學家正在演講,幹細胞生物學家鄧宏魁坐在台下聽著。突然,許多陌生電話打進來,鄧宏魁沒有接聽,把手機調成靜音。
不一會兒,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發來消息:「宏魁,有人找你,快去接電話。」鄧宏魁趕忙跑出會議廳。電話那頭告訴他:你將是2024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獲獎人。
接完電話,鄧宏魁在電梯上碰到方才演講的科學家,他問鄧宏魁:「我剛才演講的時候,專門提到你做的重要工作,你聽到了嗎?」錯過分享的鄧宏魁只好回應一個歉意的笑。
在學界同仁眼中,鄧宏魁有一個特別的標籤——幹細胞領域的魔法師。過去二十年,這位中國科學家不斷在幹細胞研究中取得新突破,幾次拓寬了再生醫學的研究邊界。有「中國的諾貝爾獎」之譽的未來科學大獎選中他,正是因為他在幹細胞領域的一系列關鍵性突破。
2024年8月16日,2024未來科學大獎正式揭曉。鄧宏魁的獲獎理由是「開創了利用化學方法將體細胞重編程為多能幹細胞,改變細胞命運和狀態方面的傑出工作」。
獲獎原因由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宣讀。王曉東說,每個人都是從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相遇的那一刻開始發育成長,直至衰老。有人類文明以來,從著名的秦始皇,到現在的矽谷大佬們,都夢想能實現返老還童,這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鄧宏魁在細胞的水平上給人類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路,做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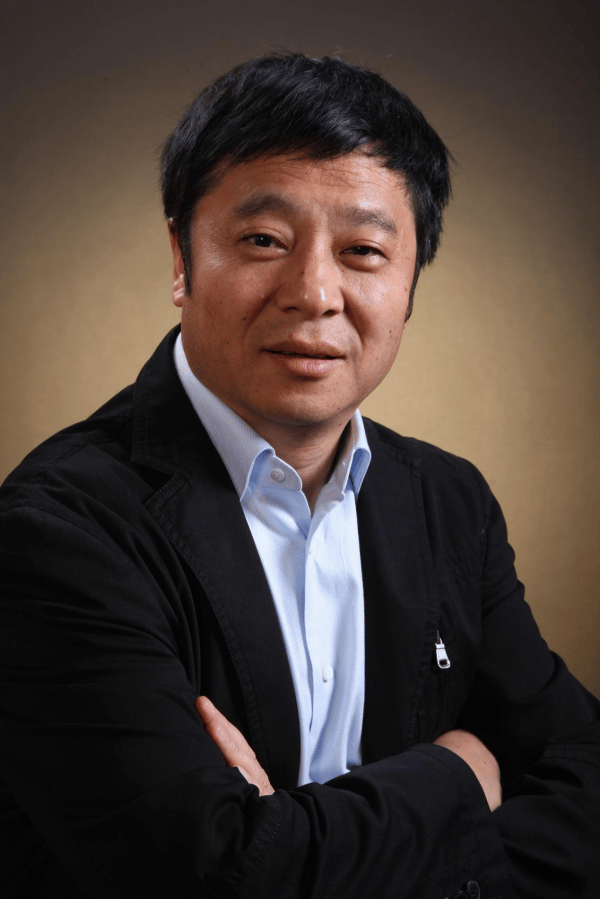
鄧宏魁 受訪者供圖
科學家一直在尋找能逆轉生命時鐘的辦法。胚胎髮育早期會出現有多能性的細胞,可以無限增殖、分化成生物體所有功能細胞類型,但其很快會分化為成體細胞,喪失「種子細胞」特性。過去幾十年,在細胞層面,科學家做到了把發育成熟的細胞從人體取出,使其重新回到原始狀態,成為多能幹細胞。第一個辦法是基於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的克隆,第二個辦法是基於轉錄因子的重編程策略,這兩個研究已共同獲得諾貝爾獎。而第三個辦法,就是鄧宏魁發現的化學重編程技術。
逆撥生命時鐘
在大獎揭曉的現場連線環節,鄧宏魁回憶起做幹細胞研究二十多年裡最難忘的三個瞬間。
第一個瞬間是在2013年,團隊首次在概念上證明使用小分子處理即可將小鼠體細胞誘導到多能狀態;第二個瞬間是在2022年,團隊化學重編程過程中發現人體細胞中激活的再生基因網絡;第三個瞬間是在2023年,團隊將體細胞重編程的多能幹細胞來源的功能細胞移植給病人,並在病人身上看到了有效性。
在1996年克隆羊誕生後,日本科學家山中伸彌又在2006年發現,通過四種轉錄因子可將成纖維細胞轉化為誘導多能幹細胞(iPSC)。然而,轉錄因子過表達的方法很難精確操控重編程過程,並可能導致隨機的基因整合和潛在的致癌基因表達,從而限制了其應用。
2013年,鄧宏魁團隊在《科學》雜誌首次報道了小鼠的化學重編程技術:不依賴細胞內源物質,僅使用外源性化學小分子就能將成纖維細胞轉化為iPSC的方法。這一研究開闢了全新的細胞命運調控途徑。
小鼠實驗成功那晚,當鄧宏魁透過螢光顯微鏡看到標誌著成功的綠色螢光時,他無法抑制情緒,獨自在樓道里反覆踱步。全新的研究途徑意味著全然的未知,為了這個瞬間,他已經探索了十多年。
標誌物散發出綠色的螢光受訪者供圖
鄧宏魁記得,研究一經發表,整個再生醫學領域都被震動——科學界沒想到用這麼簡單的方式就可以實現重編程。
在歡呼聲之外,質疑聲也隨之而來。由於小分子具有很強的靈活性,進行相關實驗時可變因素很多,一些科學團隊難以將實驗成功重複。
鄧宏魁沒有過多理會這些質疑,繼續探索如何實現人體細胞化學重編程,因為那才真正具有應用價值。與此同時,團隊也發表了一些工作成果,把小鼠重編程的效率提高了1000倍。質疑聲慢慢消散了。
「一個顛覆性的新生事物,要用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來體現它的價值,短期的噪音不用太理會。」鄧宏魁對經濟觀察報說。
9年後,鄧宏魁團隊的新科研成果再次震驚科學界。2022年4月,團隊在國際上首次報道了人體細胞化學重編程的工作,將化學重編程技術從小鼠多能幹細胞製備成功應用於人多能幹細胞的製備,並獲得人多能幹細胞。相比傳統方法,化學小分子操作簡便靈活,時空調控性強、作用可逆,可以對細胞重編程過程進行精確操控。
「通過簡單的化學小分子組合,是能夠逆轉生命的。」鄧宏魁解釋,通過化學重編程技術,一方面可以把人體成熟細胞在體外「返老還童」為種子細胞,一方面可以激活人體細胞的再生潛能,用以修復損傷、病變、衰老的細胞。
這一次,鄧宏魁團隊吸收了小鼠重編程研究的經驗,成果發表後,他們立即開始優化方法,在2023年就公布了效率更高的方法,並且研發了一款試劑盒供同行使用。
把不可能變為可能
從小鼠細胞重編程到人體細胞重編程,鄧宏魁團隊原以為很快就可以實現,因為原理是相似的。沒想到,這一步的跨越,一走就是9年。
人體細胞的穩定性更強,調控機制更複雜。鄧宏魁打比方說,如同跳高,要從1.6米提高到1.8米,看似只增高了20厘米,難度的變化卻是指數級上升的。為了克服人體細胞的穩態,在最初六年,鄧宏魁團隊篩選了多種可能性,但所有策略都失敗了。當時,業內也普遍認為,人類成體細胞的表觀遺傳限制極其嚴格,很可能無法通過化學重編程激發人類成體細胞獲得多潛能性。
一種低等生物給了鄧宏魁啟發——蠑螈。
蠑螈是再生生物學領域常用的動物模型之一。在肢體截斷之後約一個星期,蠑螈就能在截肢末端長出一團芽基組織,最後長出新肢體。這是因為蠑螈在受損傷後,體細胞會自發改變特性,在去分化的過程中獲得可塑性,藉助可塑的中間狀態實現肢體再生。
相比低等生物,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喪失了這種很強的再生能力。鄧宏魁團隊猜測,模擬低等生物,讓人類成體細胞重新建立可塑狀態,或許是突破的關鍵。
沿著這個思路,鄧宏魁團隊發現,高度分化的人成體細胞在特定化學小分子組合作用下,可以發生類似低等動物的去分化現象,並獲得有一定可塑性的中間狀態。
這是一個巨大的驚喜。「原來不同的生命現象是相通的,造物主還隱藏了一條可行的路。」鄧宏魁說,克服這第一步的障礙後,團隊以此為基礎繼續研究,最終實現了人CiPS細胞的成功誘導。
做科研時,鄧宏魁喜歡設定一個看似不可能的目標,在一個從無到有的旅程中,發現源頭創新。這樣的工作不必太擔心別人走在前面,有大把時間去試錯,但也需要耐心和長期堅持。
2001年,鄧宏魁回國,開始在北京大學從事幹細胞研究工作。剛開始研究化學重編程技術時,不僅外界不看好,團隊成員也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從回國到小鼠重編程的成功,鄧宏魁走了12年,團隊里有畢業要求的學生難免著急。
鄧宏魁的辦法是把目標拆解,直至拆解成不可拆解的小目標為止。可執行的小目標會一個個實現,增加學生們的信心。當小目標一個個實現,離總目標越來越近的時候,學生們的迫切感就會越來越強烈。2013年,成功實現小鼠重編程後,所有人都開始相信,自己可以「把不可能變為可能」。
不與多數人擠在一條路上
在博士和博士後期間,鄧宏魁研究的並非再生醫學,而是免疫學與病毒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博士導師Eli Sercarz和紐約大學的博士後導師Dan R. Littman,是科研生涯里對鄧宏魁影響最大的兩個人。
在UCLA期間,鄧宏魁的研究方向是自身免疫病。Eli Sercarz就患有自身免疫病,鄧宏魁問他:「你研究這麼多年自身免疫病,你要怎麼治自己的病?」
「宏魁,就像每台電視機都壞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沒法修,最好買個新的。」 導師回答他:「只有重建免疫系統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這個對話給了鄧宏魁很大啟發,他隱約感覺到自己應該研究再生問題。
Eli Sercarz幽默熱情,會用他能想到最好的詞彙鼓勵鄧宏魁,在科研方向上給他最大自由度。Dan R. Littman則是個嚴師。鄧宏魁初來乍到時,Dan R. Littman就對他說,有個重要課題,研究組已經做了十幾年,都沒有做出來,你敢不敢去挑戰?
鄧宏魁接受了挑戰——去尋找愛滋病病毒的受體。最終,他發現了HIV入侵T細胞的主要輔助受體CCR5,這是愛滋病的主要「幫凶」,有了它,愛滋病病毒才能破壞免疫系統。1996年,這一愛滋病研究領域的里程碑式進展在《自然》雜誌上發表。
這次成功後,雖然導師沒怎麼誇獎自己,但鄧宏魁的信心還是一下子提升了起來,此後遇到更有挑戰的課題時,他不再畏難。許多年後,當鄧宏魁在化學重編程技術上取得重大突破時,Dan R. Littman終於向他發來祝賀:「You are so lucky!」
完成博士後工作後,鄧宏魁連續見證了幹細胞和再生醫學領域的兩個重大突破。一個是1997年轟動全球的多利羊的誕生,這證明成熟分化狀態的細胞可以被逆轉回原始發育狀態,還具有產生一個新個體的能力;一個是1998年人胚胎幹細胞系的建立,再生醫學的大門由此打開。
鄧宏魁意識到:「這就是我未來想做的事,我應該進入新的賽道。」

鄧宏魁在實驗室 受訪者供圖
鄧宏魁不跟多數人擠在一條路上。對於年輕科研人員來說,沿著導師的路徑繼續走相對容易,但實現超越的唯一辦法是走到新領域去,長成一棵新樹。
博士後工作結束後,鄧宏魁在美國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工作了四年,積累了如何將基礎研究轉化到應用上的經驗後,他選擇回國,到北京大學從頭組建實驗室,從頭開展研究。
二十多年後,鄧宏魁團隊把化學重編程概念技術方法初步建了起來,下一步,他們希望把它做成一個廣泛可用的技術,還要探索用這個技術製備特定的功能細胞,用來治療特定的疾病。
鄧宏魁也沒有脫離學生時代的研究。進入再生醫學賽道後,他暗下決心:將來實現再生夢想時,要以此為工具繼續免疫學和病毒學研究。
2019年,鄧宏魁和合作者報道了全球首例利用第三代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在造血幹細胞上編輯他博士後時期發現的CCR5基因,並成功移植給一名同時患有HIV和白血病患者的案例。研究結果顯示,基因編輯後的造血幹細胞移植治療使患者的白血病完全緩解,攜帶CCR5突變的供體細胞能夠在受體體內長期存活已達19個月,初步探索了該方法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基於這項研究,鄧宏魁成為入選那一年《自然》年度人物的唯一一位中國學者。
在北京大學的實驗室里,鄧宏魁懸掛過一張照片,那是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表面踩下的第一個人類腳印。登月是人類的一大步,歷史會永遠記住它,鄧宏魁也希望做出在歷史上留下腳印的工作。
許多年過去,鄧宏魁覺得在他的科研生涯中,也有了值得被記住的畫面——11年前的一天,在培養皿一堆中間狀態的小鼠細胞里,多能幹細胞長了出來,標誌物散發出綠色的螢光。那一刻,不可能的事變成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