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慘了,吞下三噸口水才能看完一集「風味人間」。
看《風味人間》第二季的感受,叫做痛並快樂著。
每周日晚,晚飯消化殆盡睡意將起之時,《風味人間》第二季都會如期而至,用人類最原始的美食誘惑令人慾罷不能。瀰漫著迷人氣霧的甜燒白、流淌著該死甜美的崖蜜、散發著閃亮油光的燒豬、油色與糖色齊飛的巴克拉瓦……發一聲絕望的哀嚎,老實地在半夜十點打開外賣APP。
一見曉卿胖三斤,一聽李立宏誤平生。隔著美食,似乎能看到鏡頭後面陳曉卿的壞笑。
導演陳曉卿,配音李立宏,配樂阿鯤,三個長在中國人味蕾上的男人,又來聯手搞事情。
這一次,他們還請來了海報大師黃海一起放毒。連海報的紋理,都是好吃的顏色。
《風味人間》第二季
導演: 陳曉卿 / 李勇
主演: 李立宏
類型: 紀錄片
製片國家/地區: 中國大陸
集數: 8
開播之後,豆瓣評分穩穩占據9.4分,是無數吃貨如找到根據地的望斾來歸。
而在高分的背後,是陳曉卿帶領製作團隊,足跡遍布25個國家和地區,從鄉野到城市,從國內到國外,跨山川越湖泊,用8個主題,拍下300多道美食。匠心,是打造精品的第一步。
《風味人間2》為什麼好看?不僅因為它把食慾變成了視覺藝術,更因為它點透了人與食物的那點事,滲透著慾望、占有和見色起意,卻是天性與智慧的碰撞,感性與理性的共生。
原來,至味在人間。
1
美食,是舌尖的詩
「雞頭米老了,新核桃下來了,夏天就快過去了。」
汪曾祺這句話打在螢幕上的時候,驀然覺得一陣感動。
人與食物的關係,始於口腹之慾,生長於人類智慧的創造,終於日復一日的相伴與共洽。
《風味人間2》是少見的能把這種關係徹底說透的美食紀錄片。這種思路,得益於這一季的選題。從第一季講山海、講東西的紀傳體,到這一季專注具體口味甚至食材的編年史。
甜味、螃蟹、醬料、雜碎……或與人糾纏往復,或旁門左道後來居上,人類餐桌上的每一種滋味,都是一次偉大的冒險。
就比如螃蟹,「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樣的俗語,就是人們好奇,到底是怎樣的人冒著蟹鉗的威脅,尋見這種需要從骨縫裡找肉的極鮮美味,乃至發現了蟹黃和蟹膏這樣的至味。
《風味人間2》在佤族人的食譜里找到了蟹醬,這是人類吃蟹最原始的樣態,在2000年前的周朝,將蟹搗碎用鹽腌制的吃法,叫作「蟹胥」。
也有直到2018年才在食譜里躍升為新貴的「六月黃」。肥美的大閘蟹發生了變異,過度囤積的蟹黃流淌到了每一處骨隙,無處不透著油脂的醇香。殼薄黃多,蟹黃呈半流質,每一口都吃透了人對食物的所有想像。
處理這種食材,可以用最簡單的烹飪。寧波的熗蟹只用海鹽和水腌制,膏肥肉厚的母蟹體內,已經化為如果凍般軟彈的膠質。如果冰凍後食用,低溫下的紅膏與每一塊蟹肉依依相連。
那種蟹的鮮味,就是梁實秋所謂的「人人喜愛,無間南北,不分雅俗」。
也可以極盡奢侈飽腹之能事。美國馬里蘭州的藍蟹,可以只取蟹鰲里的大塊肉,加入黑胡椒等香辛料烹飪,每一口都是滿滿的「肉」欲與香甜。
又比如威尼斯人,小小的艾氏濱蟹不過硬幣大小,剛蛻殼之後全身透明。這短短几天內進行捕撈,裹上牛奶和麵粉直接油炸,入口「咯吱」一聲,焦香酥嫩。
全世界不同地域對同樣食材的理念各不相同,處理手法千差萬別。不變的,是凝結在食物里的巧思和用心,以及一代代人對美味如虔誠般的追逐。
它可以窮奢極欲,極工巧之能事。同樣的一味甜,鹽商重金栽培的淮揚菜在白案(麵食點心類)就仿佛藝術品。
翡翠燒麥,時蔬剁碎去汁水,加入白糖和豬油佐以食鹽,填補味道里的豐腴,放進麵皮團成斗狀,蒸熟之後,纖薄的外皮透亮如紗,翠綠的色澤仿佛水頭蕩漾的美玉。
千層油糕則以無數次的擀碾將糖與豬油層層溶解,點心的紋理能達到驚人的64層,芙蓉如面,綿軟甜膩。
這種美食的處理與上萬公里外的土耳其不謀而合,甜點王者巴克拉瓦,每一張麵皮的厚度不超過0.1毫米,上下疊加20層麵皮,配合奶酪和乾果,澆淋大廚才能掌握的熬糖,那一刻仿佛久別的重逢。
美食當得起廟堂之高,也從不拒絕江湖之遠。在四川鄉間的壩壩宴上,將紅糖與肥肉交疊放置蒸出的甜燒白,渾然散發著對甜與油毫不掩飾的渴求。而在四川長大的孩子,也會把這道只有在大宴上才能吃到的菜,當做最難忘的家鄉味道。
這就是美食寫成的詩,或工巧或平實,卻永遠滲透著人類最真實的慾望與情感。而《風味人間2》對內容的串講方式,將這些詩凝聚在了一幀幀令人無法拒絕的畫面上。
2
美食,是鏡頭裡的精靈
要留住這樣一首天然寫成的詩,需要最精妙的筆觸。而在這樣一部紀錄片里,「筆觸」代表著拍攝的技巧和取鏡的秘方。
對於如何展現美食之美,陳曉卿說過兩點:一是對光線、色彩、影調的運用,二是對食物的理解。前者是基礎,後者是升華。
20世紀最偉大的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曾說:「如果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而這句話可以說適用於一切紀錄類拍攝。《風味人間2》的近,近到仿佛食物就擺在你的鼻子下面。
不但是食物的樣子和色澤,鏡頭裡的美食已經細化到了紋理、質感甚至靈魂。
為了拍攝烤乳豬的表皮,攝影機被放到了恆溫300度的地爐里,只為捕捉麥芽糖在豬皮上發揮的奇妙反應。
第一季里就讓無數吃貨發出哀嚎的超顯微鏡頭則把這種近放大到了極致,比如拍攝霉豆瓣的時候,將鏡頭深入到食物內部的分子變化。於是,發酵的豆瓣竟化身為一片黃色的花田。

《風味人間2》的拍攝是分為兩部分的,首先是團隊到世界各地田野調查和取景,然後回到攝影棚,用大半年的時間拍攝這些食物最精微的變化。為了拍出這些食物的美感,設計感也是無處不在的。
比如為了突出六月黃蟹肉的紋理,抵近拍攝不說,更是「兩山排闥送『肉』來」。撲面而來的仿佛是蟹的醇香和熱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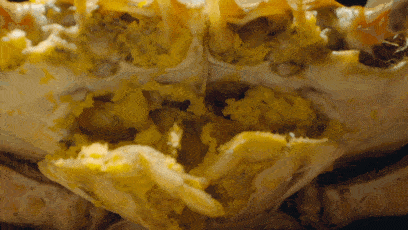
又比如,用各種動態視覺來呈現食物。怎樣讓看起來平平無奇的鷹嘴豆誘人無比?為了拍出讓觀眾印象深刻的畫面,拍攝團隊想了很多方式,嘗試了很多角度,最後使用旋轉鏡頭的方式拍攝豆子動起來的場景。
每一顆跳動的鷹嘴豆,仿佛都在用躍動的脆爽叫著:來吃我!

如是巧思,在整部紀錄片里比比皆是。用運鏡、布景和調色,《風味人間2》完成了將美食帶到每個人面前這一前提。
處理食物鏡頭的用心,對得起每一位在食物誕生過程中付出心力的人們。面對食物,這些拍攝者和片中的每個人同樣虔誠。
而這,或許是《風味人間2》真正走進每個人心裡的原因。
3
美食,是人間的靈藥
食物對於人來說意味著什麼?是生存必需品,也是生活調劑品,更是階層奢侈品。在小小的食物身上,凝聚著整個人間的過往、現在與未來。
《風味人間2》第一篇命名為「甜蜜縹緲錄」,似乎只需要聽到這個名字,就要被襲來的甜香沖昏頭腦。

但接下來的第一個鏡頭,卻恰恰讓人很難放鬆神經飄起來。
那是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采蜜人,他們每年這一時節會到絕壁上採集世界上最好的崖蜜。

兩百米高空中,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只有竹竿、藤繩、砍刀和用來熏走蜜蜂的煙球。
他們用竹竿釘進石縫來穩定身體,左腳尖勾住繩梯,右腳支撐刀具,然後點燃煙球,在瘋狂飛舞的蜜蜂群中,砍掉蜂巢的一半。只有一半,因為要給蜜蜂留下生存的巢穴和口糧。

這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之一,每年都會有采蜜人墜崖而死。但看到他們將最新鮮的蜜放入口中,露出滿足的笑,你很難判斷自己認為這種工作殘忍是否正確。

而這正是串聯起人與食物關係的第一站。正如第一季中的旗魚鏢手,他們在驚濤駭浪里拋出漁槍,這些驚險,就是人類與食物一代代相互糾纏、博弈的歷史。

甜味,曾和香料、鹽巴一樣,成為權力的象徵,吃糖就是權貴們最自矜身份的豪奢享受;螃蟹,曾經下里巴人攝取蛋白質和脂肪的無奈取食,如今卻是最頂級宴席的座上常客;豬蹄、頭肉和腸子肝肺,屠戶們都棄如敝履的下腳料,演變為而今全世界共同的食癖……

滄海桑田,口味在變,食物與人的關係不變,人凝結在食物里的情感不變。街頭一家小店裡,你隨手點要的幾味小菜,或許就凝聚著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一個菜系的興衰。
你或許在馬來餐廳里吃過沙嗲肉串,但你知道它與沙茶的故事嗎?下南洋的華人將沙嗲醬帶回本土,口味流變之後,成為潮汕火鍋的靈魂。

五十多年前,印尼華人劉瑞興操著滿口印尼話,帶著沙嗲醬的配方回到福建泉州。如今,他與妻子墨蘭花依然經營著沙茶小吃,子孫滿堂,生活平淡,而當年的異域口味,已成本土長情。

在香港深井經營燒鵝店的華姐,最拿手的是蘸燒鵝的酸梅醬。每家茶餐廳都必備的常見醬汁,在她這裡卻是具有潮汕記憶的別致滋味。這裡不但有華姐的父輩味道,更是許多潮汕人回味鄉情的尋味之所。

美食,成為人間的記事,也成為人間的靈藥。
美食,仿佛人間,苦辣酸甜,每一種味道都千迴百轉。
人為生存而吃,卻因為吃找到了生存的至樂。這樣的故事發源於尼羅河的文明肇始,至今卻在城市文明里依然找到其位置。

而在經歷了四個月的特殊時期之後,美食所代表的美好和煙火氣,更讓我們魂牽夢繞。
陳曉卿在節目開播之後,還特地寫了封信給觀眾們,心中說:「或許只有經歷了不尋常之後, 我們才知道生活里的那些觸手可及的日常,彌足珍貴。」
希望看完這部紀錄片,能像陳曉卿導演所期盼的,「讓我們重新回味世界曾經的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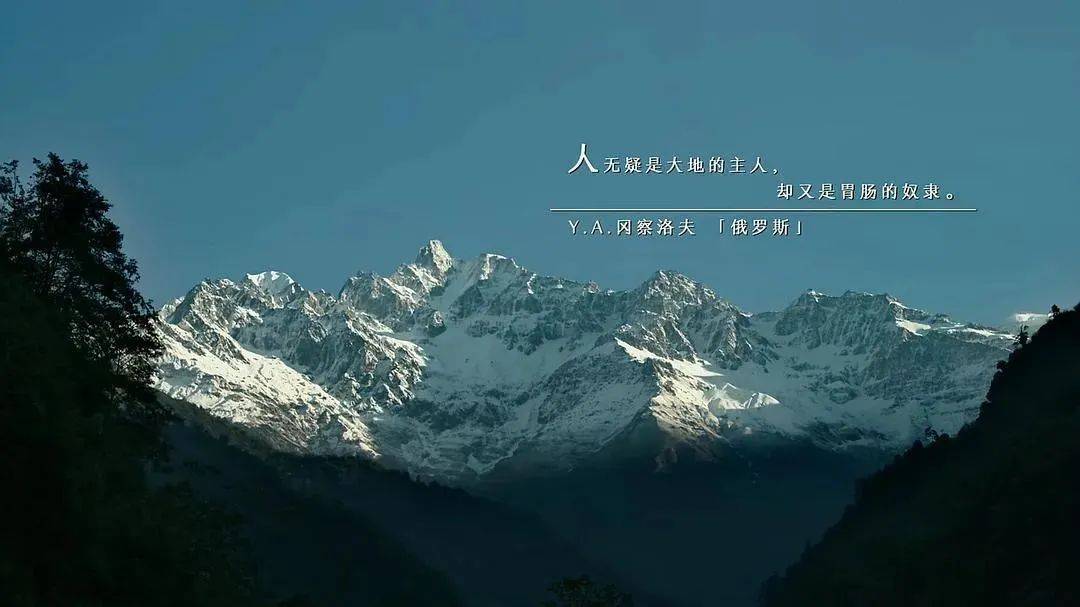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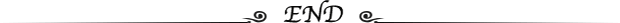
今日話題
你最愛吃的食物是什麼?
微博:@藤井樹觀影團2011
公號:藤井樹觀影團
「藤井樹觀影團」已同步入駐平台
| 微博 | 今日頭條 | 一點資訊 | 豆瓣 |
| 搜狐號 | 企鵝號 | 什麼值得買 | 大魚 |
| 趣頭條 | 虎嗅 | 百家號 | 新知 | 大風號 |
轉載聲明:原創文章請註明作者及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