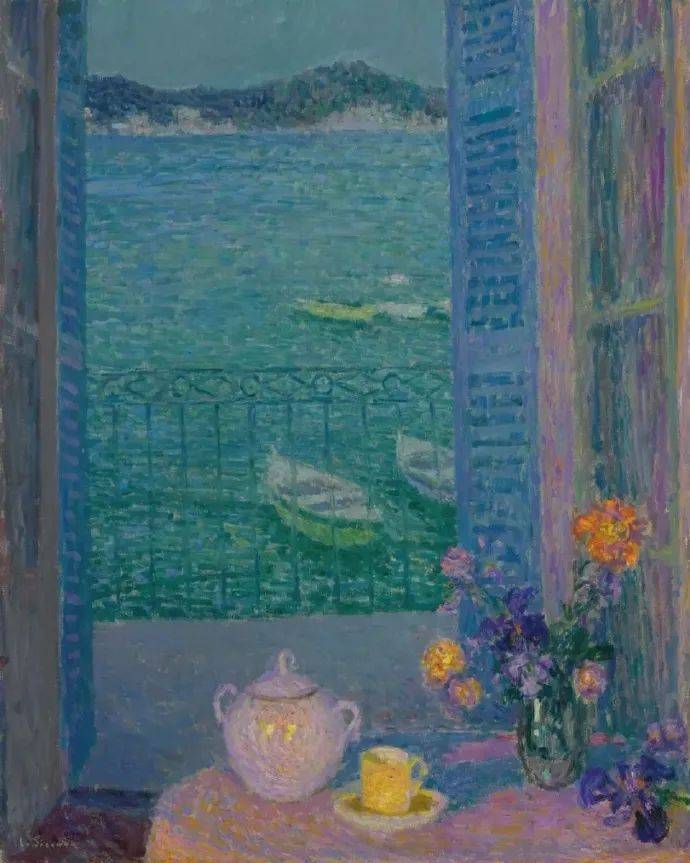
聖史蒂夫大教堂,是維也納舊城區最熱鬧的段落,莫扎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後一座拱門內的小巷,Domgasse 5 號,走不幾步,已在故居門口了。
1784 年,莫扎特與家人搬來公寓二樓,住了兩年半,寫出八部鋼琴協奏曲,還有偉大的《費加羅婚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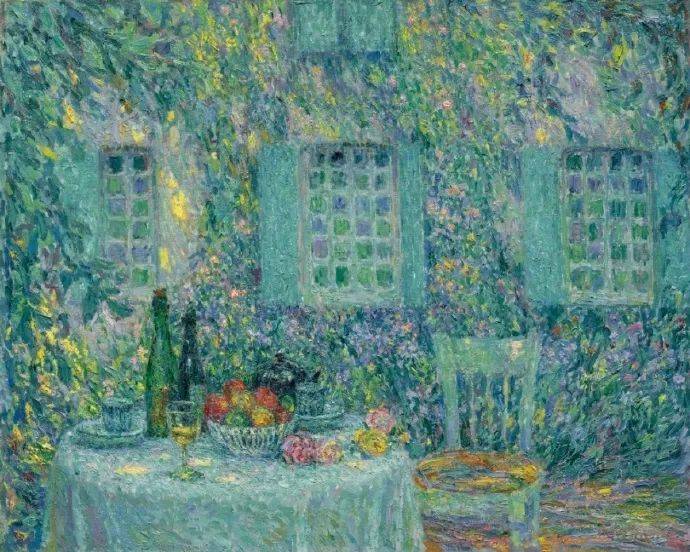
這裡闢為紀念館,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來,室內設計的美學幾經變換,現在的裝置,顯然被上世紀 90 年代成熟期的後現代模式,徹底動過了。
窗前豎著莫扎特放大的側影,每間房間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與實物的燈箱櫥窗,停著他遺留的琴、手稿、樂譜、書信、節目單、小玩意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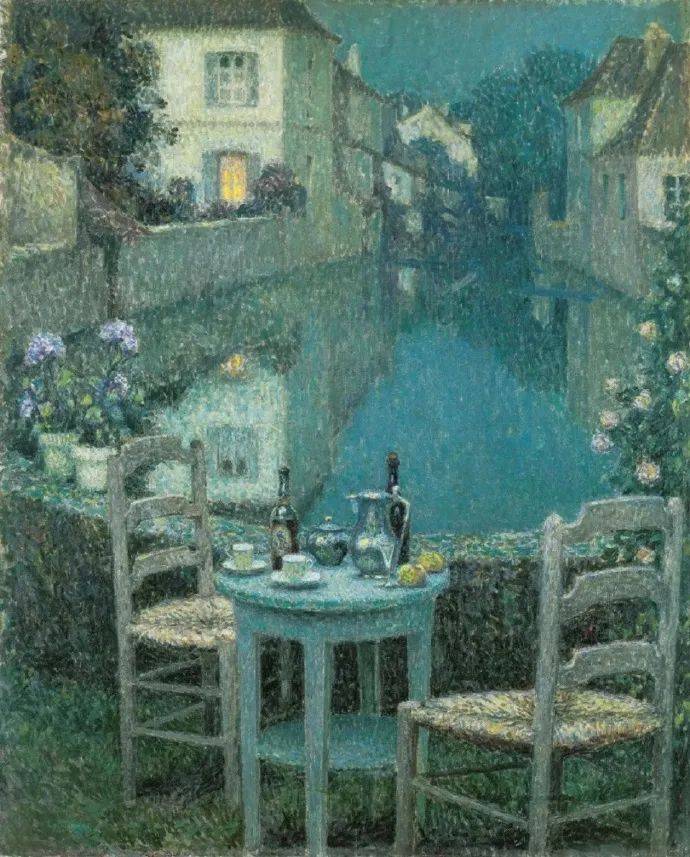
第一次看見莫扎特的死亡面膜翻制為青銅版(我不願相信他如電影中那麼戲劇性地死去),藍光照著,不像他的畫像,一臉貴氣,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
「為什麼你寫得這麼好?」他被問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為什麼這麼大。」——現在靜靜瞧著莫扎特的鼻子,要是沒玻璃隔著,伸手即可觸摸。沒那麼大,很好看,修長,飽滿,隆起,不過死者的額骨鼻骨都是隆起的。

最好看的,是一枚狹長的燈箱輪,番閃動著他的著名歌劇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台影像,無可形容,如他的音樂般高貴而開心——這不像莫扎特住過的家,而是一項展覽,他成為今日設計者百般調弄的素材。
惟在窗前俯瞰樓下的舊街巷,我心裡莫扎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經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鋪路馬車經過。離開時又在樓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據說海頓曾來這裡看望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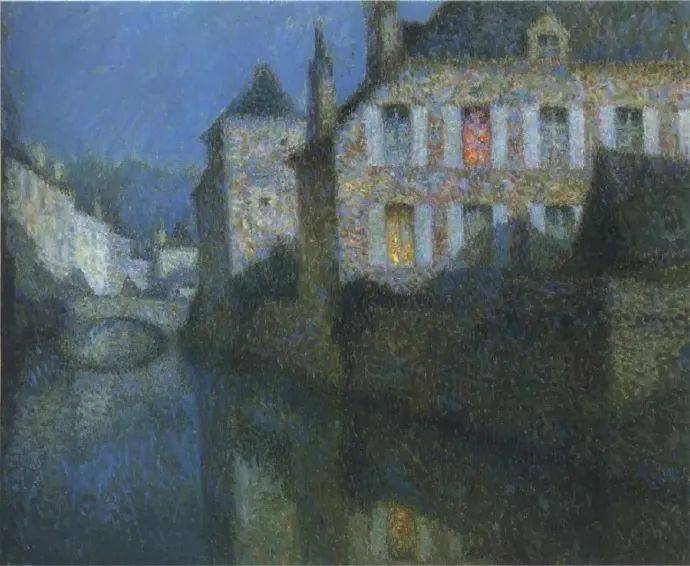
1784 年,莫扎特 28 歲,海頓 52 歲,小伙子會在這兒迎候海頓嗎?我在樓梯間看見這一老一少了:腦後的假髮束聳著蝴蝶結,脖梗襯著層層翻卷的高領,彼此擁抱,親吻,笑,說著我聽不懂的德語——
「我以自己的榮譽向您發誓,您的兒子是我所聽過的最偉大的作曲家。」當海頓對著莫扎特的父親稟告這段話,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間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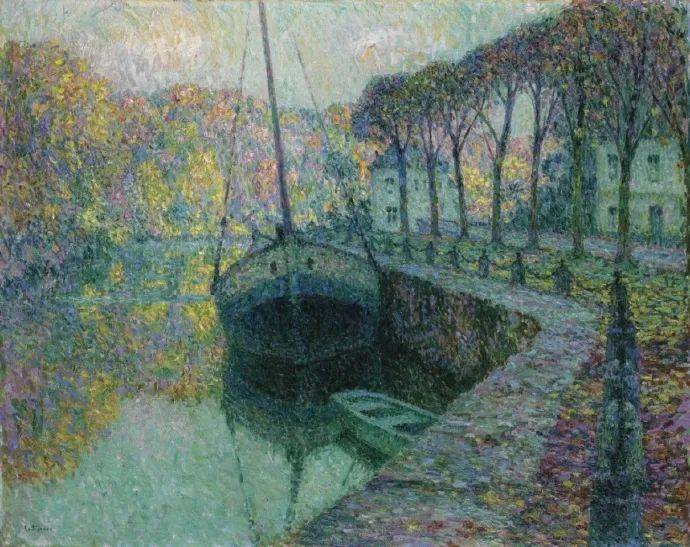
探訪故居的翌日,謝天謝地,謝天謝地,我得緣觀賞《魔笛》,神魂顛倒。他們從未死去,在一句一句歌唱中,就是他,正是他。怎樣描述這聆聽?那時不知一年後又能來到維也納,又寫一篇文章。
初到兩天,我迷失在藝術史博物館,自以為並非為了音樂來到維也納。離開那天,我已忘了城裡的繪畫。猶如發生重聽,在維也納的最後一天,耳邊總是《魔笛》演出現場的二重唱與三重唱。

真的人聲。難以承受的美。牒片的聲效,總難分辨每條喉嚨的質地和方位,非得在現場。這座城遍布音樂的蹤跡,郊外是他們的墳墓,城裡留著他們的故居,一年四季,每天每夜,全城的音樂廳上演他們的曲目。
停留幾天,豈能了解維也納。我沒打聽馬勒、布魯赫那、史特勞斯、貝爾格,還有勛伯格的遺蹟在什麼地方。我只是奇怪,仿佛私人的疑案:我怎會在貝多芬家的昏暗樓道,興起和維也納毫不相干的聯想。
提問
Qustions
&
解答
Answers
Q
記著:傅聰以前來上海講學,他把莫扎特比作李白,把貝多芬比作杜甫,把舒伯特比作陶淵明,把蕭邦比作李後主,又說亨德爾是「革命的浪漫主義」。
用「比較」來理解西方音樂是個好辦法。您看繪畫與音樂有沒有可比性,比如把畢卡索比作斯特拉文斯基?把凡高比作……
陳丹青:我以為不可比,比則兩傷。傅聰來把李白比莫扎特,一定有他私下的心得。但唐詩與歐洲古典音樂,都是偉大的「公共財產」,再怎樣個人的解讀,都不免「交付」給「公共印象」。
李白世稱「豪放」,那已是唐風的別稱(蘇軾的「豪放」就大不同);而莫扎特的「公共印象」殊難以「豪放」一句概括。即便時有「豪放」氣,也非「拔劍四顧心茫然」、「明朝散發弄扁舟」這樣純然中國士大夫式的情懷。
莫扎特大量段落的跳宕銜接,運用洛可可宮廷音樂傳統的「諧謔」手法,那種高貴的調皮相,也不見於李白的詩風。
莫扎特晚期作品,傅聰說近於莊子,倒有點意思的。但他說莫扎特「不說教,完全是愛」,然而莊子及道家的學說,哪有「愛」這回事:中國文化根本不講什麼「愛」,中國人講「情」,但這「情」與西方文化中的「愛」,不是一個意思。
A
本文節選自陳丹青《外國音樂在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