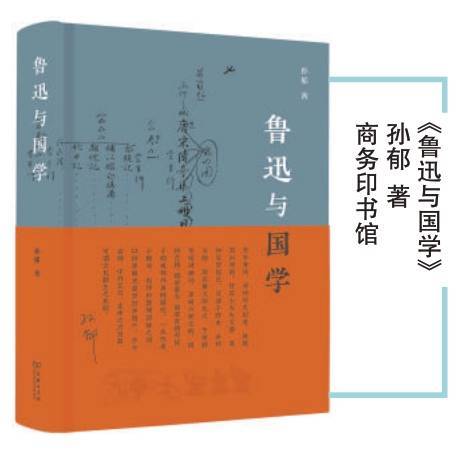
易文傑
魯迅的「反傳統」觀念常被批評,如林毓生認為魯迅是一位全盤否定傳統的人物。對此,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反思了魯迅「全盤反傳統」的學術觀點。他認為魯迅雖然在思想觀念上是「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在感情上卻依然對此有所依戀。然而,在學者高遠東看來,這種觀念雖然有所洞見,但是仍然忽視了魯迅對中國傳統的批判性繼承。不少優秀的魯迅研究者對「魯迅與傳統」進行了意味深長的探討,指出魯迅與舊學的關係,比我們所想像的豐富得多。魯迅的思維也從來不是單線條的,而是豐富的。
魯迅智慧多來自古中國文明薰陶
實際上,魯迅與中國古文明的關係是頗為複雜的:從小讀各種舊書,筋骨、魂魄都浸潤其中。長大後想要擺脫其弊害,但幽靈如影隨形,字句中不經意流露出舊學的血脈。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中,魯迅更對舊學進行了改造,使之成為適合現代中國的「國學」。在這一點背後,牽涉到古今轉換的重要問題:魯迅作為新文學的傑出代表,如何把傳統之物轉化為現代精神,是值得探討的。
因而,如果需要把握魯迅文學、思想的要害,「國學」是一個離不開的角度。研究者對此雖有所探討,但從整體性視角出發的研究尚不多見。孫郁的近著《魯迅與國學》就是這麼一部從整體性視角出發,探討魯迅與國學之間辯證關係的佳作。孫郁向來關注魯迅先生的「暗功夫」,即魯迅為文背後的知識結構。該著更發微抉隱,從金石學、考古學、文字學、文學、哲學、民俗學等多個視角重審魯迅對舊文明的現代重構與發明,體認魯迅的逆俗筆墨與深藏於文的「暗功夫」。
魯迅如何理解國學?該書開卷第一篇《從新知到國故》,道出了魯迅的獨特眼光:魯迅是從「新知」的現代視野入手,重新反觀「國故」的。而他的視野,也並非囿於儒學一隅,而是以清明的眸子重新凝視古文明的元氣。他的文字絕非朽木,亦不見酸腐的呆氣。如書中所言,魯迅的「非學院派」視野,與陳寅恪、馬一浮等儒家士人是迥異的,背後是「現代性的元氣」,「在經學之外另闢蹊徑,思想有另一個原點」。這也正是為何魯迅能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端,以《狂人日記》發出嚆矢之聲。
因此,該書所強調的「魯迅的智慧多半來自古中國文明的薰陶」,並非指的是魯迅文學、思想的復古性,更絕非把魯迅視為一位遺民式的儒者,而是指魯迅基於現代的眼光對古文明元氣的再發明,所謂「正像尼采從古希臘文明中吸收了智慧一樣,魯迅的智慧多半來自古中國文明的薰陶」。看似偏至之言,實際上是周全的。
在孫郁看來,魯迅「避開了儒學正宗之路,而發現了文明史中的另一種資源,即所謂『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正是」。魯迅對傳統的思考路徑,與尼采相類似——「復古」之路上,絕少不了「取今」,而「復古」的目的,也正是為了「別立新宗」。而魯迅之所以能發現古文明的美質,是因為百年大變局中的中西升沉,「當歐洲文明在自己的世界中出現的時候,他對於故國的舊有的形態才有了另類認識。」所謂「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是魯迅獨特的文明觀,也正是本書的根本用心所在,最後其實指向的是對「立人」與「人國」的追求,「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
國。」(《文化偏至論》)如是而已。
以「取今復古」眼光重審先秦諸子
魯迅「取今復古」的眼光是如何重審中國古文明的?這體現在對諸子資源進行了重審:挖掘其在先秦時的元氣,抵抗其在後世異化的暮氣。
魯迅對先秦諸子的敏銳眼光,如孫郁所言,也受到其師章太炎的啟發。在該書第十四篇《對章太炎學識的取捨》中,有意味深長的表述:「(章太炎)在言及莊子與佛學、儒學的時候,差異里的相似性被一一道出,確是不凡的思路……我們由此聯想起魯迅論述孔子、莊子的思想,以及隱士、俗士之關係,邏輯幾乎一致。」魯迅對先秦諸子的看法,確與其師章太炎相似,都是用「重估一切價值」的思路,摒棄那些被後世捧上神壇的木偶,拒絕那些士大夫的格套,尋找那些本然之所。這點在全書第五篇《非儒與非孔的理由》中,有較為充分的說明。在孫郁看來,在後世,孔子的思想多異化為了舊儒的暮氣。因而,魯迅對那些異化的士大夫禮教話語多有抵抗。他從來就警惕那些重來的故鬼,拒斥那些尊孔的幽靈。但是,魯迅的境界實在與先秦時期的孔子有相似之處,那就是都「不以世俗的是非為是非,都是逆風潮而動的人物」,有一種「超俗的人間情懷與思想境界」。只是較之孔子的克己復禮之思,魯迅更推崇戰士的姿態。
該書第六篇《對莊子的另類敘述》,也呈現了魯迅以「取今復古」的眼光重審諸子學的思路。在孫郁看來,魯迅對莊子的理解,來自尼采式的眼光。魯迅汲取了莊子辭章中飛動的色彩,學習了《逍遙遊》等篇章中天馬行空的思路,從而鑄造了屬於魯迅自己獨特的辭章。然而,魯迅對莊子的文學、思想絕非盲從,在其小說《起死》之中,多有獨到的反思。魯迅對莊子的批判,其深處是沉重的現實感,有著來自大地的氣息,寄託著對新的知識階級的渴望。
魯迅不只對莊子有所省思,也對墨家的思路有所肯定,並將墨家視為一種精神資源。《魯迅與國學》的末篇《晚年文本的墨學之影》就指出,在晚年魯迅的《故事新編》文本中,突出了對墨家苦行精神的肯定。這與其說是體現了魯迅對古人的解釋,不如說是他借墨家的精神,來深切觀照現實,昭示了魯迅對左翼文學、思想的體認,以及對「新人」的想像。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魯迅對舊學的再造,意味著從中華歷史中挖掘出真正的民族魂。對國學,他有自己的鐵肩擔當與不息堅守。當中華文化「花果飄零」時,他是當之無愧的中華文化守夜人。
亦對民間傳統有著深切的體認
在孫郁看來,魯迅這一「取今復古」的文明觀,不僅重釋了諸子學的意義,也對民間傳統有著深切的體認。
從民間的角度閱讀魯迅,是孫郁一貫以來的學術志趣。從民間視角來看魯迅的國學,也能打開許多問題。本書第九篇《批判舊戲的幾種理由》就從民間視角出發,體現出豐富的意味。孫郁指出:魯迅的戲劇批評,也是其文明批評的一種,蘊含著大的文化關懷。具體來說,魯迅對京劇等舊藝術多有批判,是因為他以為這些屬於儒教的舊戲,都還在陳舊的意識形態里。相反的是,魯迅推崇那些民間的戲劇藝術,認為這些藝術有新鮮的氣息,屬於天籟之音。這種觀念在他的文本《社戲》《五猖會》中,歷歷可見。在魯迅看來,新的戲劇藝術需要汲取域外的資源,從而敞開對傳統的理解,在民間的土壤中取得生機。概言之,魯迅對傳統的看法,並不拘泥於廟堂之上的大傳統,而是對民間江湖的小傳統也多有會心。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魯迅與國學》也與近年興起的「魯迅文明論」研究,產生了富有意味的對話。這些研究多過於強調魯迅早年的思想,對魯迅思想的整體性有所撕裂。而《魯迅與國學》對魯迅文明觀的探討,是從魯迅的留日時期出發,貫穿於魯迅一生(包括20世紀30年代寫作《故事新編》)的討論,具有整體性的視野與思想史意義。在本書看來,魯迅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實踐及其文明觀,所呼應的是魯迅早年留日時期所形成的文明觀,其用意都是「取今復古,別立新宗」。這讓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魯迅思想的整體性與豐富性。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