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趙培:《尚書》的經典化之路是漫長而艱辛的
考古學之外,我們對於傳統社會(圖像、電子記錄時代之前)的系統了解基本上是依靠口傳和文字記錄,前者不穩定,故以後者為主。文字記錄的主體是文獻,文獻中最重者為典籍,尤其是與傳統社會發生過劇烈互動的「經典」。文字的出現和應用是革命性的,經典的形成也是一樣,它們都是塑造傳統的利器。文字系統的出現對於人類記憶方式的革命,已太過久遠而難以具體言說。經典的誕生,與之相應的傳統之形成、變化、延續,以及傳統對於經典之回塑,卻是可以去描寫、重現的。同時,經典與傳統中國互動背後的動力系統亦可藉此揭櫫。經典成立的舊問題為何要被重新激活?傳統中國經典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模式有何獨特性?傳統中國圍繞經典展開的文化意識形態建設活動背後的動力源泉是什麼?《書經》成立過程有何獨特性?圍繞這些問題,我採訪了《〈書經〉之成立》一書的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教授趙培。

趙培
李林芳:儒家典籍經典化不是一個新題目,經學時代已有系統論說,作為這本書的論題,是哪些因素將舊問題重新激活的?
趙培:的確。儒家典籍經典化的過程,經學時代實屬不證自明之問題,聖人定經,門生傳教,官方認可,本為一體(聖人雖有孔子、周公兩說,北宋慶曆以來,雖遞見疑經之論,但此類現象,皆以經學重要為前提,是基於「求真經,證聖道」的立場而展開的)。五四以來卻又是學界主流極力「否定」的問題。所謂的「否定」,非言當時否認《尚書》曾經為經典。當時的學術主流認為傳統中國所尊奉這些經典的行為方式是錯誤的,故所討論的問題尚走不到經典如何形成這一層面上來。那時學界的主要動力在「去聖」「去經典化」。像15世紀以洛蘭佐·瓦剌(Lorenzo Valla,1407-1457)為代表的西方古典學者,藉助以語文學(Philology)、歷史學為基礎的古典考據學,從文本研究上對過去發起全面的進攻一樣,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學者們,對唐以前的相當一部分典籍進行了真偽推定,確定了一大批「偽書」。孔子和經典的關係被極力淡化,漢以來的經典生成之說,也如同商代以前的古史一樣,被「推翻」了。古史辨派雖然沒正面討論典籍經典化問題,但正是他們的辨偽企圖使得典籍經典化成為一個新的學術問題。可以說,重新討論儒家典籍經典化問題是後經學時代重構經典與傳統關係的必然要求。
此外,儒家典籍在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清華簡與相關出土資料的不斷公布,則是我們重新討論經典化問題並以《書》類文獻和《書經》為聚焦對象的直接刺激。當然,個人志趣也一直在發揮作用。我個人對古典文獻專業既有研究範式的不滿足,對古典傳統的好奇和對古典精神的探尋欲,促使自己選擇了由「《書經》成立」切入展開對經典與傳統關係問題的討論。
李林芳:就研究對象來看,能簡單談一下早期典籍經典化研究涉及到哪些問題,主要研究目的和現階段主要任務是什麼嗎?
趙培:關於研究對象和論域限定,我的處理方式是以典籍早期形態分析為基礎,著重分析典籍形成過程所對應的社會背景及其傳播所帶來的思想文化意義。典籍形態的演化、流傳渠道和方式的轉變,經典的誕生,不是簡牘篇章的機械拼合,而是跟時局之轉、文化之變以及新的思維模式和社會群體的出現等因素直接相關。
具體到《書》類文獻自身,所謂的「早期形態」可分為三大方面:載體形態、文本形態與「經傳」形態。載體形態,我們的討論對象基本限定在竹、木、帛、紙等書寫材料,《書》類文獻的載體規制,及青銅器銘文和《書》類文獻的關係等方面。文本形態,為了顯明其獨特性,我們將文字形態從文本內容中分離出來。就《書》類文獻的文本內容而言,除了描述篇章數量、定名及分合、章句異文外,我們將重點討論這些內容所反映出歷時性文本的層次性特徵,及其跟文本流傳之間的關係。文字形態,涉及字跡、用字分析(字詞系統研究)和字形形態的歷時性變化,及諸類特徵在文本衍生及流布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經傳」形態,所謂經傳,實則是經典成立之後的講法,所以此處用「經傳」為取其義之廣。例如《國語·周語下》載叔向用《周頌·昊天有成命》,叔向略早於孔子,以其解《詩》之辭,校以《毛傳》,訓釋無差,而叔向之解更為詳盡。所別者,叔向此處強調《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而《小序》但言「郊祀天地也」,可以見出儒門經典成編過程中,對王官和貴族《詩》學的繼承和損益。朱熹《詩集傳》據叔向說,定《昊天有成命》為祭祀成王之詩,似已混淆官私之學。由叔向、毛傳到朱熹的傳解上即可見出「經解」形態之變遷,而這種變遷又同經典的文本形態直接相關,故而我們整體上以「經傳」形態稱之。

《〈書經〉之成立》書中關於《書》類文獻早期形態研究內容的插圖
另外,出土文獻越來越豐富,為「古典學重建」提供了較以往更為堅實的基礎。可以說,分析古書演變的諸多現象,探析這些現象所關涉到的傳統變革、文化轉向、政治形態、學派意圖,關注傳統中國典籍經典化歷程的獨特性等更深層問題,是目前經典化研究的主要任務。
李林芳:您在書中重點討論了前經典時代的典籍形態,實際上關於前經典時代典籍的形成演進,已有一些成說,您是如何處理這些頗具張力的不同論說傳統的?
趙培:我們說儒家典籍的經典化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近代以來經學的瓦解。經學時代的一整套講法,包括對經典形成的認識,喪失了神聖性,沒有了權威性。前面提到,後經學時代的學術主流認為傳統中國所尊奉這些經典的行為方式是錯誤的,主要動力在「去聖」「去經典化」。伴隨著經典的完全史料化,古史辨派學者開始了重建古史的努力。回溯過往,我們能夠發現,古史重建作為中國史學的重要話題之一貫穿整個20世紀,一直延續到今天,其對科學材料和科學方法的推崇直接催生了近代中國考古學。古史辨派及其後學的史料辨正,考古學對古史的物質性還原,為我們的經典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與近代科學考古學相伴隨的,不僅有方法和學科的革新,更有大量出土文獻,後者為經典化的研究提供了直接材料。
由於這些歷史原因,我們在處理經典化問題的時候就天然面臨著三重張力:一是觀念張力,前後經學時代對經典的敘述不盡相同,經學時代對經典化有具體論說,後經學時代則經典地位大不如前;二是方法張力,一方面需要對近代以來的反傳統的方法加以反思,另一方面又要尋找新的話語描述早期文獻的經典化過程;三是材料張力,面對新材料和新學科,需要探索辨偽和重建傳統的新路徑。如何尋找新的話語和探討新的路徑,我們嘗試「折中」諸說:經學時代的講法並非全無道理,古史辨派的文本考證亦有其價值,考古發現同傳世文獻互有補充,亦非格格不入,三相結合,去非存是,將硬考證和軟觀念彌縫起來,勾勒出經典自身形態演進的軌跡以及其同傳統互動的脈絡。
相較於在科學實證主義的庇蔭之下進行碎片化散點分析,我個人覺得勾勒一些由線條所組成的簡筆畫更有意義,對前經典時代典籍形態的分析和描寫即是如此。書的章節安排依照時間邏輯(時代)遞進,但是每一部分的問題聚焦點不同。整體言之,前兩章我們試圖討論系統化的文字和延續性的歷史書寫前後的《書》教。西周以前,《書》的形態尚未完全定型,但是《書》之功用是可以梳理分析的。口傳和抄傳問題同樣不容易具化分析,但口耳與竹帛及其所對應的文化系統的興衰輪替之趨勢則是可以把握的。《尚書》中的「夏書」諸篇,一般認為其出現比較晚。但是《尚書》中「夏書」的早晚同夏代有沒有《書》類篇章,是兩個問題,應該區別對待。我們無心也無力去證明今存「夏書」為夏代之舊,但是我們亦不同意將其看作絕對晚出的物件。夏晉重都(都城區域有交集),加之「夏書」諸篇中的晉文化留痕,使我們可以推斷出一個「夏虛誦古」的傳統。
商代的《書》之形態研究面臨同樣的問題。存世「商書」是否當時篇章並不是問題的重點,我們更關注商代的書寫及其性質、商末理性之光等問題,因為這些是商代之《書》是否存在的必要條件。商代書寫文化,尤其是商末敘事性書寫的湧現,顯示文字書寫對巫文化的反動,意味著《書》教的性質開始轉變。西周的《書》,我們著重討論《訓典》和《書》的名實之轉。通過梳理有限的早期記載,我們能夠發現,就其功能而論,宗周代代傳承的《訓典》(彙編),可謂最早的《書》類文獻;就其「實」而言,稱名逐漸被《書》、《書》的具體篇名和類名(《夏書》《商書》《周書》)所替代。換言之,《書》類文獻的彙編形態的名與實發生過一次變化。由《訓典》而成了《書》。就《國語·周語上》所載從穆王到幽王的十數條推測,《書》從《訓典》系統中獨立出來當在厲王以後,最晚至宣幽之際已經存在。
李林芳:書分上下編,上編重點分析了相關研究方法,在研究儒家典籍經典化問題上您是如何看待中西方研究傳統及其研究方法的?西方古典學(語文學)的相關研究能夠提供哪些啟示?
趙培:儒家經典的產生、演變和確立有其獨特性,但經典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卻有著普遍性。換言之,經典化是一個世界範圍的文化現象,不同文化中,其發生過程,既有獨特性,亦有相同之處,是可以進行類型化研究的。類型化研究的可行性意味著這一研究領域的國際互鑒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上面提到,我們的研究是從兩個方面展開的,即早期形態研究和經典化過程分析,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對前者的深化和升華。就研究方法而言,兩部分是有所區別的。這就意味著,兩部分研究中可取自的西方資源也有差別。
典籍早期形態研究方面,可以互鑒的是西方古典學和語文學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豐碩的研究成果。1923年,胡適在為《元典章校補釋例》(陳垣著)所撰之序中談到西方校勘學之「三長」(古本多、譯本多、諸本易得),提醒我國學者留意「他山之石」。胡適的論說切實分析到了東西方校勘學差別之根源,然而在隨後的半個多世紀中,胡適的呼籲並未得到回應。因為語言和研究對象上的差異,東西方古典學方面的交流很少,相互借鑑更無從談起。西方古典學被正式引入我國是近四十年的事情,但是真正以之作為視角之一切入到傳統中國典籍研究中的成果依然不多。即便是熟悉西方古典學傳統的漢學家,也並沒有為我們提供太多研究範例,華格納教授(《王弼老子注研究》的作者)就曾批評道:「在現代的海外中國學研究開始的時候,人們期待它們會從歐洲古希臘和羅馬的經典研究中那些給人印象深刻的文本批評或文字學的方法論中汲取方法上的指引。在相鄰的領域——梵語研究中,情況正是如此。然而,西方學者在中國發現了有眾多學者參與其中的清代考據學傳統,其中的許多領域(如音韻學),達到了極為精深的水平。這一中國學的傳統迅速吸收了某些西方文本批判的方法,尤其是與辨偽問題相關的那些。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就是顧頡剛等人編輯的七卷本《古史辨》。而其他一些重要的西方文獻學要素,如批判性文本,則沒有成為中國學學術實踐的部分。除極少數例外,日本或西方的外國學者並沒有進入這一在質、量和歷史等方面都擁有如此優勢的領域的意圖。這一可悲的結果,致使時至今日,甚至那些最為基本的中國經典文本也沒有值得信賴的批判性版本。連和Oxford、Teubner或Loeb的西方經典著作系列相匹敵的東西都沒有,就更不用說有關《舊約》、《新約》的研究了。」(華格納著,楊立華譯《王弼〈老子注〉研究》,第4頁)華格納教授對西方漢學研究者的批評,實際上也暗示了中國學者對西方古典學傳統的忽視。其所言「批判性文本」,中國學者並非沒有相關意識,傳統經學的傳注著作中,很多都有此類批判性還原的努力,只是相對於西方「批判性文本」那樣大張旗鼓的做法,傳統中國的處理方法則略顯零散。但差別或許正是在處理方法上。系統性的實踐類研究,如段玉裁所撰之《毛詩故訓傳定本》,即為批判性還原毛傳及毛傳本《詩經》而作,但是相較於西方批判性文本,層次過於單一了些。
因為西方古典學自身的豐富性,加上引介者個人或群體偏好有差別,國內關於西方古典學的譯介整體上多偏政治思想類典籍或相關研究,文獻類的相對較少。國內學者中真正在中西文獻研究方法上開展系統比較的是蘇傑教授,2009年他編譯了六位西方古典學家(A.E.豪斯曼、保羅·馬斯、路德維希·比勒爾、W.W.格雷格、G.托馬斯·坦瑟勒、傑羅姆·卡茨)的八部論著,彙編成《西方校勘學論著選》,首次比較用心地呈現了西方校勘學的一角。稍後,其又翻譯了G.托馬斯·坦瑟勒的《分析書志學綱要》一書,首次系統地引進了西方的「版本學」論著。蘇傑的研究拉開了中西古典學深度互鑒的序幕,對我們重審經典文本及其流傳過程等相關問題多有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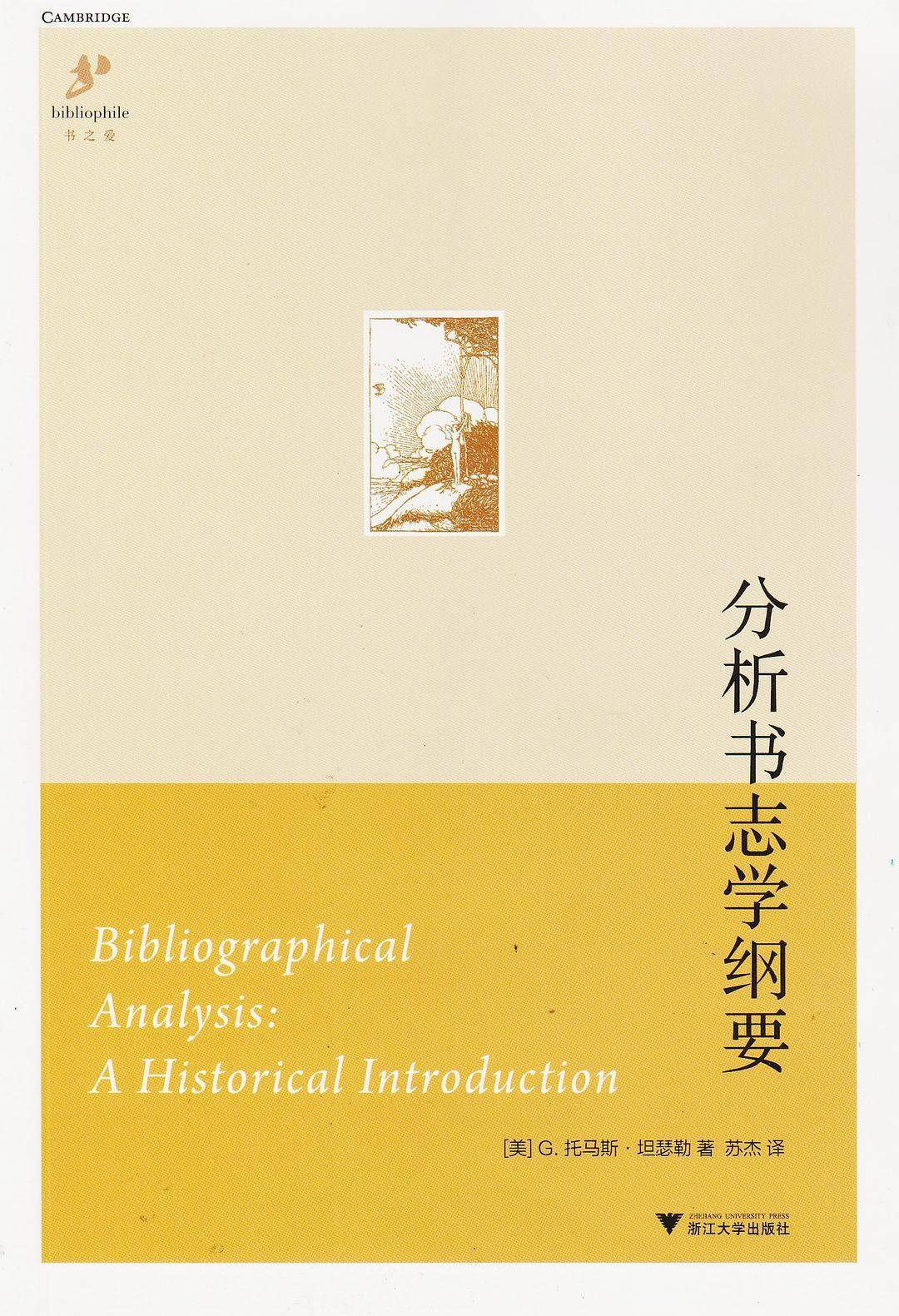
《分析書志學綱要》
與古典學相關的主要學術門類為Philology(語文學)。語文學是從文獻學和歷史語言學的角度,通過對古典文獻的考證、詮釋和評註,目的是為了讀懂古代文獻,通過古代文獻來研究古代的書面語,及其所反映出的文化和文明信息。語文學包括四大主要領域:語言學、修辭學、文本語文學(文獻學)和語法學。從西方語文學的發展來看,語文學又分古典語文學、近代語文學與新語文學三個階段。單就校勘學而言,根據來國龍的分析,新語文學同近代語文學(例如製造「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典籍的「Lachmann Method」)的差別,是兩種「範式」(paradigm)的不同:「新語文學對傳統語文學的主要批評是在很多情況下(尤其是在早期,如西方的中世紀時期),這個「原始文本」的假設只是現代學者架構的空中樓閣,是一個根本不能成立的假象。純粹的「原始文本」不但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而且,即使存在過,這樣的文本也可能不可得、不可知。而在過分追求復原「原始文本」的過程中,研究者往往忽略了文本流傳過程中的抄手、讀者、改編者和寫本使用者(他們是所謂「雜質」的製造者)的歷史作用和歷史體驗。……新語文學也被稱為「物質性的」語文學(Material或artifactual philology)強調了對寫本(manu),而不僅僅是抽象的文本(text)的研究,試圖通過寫本的全面具體的研究來了解當時的寫本文化及其社會歷史背景。」(來國龍《通假字、新語文學和出土戰國秦漢簡帛的研究》,賈晉華、陳偉、王小林、來國龍編《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第101-102頁)西方新語文學的興起,其所倡導的方法及所得出的新的認識,對我們研究先秦兩漢典籍生成、流傳,以及文本異文所反映出的文本流傳同當時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等方面皆有啟發意義。當然,新語文學所得出的,相對於傳統語文學的新認識,如將注意力從「原始文本」移到文本流傳過程上來,更多關注抄手、讀者、改編者和寫本使用者的歷史作用和歷史體驗等等。某種意義上講,經典化本身即是文本流傳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個互動環節。
經典化問題的關注重點是經典在文明形態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與之直接相關的是文明形態理論方面的研究。2015年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訪問,第一次見面,柯馬丁(Martin Kern)教授就推薦了揚·阿斯曼(Jan Assmann)教授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一書的英文版(德文原版1992年出版,2011年出英文版,2015年出了中譯本)。就經典化研究而言,這本書在文明進程模式類型研究和構建方面可謂開創先河。阿斯曼教授從文化記憶理論入手,探析了文明演進和生成過程中的一般性與特殊性,其中關於經典在不同文明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不同文化通過對經典處理方式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傳統等方面的論述,頗具啟發。該書以Maurice Halbwachs(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文為基礎,闡述了記憶的文化維度。其通過探討記憶、身份認同、文化的連續性三個方面之間的關係來論證己說。記憶即關於過去的知識,身份認同關乎政治想像,文化連續性主要涉及傳統的確立和維繫。除此之外,該書關於西方哲學、人類學、古典學和古文化研究領域代表學者的經典著作及其主要觀點的利用和點評,亦有助於我們深入到更廣闊的西方古典研究及相關領域中去。
在中西比較的視野下,我們嘗試搭建早期典籍經典化研究的方法框架和理論體系。我們以文本層次分析為基礎,討論傳世文獻背後之潛在古本研究、傳統傳箋中涵蘊的古本信息等問題,並進一步提出共時文本和歷時文本的概念。從方法層面來看,經典化其實是在「承繼傳統,匯合諸法」的綜合性要求外,確定了一個更有利於明晰古書及古代學術特點、立體的突顯經典生成過程中諸多因素互動的思考和研究維度。此一維度,實際上是建立在對傳統和近代三種主要研究路徑的反思基礎之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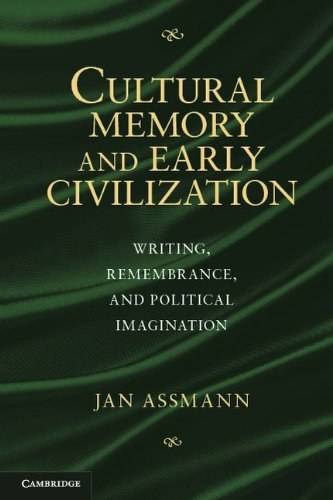
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李林芳:請簡單勾勒一下《書經》的成立過程,其同傳統文化的形成、變化、延續之間的關係,以及新舊傳統對經典的回塑。
趙培:經典成立問題部分屬於觀念史的研究範疇,部分屬於傳統經學的研究範疇,所以討論經典成立問題,必須儘量貼近古人的觀念邏輯,必須努力進入到傳統經學話語體系當中去。這是研究問題自身所決定的。
據傳世《尚書》諸篇之自指時間,它們從三代而來,是當時王官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周末年,王室微而禮樂廢,王官下移,《詩》《書》之學散在民間。春秋晚期居住在魯國的孔子,感慨世亂道息,試圖通過整理王官舊典,廣開學路,通過文化與教育手段來重整天下秩序。他的主要手段是整編與「製作」,整編是條理王官舊典,製作則是附義於魯十二公之事跡。所謂的「附義」是指他折中三代文化,取其政道思想之精華,然後來刪述製作,即司馬遷所謂的「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孔子製作的特點是「約其文辭而指博」。經過孔子的整理與製作與孔門授受,王官舊典均被賦予新義,各得其所。之後,戰國縱橫,真偽紛爭,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儒分為八,墨別為三,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再後來,宗周既滅,六國並秦,牢籠諸子,以吏為師。「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浸興。」至此,《五經》由諸子學而復歸王官學。
三代以前一直到西周,是《書》學的奠基期,鋪就了《書經》的底層色調。《書》類文獻屬於王官之學的組成部分。從《堯典》的「觀象授時」部分,我們依然能夠窺探到來自4000多年的信息。天學在古代中國起源之早,系統化程度之高,是疑古學派的人所難以想像的。《堯典》中的很多知識,如「出日」「入日」、「四方神與四方風」等,其三代損益的軌跡是可以簡單勾勒的。冠名《商書》的很多傳世篇章,其文本中所涵蘊的知識同我們見之於出土材料的商文化特徵可以互證,時移勢遷,很多內容不是後世模擬者憑空揣摩出的。西周的《書》就更不必說了,其間晚出痕跡,多有流傳所致,而非晚出。就其功能而言,西周時期,厲王以後,晚至宣幽之際,當有一次《訓典》與《書》的名實之轉,我們認為《書》的彙編當在這段時間。早期《訓典》當屬於《書》類文獻,可知《書》類文獻的彙編或當更早。
東周時期,是《書》學子學屬性的注入時期,《書》所具有的王官學與諸子學雙重個性正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孔子及孔門弟子的整編與授受,將作為宗周政典的書,轉化成儒門經典。《書》的經文與傳解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系統化」和「儒學化(子學化)」。孔門托之以「從周」,用「仁義」「君子」以改宗周「明德」之義涵。一姓一族之德,與一姓一族之「受命」,被個人化、純粹道德化,「明德」與「天命」之關聯性亦被極力弱化。或許這並不是孔門儒生有意為之,東周以降,諸侯力政的局面下,「德」不配「位」本是社會現實,無須造作為說,順其自然即可。儒、墨既顯於諸子,挾先王以爭後王,彙編典章,聚徒以授,遂成一派之經典,人文亦大興。
秦滅六國後,禁絕家言,牢籠諸子,儒家《書》學遂和其他諸子學遂被新的王官學吸納。但是秦二世而亡,漢鑒秦過,在文化政策上改弦易轍,於是再次進入「新王官學」系統的儒家《書》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遺憾的是,經歷過了「道裂」「學墜」「學分」「經殘」「改經」的《尚書》,其內蘊的諸多面向、各個層次均已有殘缺,無論是先王之政典還是聖人之治道,皆非完璧。《書經》的成立之路是漫長而艱辛的:王官學屬性,因天子史官而損,又因諸子編訂而「隱」;子學聖道屬性,因「儒分為八」而損;新王官學屬性本就立足於殘經與師缺的基礎上,雖然漢代官方傾力搜納、廣立學官,但終究根基不穩。然而作為宗周舊學的《書》,對於大一統王朝的象徵意義非同一般。於是兩漢官方搜逸典、立博士、開太學、設郡學,導以利祿,以殘經立學,遂實現了官方《書經》地位的確立。與此同時,兩漢時,諸子遺風依舊存在,承其於續者主張「希聖」「創經」,「襲舊六而為七」。更有因經殘而主張「補經」以全道者。總之,《書》中所內蘊的王官學與諸子學的張力第一次展露無遺。我們說漢代《書經》「立而未成」,正是基於此而言。大一統王朝希望經典傳解標準化,並能夠有利於於王朝統治。諸子後學,尤其是孔子的追隨者,則以追尋聖道為己任,反對經學的利祿化、平庸化、繁瑣化。兩種力量在經典文本內外互動博弈,推動著傳統經學的發展。
《書》來自古老王官學的經典隨著群經一樣波動著自己的「成立」。當然,《書經》的成立也有著自身的特殊性。經歷了「道裂」「學墜」「學分」「經殘」「改經」,在漢以後又經歷了永嘉喪典與東晉的「偽經」「偽傳」,命途實在是多舛。就《尚書》之流傳,孫星衍有「七厄」之說:「一厄於秦火,則百篇為二十九;再厄於建武,而亡《武成》;三厄於永嘉,則眾家《書》及《古文》盡亡;四厄於梅頤,則以偽亂真而鄭學微;五厄於孔穎達,則以是為非,而馬、鄭之注亡於宋;六厄於唐開元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並《偽孔傳》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真;七厄於宋開寶中,李鄂刪定《釋文》,則並陸德明《音義》俱非其舊矣。」經此「七厄」,今傳《尚書》可以說是「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反觀「七厄」,我們發現孔穎達主持《尚書正義》編定及其推廣,蔡沈《書集傳》的撰成及其立學,亦可以看作《書經》之「成立」,前者將偽孔經傳官學化,後者則別立宋學之《書經》。儘管如此「波動」,但是當我們提到《書經》的時候,沒有人對他的「成立」表示懷疑,儘管也沒有人能說清楚自己心目中《書經》的「成立」究竟指的是哪次「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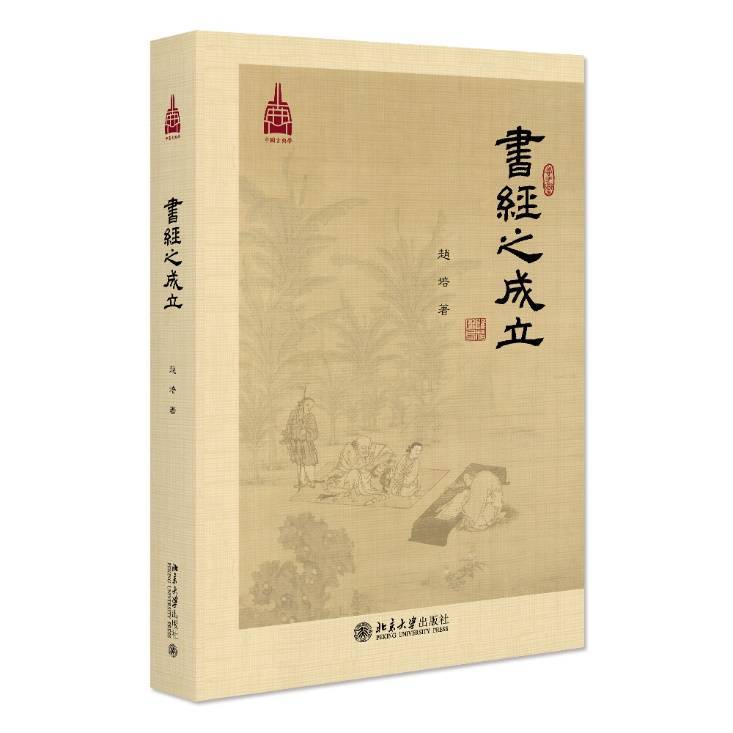
《〈書經〉之成立》
李林芳:系統分析了《書經》成立的相關問題,能不能請您談一下,如何返回到經學的歷史現場?能否談一談經學演進的內部動力源泉及其秩序模式?
趙培:關於經學演進內部的動力源泉及其秩序模式問題,我們曾經嘗試提出一個「經子和合」的概念。我們用這個概念來強調儒學的經子雜糅性,經與子為儒學的一體兩面,是對立與統一之關係。儒學自身的「經子和合」特性決定了傳統中國文化歷久彌新不斷發展的。
何為「經子和合」?我們從司馬遷對孔子的贊語談起。司馬遷《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中言:「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諸子百家當中,儒家學說最接近宗周的王官學,其繼承了宗周的《詩》《書》古學並試圖復歸當時的禮樂文化。這一特徵決定了儒學自身的內在張力,這種張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孔子折中諸學以「還原」宗周舊學。宗周舊學隨著天子失官,其原貌已不可盡知。《左傳·昭公十七年》載: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正義》曰:「仲尼學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是聖人無常師。」孔子問職官於郯子,即是其例。又《漢書·藝文志》所錄「仲尼有言曰:禮失而求諸野。」則孔子實際上並非宗周學術的最理想傳人,他「好學」且「無常師」,主張「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將所學折中在對經典的「再詮釋」中,試圖「復位」宗周文化。二是宗周舊學折中於孔子。儒門尊經,因為孔子雖然「述而不作」,但他通過講學奠定了(也是「限定」)經典的解釋,所以司馬遷言後世儒生學習經典又需要以孔子為歸宿。
武帝以來西漢王官之學的重建,表面上是崇儒,實則是尊王,武帝想要恢復的實際上是宗周王學,而非孔門家言(所謂「家言」,指的是諸子百家之私論)。如此,則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孔學和宗周王學之間是什麼關係,二者能否等量齊觀?二是後繼帝王能否準確把握崇儒和尊王之間的界限,若不能,又會出現什麼問題?據《漢書》載,元帝「柔仁好儒」宣帝就曾擔心,「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裡宣帝將孔學與宗周王學等同,認為其只講仁義,而漢家制度則是外儒而內法。若結合第一個問題,那麼即便是「純任德教,用周政」也難以純一,因為「周政」依託孔學而傳世。當然,這裡涉及到獨尊儒術後,王官與家言的矛盾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諸家之學各有特點,但作為整體,相對於宗周王官之學而言,他們又具有很強的自新精神。新興諸派學說中,充斥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如儒家和墨家對禮樂文化的態度、儒家和道家對出仕的態度,法家與儒家在治國理念上的差異,等等。這些矛盾和衝突,顯示出新興文化的活力。就連一直宣揚復古、擁護舊制度的儒家,在舊制度業已崩壞的情況下,也需要不斷地重新解釋宗周的文化,為其尋找現實的合理性。孔子晚年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成「天子之事」,「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而「亂臣賊子懼」。如此則《春秋》更是順時順勢而為,《春秋》學最能體現儒家的子學屬性。
當然,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後,其子學屬性逐漸被壓制,作為經學的儒學與子學在官私立場上開始對立。如《漢書·宣元六王傳》載東平思王劉宇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與《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可以見出當時對諸子書和《史記》的警惕,諸子和經學分判甚明。據此,我們就容易理解揚雄雖然繼承了儒學子學屬性的精神內核,但在《法言·吾子》中言「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睹其識道也」,拒斥諸子的緣由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儒學內部的子學屬性的潛存,呈現出一種「經子和合」的狀態。
「經子和合」的狀態反映出儒學的多副面孔:就其經學一面而言,作為獨尊之學,確實存在尊經傾向,經典的權威性與典範性不可褻瀆;就其子學屬性而言,從孔子開始就樹立了一種好學且無常師,折中六藝,創製經典的儒家聖人形象。孟子希孔子,處亂世而辟邪說。僅就這一面向而言,後世之儒所可繼承的儒學遺產是非常豐富的。孔子、孟子作為聖人的示範作用,使後來的希聖者不僅行聖人之所行,並且行製作之事:創經、擬經、續經、補經。因為後繼「希聖者」重視的面向不同,使得儒學呈現出多種形態。加上政治環境的變化,其間既有歷時的差異,又有共時的不同,所以在儒學史上我們看到了董仲舒的「折中陰陽」,揚雄的「雜取黃老」、擬經與重學,王通的擬續經典,韓愈的闢佛老與重構道統,柳開的「肩愈」(宗尚韓愈)與補經,石介的以韓愈比肩於聖人,程朱的暗取釋氏以成新儒之學,等等。因為側重不同,即便是「希聖」一方的儒者對經典擬續增廣問題的認識也有差異,這種差異最直接地反映在後世對韓愈、揚雄、王通、柳開等人的評價上。
道統建構同儒學的子學屬性直接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儒學子學屬性的外顯的必然結果。這種子學屬性最直接的體現是道統提出者往往會依照「希聖」的標準將自己放在聖道統序之中。儒學的子學屬性的彰顯,使得對聖道原貌的追尋逐漸超越了對經典原有架構的遵從,加上漢代重建的儒學經典系統原本就存在缺陷,所以理學家們逐漸開啟了以《四書》統領《五經》的新儒學轉向。當然,我們應該注意到,新儒學自身體系的完備使得在部分理學家,尤其是朱子後學看來,揚雄、王通、柳開等擬補經典者在道統中的位置也是需要重新審視的。儘管如此,就其經學實踐的邏輯基礎而言,理學家和擬續經典者其實處在儒學發展的同一脈絡中。
揚雄、王通和柳開諸人皆自命為聖人之繼承者。相較於揚雄和王通,韓愈身上已經展現出了新的面向。揚雄和王通的「希聖」,基本上是「走老路」,像孔子那樣通過擬經、創經來「繼聖道」「治亂世」「明賞罰」,其「發揮」基本上還在基於原有的五經架構。但從韓愈開始,儒學開始了心性轉向。但是到了二程和朱熹那裡,韓愈也被排拒在道統之外。程頤以程顥直接接續孟子,朱熹則是在二程之前添上周敦頤《宋史》載黃干之言:「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除了程朱的道統說外,陸九淵認為自己承孟子而繼道統,其《與路彥彬》載:「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無論是程朱,還是陸九淵,其所提出的道統說都將漢唐經學的傳承一概抹殺了,或言覺得其「學統」無益於「道統」,千餘年來未能得聖道之真。對漢唐「學統」的否定式破壞意味著需要建構新的學統,以《四書》為綱目的新儒學知識統緒便隨之確立,這裡我們看到了一種儒學的子學屬性對以經學屬性的反作用。朱子依照其道統說,收集周、張、二程等人的相關資料編纂而成《伊洛淵源錄》,依照四庫館臣所言,此書出後「《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多據此為之。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派,亦自此書始。」又萬斯同《儒林宗派》提要中館臣言:「《伊洛淵源錄》出,《宋史》遂以道學、儒林分為兩傳。非惟文章之士、記誦之才不得列之於儒,即自漢以來傳先聖之遺經者,亦几几乎不得列於儒」,可見其貌似成統,實則造成了道統與學統的分裂,理學道統表現出很強的排他性,其間非但沒有漢代經師的位置,荀卿、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等人,也全都出局了。
「經子和合」強調儒學的經學與子學的雙重屬性,因為這一特點決定了我們是否能夠真正進入中國經學,甚至傳統文化的演進歷史當中。當然,我們不能忽略掉儒學作為經學的一面,正如我們不能忽略掉很多反對擬續經典的聲音一樣。揚雄之時,即有這樣的聲音:「諸儒或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也。」僭越和侮聖是反對者的主要論點。但是我們要清楚認識到,經學成為官學,成為利祿之學後,作為考核或考試的標準,其可發揮空間非常有限,自身活力與自新能力均大為減弱,長此以往,經典與聖人、聖道的距離越來越遠,最終有官而無學。縱觀整個經學史,儒學的子學一面上揚之時,往往是其調整自新之時,一變而通,顯示出巨大的能量。可以說儒學之子學屬性增強了其現實適應性,是其不斷「當代化」的動力之源。討論儒家經典化問題,不能忽略了儒學「經子和合」的特徵。正是這種特徵,使得儒家典籍經典化顯示出別具一格的獨特性。透過經典化問題來重新認識經學史,重新定位經學史上的節點式人物,才能真正穿過歷史的迷霧,洞悉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
最後,當我們從「經子和合」的角度來看待儒學發展與傳統中國文化演進史的時候,能夠發現經典就如同土壤一樣,不同朝代的中國人以此為根基,播種耕耘,革故鼎新,不斷化成新的時代文化,展現新的時代風貌。當然,這些土壤也為傳統中國文化設定了邊界。然而隨著經學時代的瓦解,我們在舊壤中摻入了更多更有營養更肥沃的新壤。「經子和合」的傳統精神提醒我們要播下屬於這個時代的種子,這種不斷「當代化」的自新精神,古今一揆,最值得我輩寶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