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已是『半機器人』,你的手機和電腦,都是你身體的延伸。」去年12月1日一場發布會上,馬斯克如此說。
根據這位科技巨頭、世界富豪的解釋,「如果你忘記帶手機了,你還是會去摸口袋,這就像肢體缺失綜合症。忘記帶手機就像是缺少了一個肢體,你已習慣於與它互動」。他的意思是要進一步說明,人類如果要應對人工智慧(AI)並與之共存,最大的限制是——能多快地與計算機互動。
在發布會現場,由馬斯克和8名聯合人創立的神經科技和腦機接口公司Neuralink,展示了如何讓一隻猴子用「意念」打出「歡迎來到展示和講述活動」的字樣。馬斯克當時更是承諾,將在半年內獲得批准,開展「無限大腦晶片」的人體臨床試驗。
前世界首富這次沒有食言。當地時間上周四,Neuralink宣布公司已獲得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批准,將啟動其首個人體臨床研究。
Neuralink在社交媒體宣布,將開展人體臨床試驗。
這意味著Neuralink將會把他們的設備植入人體大腦中。因為馬斯克自帶巨大流量的「體質」,這個消息引起了外界極大關注。實際上早在2021年,另一家研發腦機接口技術的公司Synchron已獲得批准開始進行臨床試驗,它在澳大利亞對四名患者進行測試,並在今年1月發布早期研究結果:受試者通過意念成功發出文字信息,無需打字過程。
馬斯克曾雄心勃勃地宣稱,研發腦機接口技術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全腦介面」,在未來它能夠與人類的整個大腦連接,而在短期內讓其可以與人體大腦特定部分對接,幫助失明者及脊損傷等疾病人群重獲生機。
普通人想知道的是,這個「短期」是指多長時間,腦機接口技術還有多久可以大規模應用於臨床?
腦機接口技術(Brain Computer Interface)相當於將腦電信號轉換為控制指令,可以幫助運動功能障礙患者如腦卒中、漸凍症等與外部設備交互,從而提升生活質量。
01
「已知宇宙中最複雜的物體」
為了弄清大腦的奧秘,千百年來科學家和醫學家們可謂費盡心思。人類的感覺以及身體活動的指令來自何方?它整個工作機制的過程是怎樣的?人的情緒、意識、思想、學習與記憶等認知行為,居所又在人腦哪裡,它是如何受到大腦影響的?這些問題像神奇的複雜迷宮一樣,引誘著人們的好奇心。然而即使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智者也得承認,人腦是「已知宇宙中最複雜的物體」,每當科學家們知道得比以往多一點,就會發現已獲知的東西還是太少。
人類遠古時期,先人們一直認為,心臟是產生感覺與思想的器官,因此人難過的時候會「傷心」。直到公元162年左右,羅馬時期的醫生蓋倫通過在動物身上開展一系列實驗後,才大膽地提出了一個說法:大腦很有可能才是產生意識的地方。
蓋倫認為,大腦會產生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氣體,它在人體全身神經中流動,進而控制各種軀體運動。
公元2世紀時,羅馬醫生蓋倫用豬開展試驗。這幅圖片來自一部出版於16世紀的蓋倫著作集的扉頁。/ 圖片翻拍於《大腦傳》一書
時間過了1500多年,蓋倫提出的「精氣說」才終於在科學界找到相應答案:18世紀末隨著對自然界中電的研究的深入,義大利科學家伽伐尼、伏打等人在生物學領域揭示了生物體內電的力量,並利用電讓青蛙肢體收縮。蓋倫所提出流竄與人體各處的「氣體」,實際上就是生物電。
更深層次的問題隨之而來:生物電是如何在大腦神經元中產生並傳輸信號的?1952年英國科學家霍奇金和赫胥黎發表研究成果,他們利用槍烏賊作為實驗對象,發現了神經元放電原理——鈉、鉀離子的跨膜流動,兩人建造的模型解決了困擾生物學家們幾十年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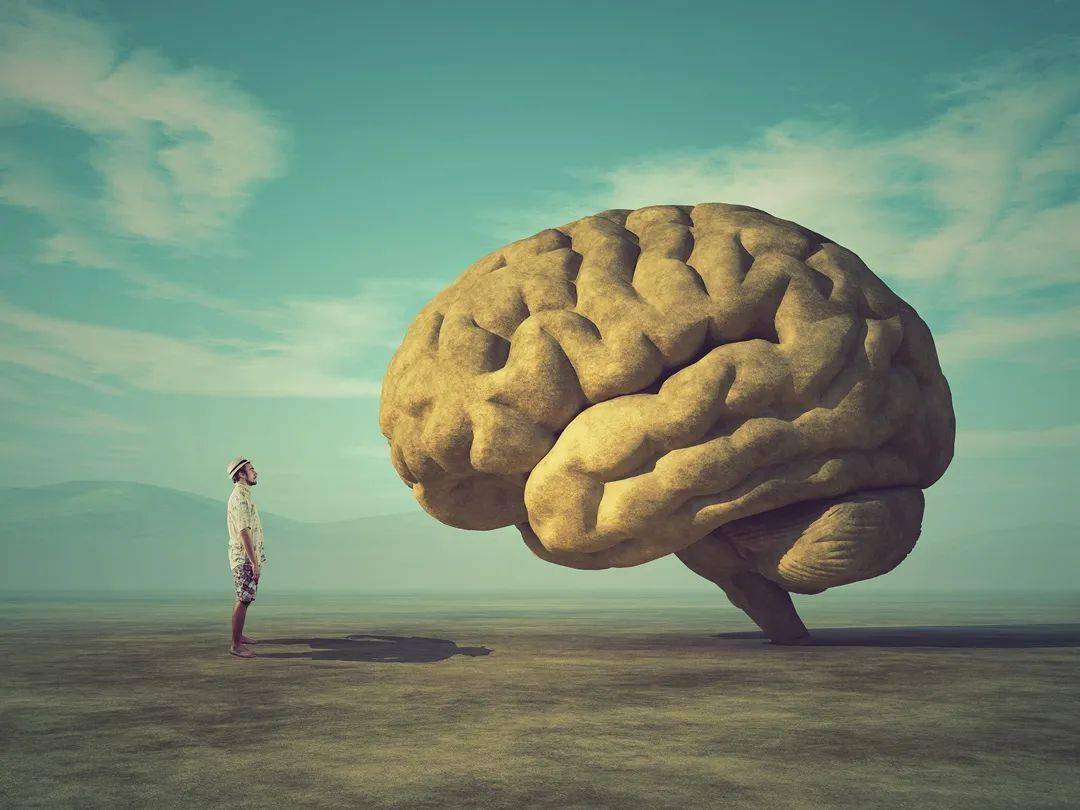
人腦非常奧秘,中國科學院腦科學中心高級研究員仇子龍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目前對大腦的探索,就相當於一群科學家去一個陌生的大城市探險,在經過數年努力後只搞明白了一兩幢建築物里的住戶情況。/ 站酷海洛PLUS
哺乳類動物的大腦被堅硬的頭骨包裹著,如果對神經元進行最準確的電記錄和接收大腦指令,必須先通過外科手術去除頭骨,讓微小的電極充分接觸絲毫般的神經纖維。現在馬斯克的公司所進行的腦機接口研發,就要將測試者的顱骨鑽開並切除一部分,這稱為侵入式腦機接口:
手術機器人 鑽開顱骨並切除。/ 視頻截圖
一個跟硬幣差不多大小、用於刺激及接收腦電波的傳感器N1植入體,通過極為精細的手術避開血管系統,置入運動中的大腦。這植入體在柔性薄膜上進行微加工而成,帶有電池可以進行無線充電。
置入傳感器。/ 視頻截圖
據馬斯克團隊成員介紹,Neuralink公司配置的是手術機器人,機器人在家中就可以安全、可靠地為有需要的人植入設備。機器人將植入體放入大腦後,再縫合切口。
科學家在人類大腦中植入傳感器的構想其實早已有之,20世紀60年代最原始的方案,是在人腦內植入傳感器,收集腦電波信號後傳送到計算機,再由計算機發出具體指令控制機械。這相當於通過大腦意念在指揮機械裝置。
實驗早已證明,植入大腦中的傳感器與大腦神經元相連得越多,計算機接收到的信息越精確,然而如何製造出適合植入人腦而又安全輕便的傳感器,一直考驗著科學家們。直到2004 年後,腦機接口才從科學論證進入應用實驗階段的關鍵期,美國神經科學教授尼科萊利斯帶領團隊研發出更適合於植入大腦的傳感器。2014年巴西世界盃開幕式上,尼科萊利斯的志願者、癱瘓患者平託身著一套「外骨骼機器衣」的裝置,用意念控制裝置為揭幕戰開球。
2014年巴西世界盃,身穿智能裝備的癱瘓患者平托為揭幕戰開球。/視頻截圖
將人體最奧妙的器官與當今最熱門的科技——AI結合起來,當腦機接口技術成為世界科研尖端潮流,像馬斯克這樣的追逐者當然不會甘於人後,2020年8月他的Neuralink公司展示了使用植入傳感器讀取豬的大腦活動;2021年4月Neuralink發布了一段視頻,一隻雄性獼猴使用「意念」在螢幕上用移動光標接住來回彈跳的球。也正是這兩則消息,讓腦機接口聲名大噪。
除卻這種侵入式操作,腦機接口還有其他兩種方式,本月初有國內媒體報道過「國產腦機接口讓猴子通過意念取食」的消息:雙手被綁住的猴子,想吃食物時產生伸手的衝動,於是通過腦電信號操縱機械臂運動將食物送到嘴裡。
這是南開大學段峰教授團隊進行的「介入式腦機接口試驗」,它需要在試驗者頸靜脈刺個小口,通過導管將裝有傳感器的支架送入位於大腦運動皮層腦區的血管。當導管被移除後,支架在血管壁內擴張,貼近血管內壁採集腦電信號。
此外還有非侵入式腦機接口——通過頭皮採集腦電信號。這種操作當然會比開顱植入傳奇器安全得多,但其缺點也一目了然:隔著頭皮採集到的腦電信號,難以保證質量。
腦機接口實際上是對不同部位的腦分區進行「腦密碼」解析的途徑,通過它我們可以更好地解析大腦的功能。 / 站酷海洛PLUS
02
眼睛看不到,大腦「看見」了
四年前有科學家團隊做了一組實驗,訓練小老鼠在看到一組線條後舔飲瓶子裡的水,並記錄下小鼠腦中視覺中樞的少量細胞對這些圖像的反應。隨後在小鼠相關的腦細胞中,研究者人為地重現了這種神經元活動的模式。這時儘管小鼠處於完全黑暗的環境中,它們卻表現得仿佛看到這些線條一樣。
有沒有可能即使人的眼睛看不見,大腦卻可以「看見」?馬斯克說,通過腦機接口技術,他們團隊最早想在人體實現的兩個功能,一是恢復視力,「即便一個人生來就是盲人,但我們相信,仍然可以恢復『視力』,因為大腦皮層的視覺部分還在那裡。我們通過向每個通道注入電流來刺激大腦中的神經活動,它可以讓我們繞過眼睛在大腦直接呈現畫面」。
二是解決脊柱損傷問題,「當你觸碰一個物體時,感覺沿著脊髓向上進入大腦。但受傷後這個聯繫被切斷了。如果我們能把電極植入脊髓,就可以刺激這些神經元,激活它們進行肌肉收縮和運動」。這相當於將在人體大腦與受損神經之間架起一座「數字化橋樑」。
人們對腦機接口的未來充滿憧憬,像馬斯克這樣充滿雄心壯志的富豪企業家,不在少數。但科學家持非常謹慎的態度:以侵入式腦機接口為例,其從首次應用到臨床至現在已經過去十幾年,但截至目前還沒有真正大規模地應用到臨床上。
即使馬斯克團隊的成員,在去年發布會上也承認,腦機接口的未來,還要面臨設備隱匿性、充電、升級如何保證等諸多挑戰。
國內就有專家在醫療健康產業峰會上表示,腦機接口從試驗到臨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目前腦機接口大概一百個通道左右,能夠轉換的信息相對有限;二是現在臨床上使用的剛性電極生物力學性能跟大腦組織有比較大的差異,不僅在植入過程中容易對大腦產生損傷,而且剛性材料植入以後會和大腦軟組織發生相對的運動,容易引起大腦組織免疫炎症反應,使得植入以後電極在幾個月甚至在幾周以後會失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目前腦機接口的應用。
而且腦機接口是一門綜合學科,當中既涉及醫學、材料學,也包含包括通信學、智能處理等技術,當發展到一定階段,心理學、行為學、倫理學也很重要。
據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公布的《腦機接口標準化白皮書2021》預測,腦機接口技術潛在市場將達數百億元。/ 站酷海洛PLUS
綜合諸多因素考慮,腦機接口技術離抵達臨床還有多遠的路要走?正在參與腦機接口研發、試驗的北京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馬永傑博士在接受北京日報記者採訪時作了一個判斷:
「完成首例動物試驗是突破性的進步,是從0到1的進步。但抵達臨床是一個從1到100的過程。」
「介入式腦機接口真正走到臨床,可能還要5年甚至更長時間。」
「完成首例動物試驗是突破性的進步,是從0到1的進步。但抵達臨床是一個從1到100的過程。」
「介入式腦機接口真正走到臨床,可能還要5年甚至更長時間。」
另一方面,馬永傑也認為,未來在一定程度上將人類的思考、意識、記憶存儲下來,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你甚至可以想像得更加科幻一點,比如意識的直接顯示、通過意識實現駕駛等,都不是沒有可能。只不過這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
這個周期要多長,現在沒有人能給出準確答案。 腦機接口的話題談到最後,都要回到最初的認知里:人腦,實在過於奧秘。
當然,人類對未來的暢想,人的大腦對一切未知事物的好奇、一次次追索探尋,正是社會不斷進步的重要推動力。樂觀一點也許也可以這樣說,終有一天,人類大腦會令人完全知曉大腦。
編輯|廖穎瑤
封面|站酷海洛PLUS
RECOMM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