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園與晴廬事件:末路還是曙光?
美麗園小區事件將帶給物業管理什麼?
《華夏時報》9月4日報道:鴻銘物業公司撤離海淀美麗園小區已經3天了,3日下午3點,小區200多名業主自發成立了業主臨時大會,欲罷免業委會,並簽名決定召回鴻銘物業還是選擇新物業。1378戶業主中,已經有近600人簽名。
9月3日下午6點,正在國賓酒店參加《物業管理條例》實施三周年,回顧業主團結互助及申請成立業委會協會座談會的律師秦兵,在得知美麗園業主和業委會發生衝突後,立即號召會場50餘人到美麗園小區聲援業委會。在當天舉行的座談會上,業委會負責人發表了致北京市物業行業的一封公開信,並宣布申請成立「北京市業主委員會協會」,200多名各小區業委會的負責人簽名響應。
點評:美麗園小區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用一位資深社區管理人士的話說:它讓我們見證了一次「業主拿自己財產進行的民主試驗」,它是發生在今天的北京版的法國大革命,昨天的激進派很快被更加激進的人物所取代,前者被批判為「保守者」,而被清洗出社區管理的舞台;直到人們渴望安寧的時候,革命者也將受到清算。
無論如何,這種「業主維權」已經表明出了和以前的物業管理糾紛種種不同的特徵,它所形成的決裂將是巨大的、完全的、決定性的,而這種徹底性包含有一切未來發展的萌芽。——中國物業管理的革命,不過是才剛剛開始。
作為當事人之一的物業管理企業,也應當警醒和感同身受:鴻銘物業與我們每一個同行同質同源,她的困惑與悲哀,這種對待業主「食之無肉,棄之有味」的雞肋情結,與我們絕大多數人同樣並無二致,假如我們沒有能力進行自我改革,即使業主處在分歧當中,原來的物業公司也不會得到寬恕。
——深圳《住宅與房地產》2006年10月「時事點評」梁曉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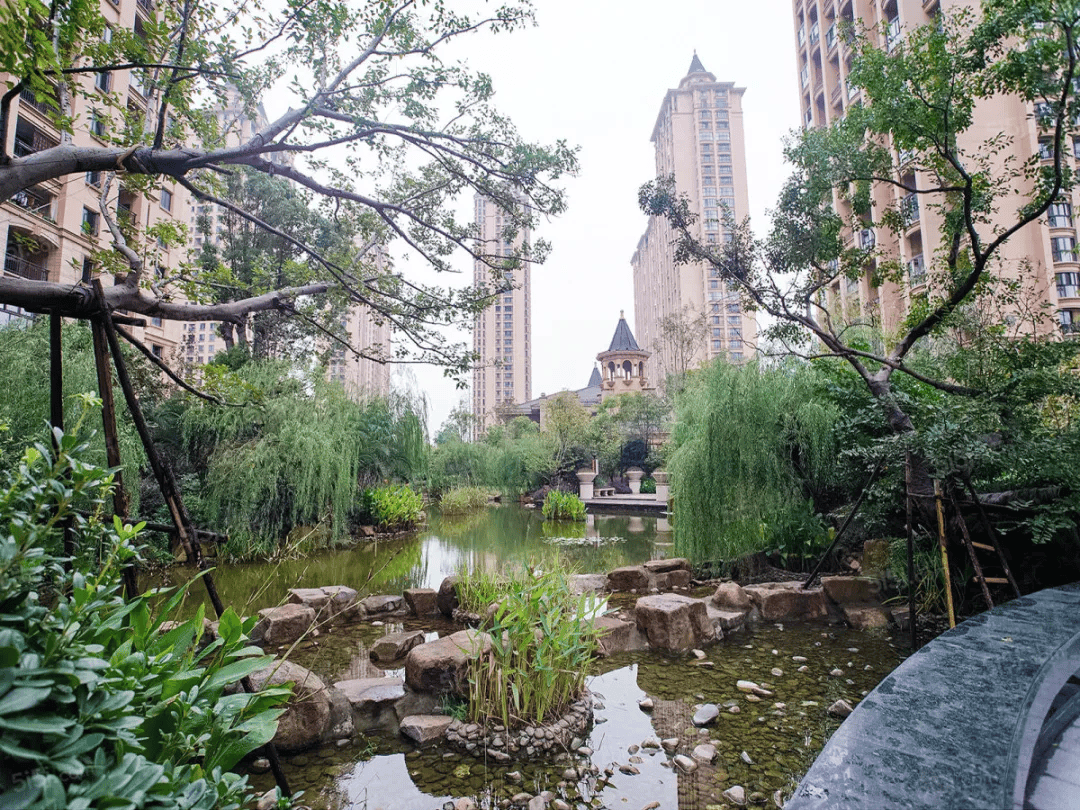
昨天聽過一段錄音,當業委會主任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表達出他自己個人面臨的危機時,在另一方表現出一陣鬨笑,這令我內心浮現出強烈的感受:儘管談不上光明一片,而我從不認為中國社區的民主探索漆黑一團,歷史經常重複兩次,第一次以悲劇呈現,第二次則會喜劇呈現,至少今天來看,曙光已經呈現,在這種時機我有一些獨特的思考,雖然不失片面,但我依然認為有其可操作性和值得嘗試之處。我們需要一點一點地去梳理問題,然後找到解決之道。
第一個問題:業委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為什麼他們更容易受到來自於業主內部的質疑?
答:業委會存在的制度背景是民主政權亦即「開放社會」,它的潛台詞是「每個人都並不知道什麼東西是最正確的」、「每一個人都能對政策發揮影響,即使不能改變政策,至少我們能夠評說政策」,然而與之相對應的「專制政權」或「封閉社會」首先的任務是消滅反對者。
容忍一個強大的在野黨存在,是民主社會的基本條件,而恰恰相反,任何一個家長式社會就必須首先取消掉一部分人的話語權,獨裁更是如此,中國古時的「言官」經常是制度開明的體現——魏徵這樣的人讓唐太宗都非常惱火,甚至經常想幹掉他,——而所有業主均有權質疑業委會和物業公司,是業委會制度體系的優越性所在,這是優點而不是缺陷,所以碰到的難題在於與這個民主制度相關的人,民主本身並不能提供製度理性。我們經常還去說「烏合之眾」,但我們幾乎從來沒有尊重過烏合之眾。
所以,因一個民主社會的政治缺陷就責備「制度失靈」是大錯特錯,我們更應把責任歸於自己,即這個社會的成員,特別是我們在某個階段上成為管理者時更應找到自己的問題。業主自身在智識上的成熟和道德上的完滿,也是一個過程,通過和諧社區發展中心早期舉辦的幾次研討會都可以看出,人與人的平等溝通極為困難,中國人的民主修養還需要從「開會」、「議事」做起,這是一個基礎建設。從事業委會工作的人,最初也許都抱有種種私慾和不同的目的,但是能夠堅持下來的人,應當說無論是智識還是道德層面,都不再會和那些「事不關己」、「胡攪蠻纏」的人同日而語。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最好的物業管理公司也能引起業主不滿,為什麼他們總是「管不好」?
AI的回答:物業管理公司引起業主不滿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
1. 溝通不暢:物業管理公司與業主之間的溝通不暢,導致信息傳遞不及時或者存在誤解,造成業主不滿。
2. 服務質量不佳:物業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務質量不符合業主的期望,可能存在態度惡劣、服務不及時、處理問題效率低等情況。
3. 缺乏透明度:物業管理公司的管理方式缺乏透明度,業主無法了解物業費用的使用情況,或者對管理決策不清楚,導致不滿情緒。
4. 管理混亂:物業管理公司管理不當,導致物業設施維護不及時、安全隱患未能及時處理等問題,引起業主的不滿。
5. 利益衝突:物業管理公司可能存在利益衝突問題,導致其在處理業主事務時存在偏向或不公正的情況,進而引起業主的不滿。
總的來說,物業管理公司引起業主不滿可能是由於管理不善、服務質量低下、溝通不暢、透明度不足等多個方面的原因所致。要解決這一問題,物業管理公司需要加強管理能力、提升服務質量、加強與業主的溝通等方面的努力。
我的回答:物業公司們為什麼管不好,除了缺乏工匠精神之外,我們不能將之簡單歸咎於乙方責任。現在可以提出一些對現實的描述性假設:物業管理費支出不透明,有被浪費和侵占的危機或傾向。公共區域產權歸屬的界定不明,其收益的去向受到業主質疑。(前兩項一般是業委會炒物業的理由)政府部門對社區內的糾紛處理進行推諉,不作為(這是北野先生經常強調的)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對社區的較多攤派,增加了物業管理成本。單個業主強大的談判能力提高了社區服務的交易成本,他們可以採取拒繳費用的方式實施單個業主的抵制,物業管理收費太難了。(這兩項是物業管理人士的苦衷)「業主滿意度」和「物業完好率」不能夠以相同房價檔次的深圳、上海來比較和參照。
朱憲辰教授的答案:1、多邊合約達成與實施的集體行動困境+雙邊交易信息不對稱的模糊合約糾紛。
2、共享事務治理——非市場、非政府的「共享事務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s)」的自主治理。奧斯特羅姆夫婦將此稱為CPRs。
3、行為理論啟發:大多數人大多數場景的簡單信息認知特徵,即他們只願意接受非常簡單的信息,並依此作出利弊的估計判斷;多邊、雙邊互動中投入精力者主要受情緒道德直覺支配。
第三個問題:原先開發商手中的香餑餑,為什麼傳到業主手裡就變成了臭狗屎或燙手山芋?
為什麼前期物業管理開發商還能管得好,到了業委會成立之後,物業怎麼都反而管理不好了?原因在於這個行業其生存背景就是一種制度環境高度衝突的產物,政府和開發商,業主和社會,其中的利益訴求錯綜複雜,對開發商或者說大物業而言,凡是能用錢解決的問題本質上壓根不是問題。但今天更大程度上是業主們和干預者的訴求衝突,業委會指望倚靠著鐵板一塊的業主陣營其實是天方夜譚,他的責任、權力和法律上的定位(業主大會召集人和決議實施執行人)其實完全不匹配,甚至存在角色對立。
這裡各相關主體忽視了一點:民主社會的特點在於,談判主體的資格是受到嚴格限制的。當年一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倡議創立國聯,但是國聯成立後美國自身卻沒有加入,因為被美國國會給否決了,美國國會同樣也否決了威爾遜主持下的《凡爾賽條約》,年輕的凱恩斯寫過《和約的經濟後果》。如果威爾遜是業委會主任,他就總是這樣被擱置在尷尬境地——業委會的所謂物業管理招標,對老物業而言,它除了「威脅」以外,並沒有提出任何「承諾」;對新物業而言,其實兜售的無非是一張空白支票,許諾的這個管理費標準業委會並不幫他收,但投入的錢卻真金白銀要打進「共管帳戶」,這個承上啟下的環節大可質疑。假若衝突是必須的,那麼問題就在於業委會成立之後,老物業公司馬上喪失了或被打亂了與業主之間的正常溝通渠道。一個敲詐者也許因為主人不在家,而失去敲詐的機會。綁架犯也是一樣。你可以把物業公司認為是一個敲詐者和綁架犯,但是他們的難題在於壓根找不到威脅的對象,或對應的業主或業委會成員向物業公司提出的每一個要求,物業公司如繼續在社區中生存的話似乎只能無條件滿足,否則就是業績越來越差,怨隙越來越深。所以業主們一邊聲稱「取消物業」、「賴著不走」,一邊還在援引《民法典》要求物業企業不能擅自撤出。這拉扯之中的痛苦自非常人所能承受和領會。
二零二四年六月六日
- END -
聲明:此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若有來源錯誤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權益,您可通過公眾號後台與我們取得聯繫,我們將及時進行處理。
本文不代表平台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