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
鳳凰網
(ID:ifeng-news)
作者:喬雨萌
「97年的萬辭王駕到。」這是徐暢在社交平台上的個人簡介。
對於「萬辭王」這個新生詞彙,有網友如此解讀:「干一行恨一行,行行都能幹破防,不上班心發慌,上了班又只想躺。」
不是隨便誰都有資格自稱萬辭王——4年前,徐暢從一所二本大學的中文系畢業。
本科同學中,有人現在還在讀博,而她已經換過15份工作,目前在找第16份。
她干過和專業沾點邊的文案策劃、活動策劃和新媒體運營,也曾「脫下長衫」,做前台、當書店店員。她待過網際網路大廠,也被招搖撞騙的老闆忽悠進過創業團隊。海量工作讓她見識了「物種多樣性」:畫餅的面試官,摸魚的店長,把開黃腔當有趣的男領導,以及她學不會的職場「宮斗」。
十一個月,是徐暢留在同一家公司的最長時間。風平浪靜的話,大部分工作可以持續兩到三個月。最短的一份,她只做了三天。
每次把辭職信甩給老闆,她都覺得「太爽了」,平時厭煩的同事和辦公室也變得「順眼很多」。終於能從這個糟糕的環境逃走了,她想。
不過,一旦幾個月沒工作,虛無的感覺又湧上來,銀行戶頭一點點變少的存款也催生著焦慮,於是她再度投簡歷,面試,帶著痛苦面具上班,幾個月後辭職。周而復始。
別人說她性格「沖」,這位萬辭王承認。但自我懷疑也常常縈繞她:「為什麼大家都可以忍,就我一個人忍不了?」

(圖/unsplash)
帶著困惑,她在社交平台上發帖講述自己的經歷,沒想到聚集了一大批萬辭王。這些年輕的「王者」起碼換過四五份工作,像她一樣做過十幾份的也不少。有人工作才三年,已經打過好幾起勞動仲裁。
鳳凰網和五位萬辭王聊了聊。他們都是95後,學歷和所學專業各不相同,但對於工作抱持著類似態度。和父母輩不同,他們不將工作視為人生意義的重要寄託,不信奉「勞動最光榮」的社會倫理,也沒有「融入集體」的焦慮。
對他們來說,自己的感受最大。身邊人常常評價他們「不穩定」「玻璃心」「缺乏忍耐力」,但在他們看來,是自己不願向「有毒」的當代職場文化低頭,儘管如是堅持需要付出代價。
於是他們以萬辭王自嘲,一面消解現實生活帶來的失落,一面昂起頭為自己打氣——如果一份工作里,要付出的勞動和情緒價值超過了能賺到的錢,「那就換一個」,徐暢說道。
職場小白的頓悟:
世界是個草台班子
2024年7月,徐暢正努力為簡歷填上新的一筆。兩周前,一個行政崗位的面試現場,面試官問她,你有哪些技能?
她自信滿滿:Word、Excel、PPT、PS,我都精通。
面試官也侃侃而談:我們為員工提供有競爭力的薪資,優厚的年終獎和各種福利。
他們相視一笑。面試官和她握手:期待你的加入。
徐暢心裡清楚,無論哪個辦公軟體,她都是「半吊子水平」。一定要說有什麼擅長的,那就是搜尋引擎用得不錯——有什麼不懂的,「萬能」的網友都能解答。
她同樣清楚,面試官在給她「畫大餅」,但出於現實的壓力,她只能接受,畢竟「活著更要緊」。
做過15份工作的她現在篤信,面試就是一場相互的「詐騙」。
她不擔心「騙局」暴露,「有什麼不會的,幹著幹著就會了」。

(圖/unsplash)
「從我換了N個工作的經驗看,對於市面上百分之八十的工作,一個人只要智商沒問題,幹個半個月到一個月都能勝任,」徐暢說,「只要我能把工作做好,領導也不會計較我面試時有沒有說真話。」
——畢竟,其他人的水平可能也差不多。剛工作時,她的學習勁頭很足,遇到不懂的喜歡問領導,問資歷深的同事。幾次之後,她發現,「他們肚子裡的東西也就那麼多,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跳槽14次的鄭雯對此也有著切身體會。她畢業於一所專科院校的動畫設計專業,因為厭倦了一直從事的銷售類崗位,決心轉行計算機,零基礎的她刷了兩個月面試題,順利入職一家網際網路「小廠」。
剛進公司時,她戰戰兢兢,擔心自己身為「小白」被嘲笑。不過她很快放下心來:公司里的其他同事,有的已經工作了十幾年,有的名字前掛著高級職稱,但技術水平還是「很水」——代碼全靠搜索,搜索不到的靠「甩鍋」。她恍然大悟,原來「大家都是混子」。
有人問她是怎麼找到這麼多工作的。她說,竅門就是自信,不要怕,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草台班子。
「世界是個巨大的草台班子」,在鳳凰網和幾位萬辭王的對話中高頻出現。根據新京報書評周刊的解讀,這句去年開始流行的網絡用語,意在描摹一種「表面上光鮮亮麗,實際上各種問題漏洞百出,到處都有混子、投機者,認真、踏實做事的人沒幾個」的狀態。

(圖/unsplash)
像是看透了世間真相一般,年輕的萬辭王們決定坦然做自己——和在職場中放低姿態的父母輩不同,職場氛圍的和諧、領導同事的認可,那算什麼?既然職場中的大多數人不過是「打腫臉充胖子」,為什麼還要假模假樣地委屈自己?
於是,權力地位那一套在萬辭王這兒不管用了——他們不願、也學不會違心地對領導畢恭畢敬,笑臉相迎。
徐暢幾次和上司正面「對線」。一次是在書店打工時,因為看不慣店長「什麼都不做,還有臉來要求別人」,她激情澎湃地列舉了對方的「十宗罪」並發到工作群,衝突以店長的主動辭職告終。不過這份工作也很快畫上句號,因為在父母眼裡,「終究不是正經班」。
還有一次是對著一個她認為「在外做舔狗,對內有點權力就上頭」的老闆。她帶著寫到凌晨三點的策劃案向他彙報,他一眼沒看,輕飄飄地來了一句,換個主題重寫。徐暢拒絕,逕自走出公司,結束了這份三天前剛入職的工作。
「社畜模式」:
奇葩公司全趕上了
萬辭王不是一天練就的。他們也曾像其他打工人一樣,渴望一份表面正常的工作。
二本畢業的陸帆自認對工作的要求不高,合法就行:朝九晚五,雙休,收入四五千。但打開招聘軟體,將地點定位到她的家鄉,一座北方二線城市,幾乎全是單休的工作,大小休的都很少。
更讓她感到「炸裂」的是,當地很多公司不給員工繳五險一金。在她現在任職的一家外教機構,百來號員工里,沒有一個上著社保,其中不乏乾了兩三年的人。
三年換過九份工作的陳晨有時覺得,怎麼奇葩公司都讓他趕上了。
他打過兩次勞動仲裁。一次是他作為全職員工被轉為外包,最後公司和他庭外和解。還有一次,他在無薪試崗一個月後被「惡意開除」,仲裁勝訴。
有一家公司在員工手冊里明晃晃寫著:上班期間聽歌罰100塊錢,閒聊罰300塊錢,遲到一分鐘扣50塊錢,可累加,無上限。陳晨瞠目結舌:我是不是要倒貼錢上班?入職三天,他果斷跑路。

(圖/unsplash)
梁菲也打過15份工,在一年半之內。
干過行政,當過前台和服務員,也賣過鴨脖、鮮花、珠寶黃金、健身卡、二手房甚至是陵園墓地後,她得出結論:資本家一律把打工人當牛馬使用。
在花店兼職時,她每天從早十點干到晚十點,這份工作突破了她對小時最低工資的預期,「你猜掙多少?6塊錢一小時」。做服務員更累,每天中午上班,半夜下班,日薪100塊。上崗不到一周,老闆以「衛生不過關」為由扣了她三百塊錢,她沖老闆比了個中指,「直接走人了」。現在,她只想找一份工資和工作量匹配的工作。
「三千的工資讓人干出三萬的成績,換誰都會跑路,」梁菲撇撇嘴,「每天當牛做馬又挨叼,工資五位數還能咬咬牙勸自己忍忍,月薪三千忍不了一點。」
當「牛馬」也就罷了,但今年23歲、做過12份工作(包括全職和兼職)的陸帆,不理解為什麼同為牛馬,還要爭著「無底線內卷」。
那份工作是石膏頭像手繪師。陸帆很喜歡這個職業,因為夠「純粹」——不用賣東西,不用跟人聊天,只要專心畫像就夠了。
入職第一天的中午,她放下筆,邀請同事一起去吃飯。同事擺擺手拒絕,從包里掏出一個麵包,說要抓緊時間工作。她後來得知,這裡大部分員工中午都不休息,吃個十分鐘的便餐就接著畫。而這般工作強度,獲得的回報相當微薄:畫一件石膏像,2元。如果客戶退貨,員工按照產品售價被扣工資,一次至少30元。
「我的天老爺,我覺得他們都是奇葩。」陸帆感慨。於是每天中午,她一個人到外面覓食,再散個步,晃蕩夠午休的一個半小時,再不緊不慢地回去。
同事私下和她說,自己也不想中午加班,但「大家都這樣」,「不好意思不加」。
「可那是屬於我的休息時間,」陸帆聳聳肩,「我就是覺得我不能被壓榨。」
陳晨的「覺醒」一刻發生在無盡的加班之後。
那是一家規章制度寫著每晚六點下班的公司,但陳晨離開辦公室的時間從沒有早於晚上十點,凌晨也是常事。
每次深夜走出公司,他「還沒有從社畜模式轉換過來」,只覺得精神恍惚。直到下了地鐵,走到小區門口,整個人像「泄了氣的氣球一樣萎下來」,他幾乎是飄著回到家,簡單洗漱一下,一頭栽到床上。

(圖/unsplash)
他試過和領導溝通。上司語重心長,「男孩子吃點苦怎麼了,剛從學校出來就是要吃苦」。他懶得再爭辯。
情緒在陳晨入職滿月後的一個周末爆發。周六一整天,加班,周日白天,繼續加班。到了周日傍晚,他把手頭的工作收了個尾,去看早就買好票的演出。在劇院裡,他的手機不停振動,是同事催他幹活的電話和微信。他關了機。第二天,同事向老闆告狀,陳晨就坡下驢,遞交了辭呈。
「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享受一頓晚飯,和朋友聊聊天,看一場演出,不被打擾,」陳晨說,「我不想變成一個打工的機器。」
升級打怪,
還是慢慢「學乖」
剛畢業時,徐暢也曾迫切地想在工作中學到點東西,想要大展一番宏圖,幻想像《穿普拉達的女王》里的安妮海瑟薇一樣在職場裡升級打怪。但她很快發現,理想和現實之間隔著一道「馬里亞納海溝」。
徐暢曾在一家網際網路大廠實習。四年多過去,當時的場景仍歷歷在目——
八點半,胸前掛著工牌的員工魚貫進入公司。泡好咖啡,戴上護頸椎的套子,往工位上一坐,直到下班。喝水的頻率不會太高,因為廁所的坑位有限。
在那裡,同事間要以「XX同學」稱呼,程式化的笑容是每個人的面具。足夠客氣,但沒有「人氣」。
在那裡,她學會了一套全新的語言體系:賦能,對齊,顆粒度,感知度,心智,賽道……如何區分痛點、癢點和爽點?中文系畢業的她對著字典研究了許久。
在那裡,溝通要「留痕」,因此交流大多發生在線上。辦公室里,人聲不常有——相鄰工位的同事可能一整天說不上一句話。更多是密集的「噠噠噠」打字聲,以及頻繁響起的「叮」,那是辦公軟體的提示音。

(圖/unsplash)
在那裡,時間精確到分鐘,萬事都要預約,即使是和相隔十米的同事溝通一個簡單的問題,也要在辦公軟體上問,五分鐘後我們去會議室聊?
最恐怖的事無外乎績效被打低分,她聽說不少同事在績效考核前會徹夜失眠。
「每個人都像是被一個職場的殼子套住了。」徐暢覺得壓抑。三個月的實習期結束後,她再沒考慮過進入大廠。
從學校步入社會,徐暢逐漸發現,許多過去的行事法則不再適用。
比如對於高效率的追求。第一份工作時,老闆叫她寫一份項目書,她幹勁滿滿,「肝」了個通宵,第二天早上就把列印好的文稿放到了老闆辦公桌上,心裡還頗有些自得——在學校時,「快手」的她總是老師表揚、同學羨慕的對象。
期待的稱讚沒有出現。老闆拿著項目書端詳了一會兒,語氣微妙,「寫得真快啊......你今天也別閒著,把XX項目的策劃做了」。她分明記得那是一個已經「流產」的項目。
走出老闆辦公室,她滿腹疑惑,問同事什麼情況,對方語氣冷淡,「我在忙」。直到聽到同事跟別人抱怨,「小徐怎麼這麼卷」,她才意識到自己「犯了傻」。
從那之後,她「學乖」了。DDL(截止日期)是哪天,她就哪天交。老闆和同事對她重新展露笑顏。

(圖/unsplash)
但還有一些做法和規則,是徐暢至今無法理解和適應的——
比如,一整天都沒有工作,臨到下班點又被安排開會。比如,領導一句不滿意,整個項目組就要通宵改方案。比如,員工下了班不能走,不是因為還有工作要做,只是因為領導還沒走。還有那些「屎上雕花」的工作,「沒實質意義,純粹為了好看,為了做面子」。
有一次,她負責策劃一份文案,老闆反覆叫她修改。這次說這句話應該放在前面,那句後面不能用逗號,下一次又說,還是應該把這句放後面,標點換回逗號比較好。
這樣來回改了十幾遍之後,她「火」了,直接沖老闆說,我真不理解你為什麼要在這些細小的地方一直糾結,這句話放在前面和放在後面,意思有什麼區別嗎?她追問,既然你要改,你告訴我,到底怎麼改?這樣改的意義是什麼?你真的覺得這樣改會更好嗎?
老闆啞口無言。後來,她逐漸被邊緣化,工作清閒,但沒意思。很快她主動請辭,一如既往,「何必等到最後你把我開了,我自己先走算了」。
除了職場對打工者無差別的虐,身為女性,徐暢還在公司遭遇了性別不平等,甚至是言語暴力。
她曾在一家個護品牌工作。一次腦暴會上,徐暢和同事討論公司產品在公共廁所的廣告投放策略。隔壁部門一個男性小領導突然插話,不如在男廁所貼上AV的視頻連結?在坐著二十多人的會議室里,他甚至學起了AV里的聲音。在場的男性鬨笑。
徐暢渾身狠狠一抖,轉過身怒視擬音者:你有毛病吧,低不低俗?
對方全然不在乎,繼續嘻嘻哈哈:對啊,我就是這樣一個低俗的人。
被徐暢罵過幾次後,那個男領導不敢再在她面前開黃腔,但繼續騷擾其他女同事。
她們不敢聲張,只能一臉苦惱地找到徐暢,請她幫忙,「去說說他,這個人真的是腦子有問題」。
同為打工人,徐暢和身邊人的感觸常常是相通的。領導是傻X,同事是傻X,公司在做不知道有什麼意義的項目,業務領導明明什麼都不懂,還要求我們做這做那……她經常在他們口中聽到類似吐槽。
但萬辭王和普通人的最大區別是——「我為什麼要忍?」
「死刑犯」,
在忍與不忍之間
離職一時暢快,作為萬辭王,卻不得不承受長久的代價。
最直接的是下一次求職時面試官的「拷問」。每次因為「不穩定」被judge,陳晨都在心裡大喊,「你以為我不想穩定嗎,我比你更想我穩定」。
無奈之下,萬辭王們被逼成了一個個「簡歷裁縫」,在每次面試前努力「縫縫補補」:只留下那些在職時間長、和崗位相關度高的工作經歷,「反正短的不交社保,即使做背調也查不出什麼」。
但大段的職業空白期同樣會引起面試官的質疑。對此,他們也逐漸掌握了應對的話術:「沒工作的時候,我在嘗試做自媒體,也會接一些散活兒」——要訣是,別閒著。

(圖/unsplash)
「在中國的職場,跳槽過和gap過的人等於『死刑犯』。」梁菲總結。
4年15份工作的經歷,也讓徐暢成了朋友圈的異類。很多人說,好羨慕你,你的心態真好。也有人問,你家是不是特別有錢?
之前,她會一板一眼地糾正:我家只是普通的工薪家庭,我畢業之後沒再管家裡要過錢。其實我也想過穩定的生活。一直跳槽,我也很焦慮。
但現在,徐暢已經「不會再爭了」。她認為這只是個人選擇,多說無用。
畢竟就算親如父母,也總是因此質疑和否定她。如今,她和父母的溝通僅停留在最基本的生活方面,比如今晚回不回家吃飯,吃什麼。他們默契地不提起和工作相關的任何話題,「一說就爆發」。有時在家休息了兩三個月,徐暢在自己房間裡躺著,父母走進來,欲言又止。壓力瞬間衝到她的頭頂。
「雖然我對外總是表現得很強勢,但我也很敏感,一直很想得到我爸媽的支持,不想成為他們的負擔。」她說道,語氣里透著落寞。
面對職場冷眼和親友的不理解,在和鳳凰網的對話中,幾乎每個年輕人都談到了纏繞在他們內心的自我懷疑:「為什麼大家都可以忍,就我一個人忍不了?」
徐暢試過走上常規的生活軌道,做一個穩定的工作,領一份穩定的收入。在前幾個月,她幾乎成功了,她以為自己終於蛻變成為一個「情緒穩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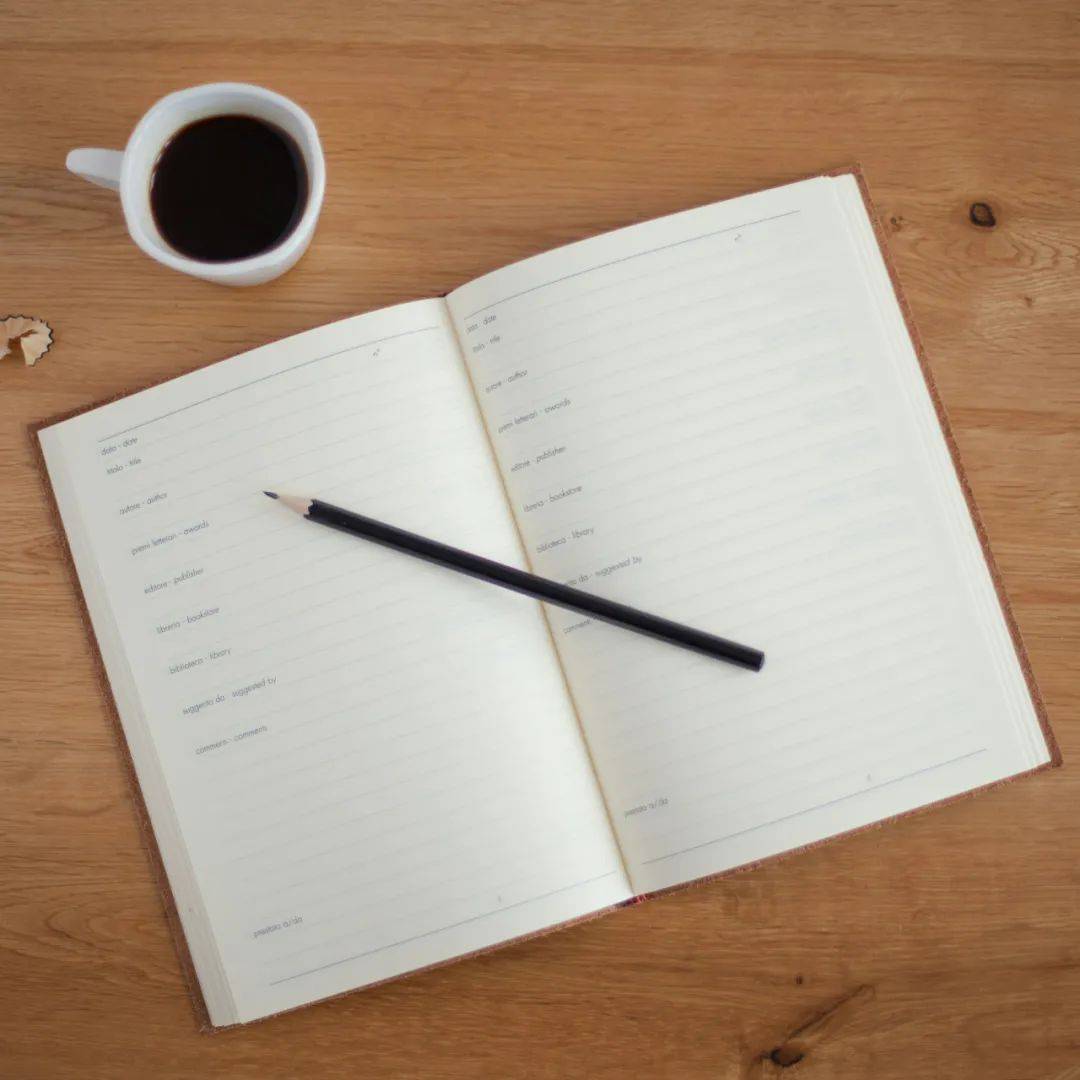
(圖/unsplash)
在那份工作還差一個月就做滿一年的時候,她經常覺得手腳發麻,心跳飛快,上醫院一查,才知道自己患上嚴重的焦慮症和抑鬱症。醫生面容嚴肅:你太壓抑自己的情緒了,必須要改變。她點點頭,一出醫院就提了辭職。保工作還是保命,她當然選後者。
於是她又回到就業兩三個月、休息兩三個月的循環里,同時回到生活中的還有父母的不滿和諷刺。「就像往我身上扎刀子,」她說,「他們最了解我,所以也最知道怎麼讓我痛苦。」比如那句她父親常說的:你住家裡都不用交房租,占了大便宜。
對於父母的冷言冷語,徐暢只能忍耐。她考慮過搬出去自己住,但被杭州的經濟發展速度打消了念頭。她算過一筆帳:外面隨便租個房就得三千起步,日常開銷也要三四千——她平時喜歡逛個酒吧,健個身,現在還在學陶藝。之前她最高拿過月薪一萬,「但現在行情不好,多半達不到」。
「我不想放棄現在這樣輕鬆的生活,」她自嘲這是自己的「劣根性」,「如果出去住,我在工作上要吃的苦會多得多,我必須忍到死。」
如今,徐暢只把工作當成一種「賺錢的東西」:「對我來說,可能現在的狀態就是最優解。」

(圖/unsplash)
其餘幾位萬辭王也是一樣,在忍和不忍之間反覆橫跳。他們都勸過自己「再忍一忍,再多待一段時間」。不過「忍」的意識一旦產生,長則三個月,短則半個月,他們就會發現自己「忍無可忍」。
每到最糾結的時刻,梁菲就會盤算自己的現狀:沒結婚,沒孩子,無房貸,無車貸,父母和自己都身體健康。她想,我有什麼必要忍,有什麼必要吃這個苦?於是辭職的最後一絲心理壓力被卸掉,畢竟,「好工作難找,但月薪三千的遍地都是」。
在一份份工作間輾轉騰挪的四年來,徐暢能感覺到自己的變化。
比如她學會了委婉「甩鍋」。之前被安排不屬於她的工作,她會生硬地直說,這不是我的事情,我不做。現在,她會繞好幾個彎,拋出託辭——
這項工作之前一直是其他同事負責,我對這方面不太了解,交給我做的話,我需要從頭學習,對團隊而言會浪費比較多的時間,拉低整體的效率。
這在大多數人眼中是日漸「高情商」的表現,但每次在聊天框打出這些話時,徐暢還是會「渾身難受」。
小時候看童話,她常常做「公主夢」;如今再看,她的目光開始為童話裡邊緣的「小角色」停留:收留白雪公主的七個小矮人是辛勤的礦工,《綠野仙蹤》里的鐵皮伐木人在勞作時被斧頭砍斷了四肢、劈開了身體,數不清的侍從和僕人環繞在公主王子身側。
她不由感慨,同是天涯「打工人」。
從小看的各種文藝作品也教會她,人要善良,要誠實,要追求公平和正義,但進入社會,她在一次又一次的「犯傻」中意識到,這些「美好的品質」,也許反而是一個人成功最大的絆腳石。
夜深人靜時,她感到幻滅。但她還不想妥協:
「反正,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