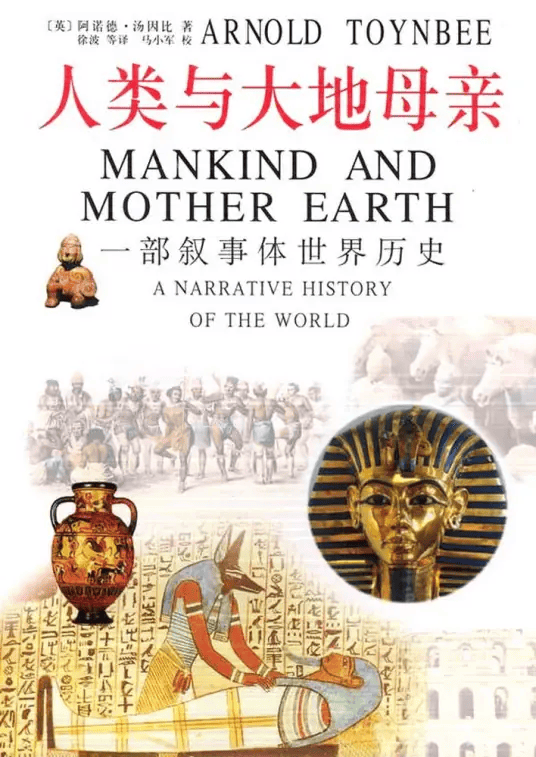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1889-1975),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在其撰寫的世界通史《人類與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中,對於中國文明的起源、特徵和前景有著獨到的論述,對於中國文明的未來做出了積極而樂觀的展望;對於中國馬拉戰車、文字和青銅器的起源做了非實證性的假設。本書完成於1974年,英文版出版於1976年。徐波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中國文明的起源
自從公元前第四千紀末期最早的地域性文明——蘇美爾文明的早期以來,與之類型相似的文明社會來去匆匆。諸區域文明中最早的樣本——蘇美爾文明並沒有長久、穩定地保持其獨有地位。大約公元前三四千紀之交,法老文明誕生於埃及;公元前三千紀的下半葉,小亞細亞、克里特和印度河流域也出現了一系列區域文明。其中,也有一些倖存至今,但即使它們中間最古老的倖存者——中國文明,也比它的蘇美爾、法老埃及的文明先驅至少晚了近1500年。
中國的區域文明(被稱為商朝,別名殷)誕生於大約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徵源於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晚期(即龍山黑陶階段)。與西南亞的肥沃新月地帶和埃及不同,中國文明的興起沒有伴隨著定居地的變動。如同地中海東部一樣,中國的新石器文化依賴於降雨對農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勢相對較高的風化黃土地帶,包括甘肅、黃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東部的黃河與漢水、淮河間的廣大地區,這也正是龍山新石器文化後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國文明的開拓者們並沒有開發河谷底部的沖積層土壤以供耕種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國的古老文明升起於地平線1000年左右,蘇美爾和埃及類型的治水方式才成為中國經濟的顯著特徵。
東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並不像蘇美爾文明及其前身美索不達米亞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那樣有過明顯的斷層。不過,兩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類似的新趨勢。與蘇美爾一樣,中國由新石器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的歷程,伴隨著統治集團與臣民階層財富和權利的嚴重分化。安陽(商朝的最後一個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與烏爾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處,儘管後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構宏大,並擁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在蘇美爾,沖積地被開發成耕地推動了社會財富的不斷集聚,也使得極少數統治者能夠獲得窮奢極欲的享受和陪葬。在中國,也出現了同樣邪惡的趨勢,而整個社會經濟資源卻沒有任何同步的增長。
中國文明破曉之際,也曾出現過一系列創新,這使我們回憶起伴隨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突然誕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國也不例外,這些創新萌芽的突發性,似乎預示著那裡的文明同樣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產生的,從而與蘇美爾文明顯著的自發進化形成鮮明的對比。
一項突發性的創新就是馬拉戰車的使用。毋庸置疑,這是在公元前18世紀或稍後一些時候由歐亞大草原傳入中國商朝的。第二項創新是一種文字符號的應用,即中國商代文字的發明。它是中國古典文字的先驅。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樣,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蘇美爾文字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很可能既細微難辨又比較間接。中國文字還有一個特點與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獨特風格,但文字的結構來自蘇美爾語,這種結構(對表意符號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邏輯又顯得笨拙)過於罕見以至於可以肯定,它是在三個不同的場合獨立發展成形的。中國古代文明初創時期的第三項突發性創新是青銅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擲器、武器和祭器等。製造青銅器的技藝也無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銅器就像其文字一樣,帶有典型的中國特色;青銅器皿設計精巧,顯示了高超的工藝。當然,我們可以想像,中國青銅器或許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有木製原型,只不過這種原型在今天已無跡可尋。但是,這一假設僅能解釋手工製作風格的源頭,而冶金技術的突然獲得則仍然是一個謎。
商代青銅器的構成元素中,錫的含量較高(17%)。距離黃河流域最近的錫、銅產地是馬來亞和雲南;但熔合錫銅和鑄造合金製品的技術不可能由南方傳入黃河流域。東南亞最早的青銅器文化(稱之為「東山文化」,位於越南北方)也不會早於公元前最後一千紀的後半期。暫且不論銅錫合鑄技術來自何方,而此時的銅、錫卻早已輸入黃河流域為中國所用了。亞洲的熱帶地區很可能是中國商代的金屬來源地。因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成分,具有經由歐亞草原傳入中國北部的西方文化成分之外,還含有一定的熱帶文化源頭。中國的商代主要種植小麥、穀子和水稻;飼養的畜類除了普通的家畜外,還有水牛;他們馴養的兩種豬,其中的一種起源於南方。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植物最早是在一些熱帶沼澤地區馴化出來的;這一地區的文化與中國北部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類似。但似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從亞洲的熱帶地區到黃河流域的南部存在著一種與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相類似的文化。從地理位置上看,距黃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不僅相距遙遠,而且為崇山峻岭所隔絕。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東部和南部擴展到了印度那些現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麥)為主要農作物的地區,此點至今無據可考。
因此,商文明進程中的熱帶淵源仍屬不解之謎。根據中國的傳說,如今地處中國境內的黃河流域以南的地區,更不必說越南境內,都僅僅是通過被漢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國北方移民的滲透。不可否認,這一傳說並非只是中國文化偏見的反映。公元19世紀,長江流域南部人跡罕至的高原地區發現了一些倖存下來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從而證實了這個傳說。此外,當代中國南疆與東南亞鄰國的交界地區還發現了其他倖存下來的原始民族。不過,最早培育出水稻、馴化了水牛的地區依然無法確定。
中國文明的統一性和未來
在公元前221年,從印度次大陸到直布羅陀海峽,在中國以西的舊大陸文明中心的廣大地區,沒有發生任何決定性的事件。與此相反,這一年對於中國來說卻是劃時代的一年。就在這一年,中國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統一的完成標誌著中國歷史的分界線。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國只是一個文化上的統一體,卻從來不是一個政治上的統一體。那時,中國不時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但到公元前221年,在或短或長的分裂和混亂的插曲之後,它再次達到政治上的統一。
在中華帝國,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視為對整個人類世界的統治;其臣民總是把自己看作一個世界國家的公民,而不是外來征服者的犧牲品。傳教士們打算把福音傳遍整個人類,中
國哲學家墨子則宣揚,人類應該相愛,並以無私的忠誠來為一切同類謀幸福。孔子思想最權威的解釋者孟子曾反駁道,墨子的教條是無法實現的。孟子擁護孔子維護等級禮制的理想。但是,經驗說明,由個人相識而激發的愛和僅僅根據一般的人性需要而產生的對所有同類之愛,並非必然互相排斥的社交表達方式。
中國人曾經把中華帝國視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國,他們今天正在思考著自己的國家作為全球競技場上彼此爭戰的國家中的一員所發揮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正在忘掉自己歷史上那殘酷的一頁;那時,中國自身成了地方諸侯國家的戰爭競技場。另一方面,中國人似乎對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統一以來的歷史十分敏感,因為他們正盡力避免國家機器同農民的疏遠。而農民,自漢武帝即位以來,便成為「中國的悲哀」。
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在中國首倡以政績徵募文職官吏的制度,並通過考試對候選人員的能力進行評判。中國皇帝的文職官吏是人類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們長期平安有序地管理著這麼龐大的人口,這是其他國家的文職人員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們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們為了自己個人的特權而濫用權力,從而一次次地把中國帶入災難。中國領袖們正在採取措施防止悲劇的重演。與中國過去的改革家們相比,中國領導人是否能獲得更大成功,人們將拭目以待,但至少他們目前行動的魄力便是一個良好的徵兆。
如果中國人真正從中國的歷史錯誤中吸取教訓,如果他們成功地從這種錯誤的循環中解脫出來,那他們就完成了一項偉業,這不僅對於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且對處於深淺莫測的人類歷史長河關鍵階段的全人類來說,都是一項偉業。
(節選自[英]湯因比(A.Toynbee):《人類與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徐波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