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經,周雨彤是一個缺少安全感的人,角色似乎成了她的安全港——在戲裡,她可以哭可以笑,可以肆意發泄自己的情緒。但當她回歸到自己,她忽然覺得空蕩蕩的。她忽然意識到,「當你把對外索取換成對內,你會覺得享受就好了——享受這個職業是瞬息萬變的,享受今天在高處、明天占低位,享受有人愛你、有人離開」。
作者 | 高勝寒
題圖| 由受訪者提供
在《春色寄情人》的殺青宴上,周雨彤大哭了一場。
殺青宴在上海的一艘船上舉辦,對周雨彤而言,這是「吃的體驗感很差」的一頓飯。登上船的那一刻她就開始慌張,因為她知道船在江中行駛一圈後就會靠岸,大家就要散場了。進行到尾聲時,製片人提議大家都講兩句,和這部劇做最後的告別。周雨彤剛要開口,就聽到船發出了即將靠岸的汽笛聲,沒忍住一張嘴就哭了出來,一邊哭一邊說:「一開始我以為自己捨不得的是泉州,後來我以為我捨不得的是南枰,今天我才知道,我最捨不得的是你們。」
她這一哭,殺青宴變得傷感起來,劇中飾演莊潔(周雨彤飾)母親的劉琳開始安慰她,「女兒你別哭,我和你說演員的情緒很珍貴,你要用到你以後的戲裡再哭。」飾演陳奶奶的方芳聽到這話開始反駁,「孩子想哭就讓她哭,為什麼不能哭?」大家都沒走出戲裡的身份。那些時刻,周雨彤「真的相信這是我的奶奶,這是我媽,這是弟弟妹妹」。

(圖/《春色寄情人》)
剛出道那幾年,周雨彤每逢殺青必哭,「那時候還小,會有一場夢做完了的感覺。」後面拍的戲多了,她可以慢慢將自己與角色分割,有很多笑著殺青的經歷。但這一次,《春色寄情人》帶給她的感受卻不太一樣——成為有著身體缺陷,但陽光開朗和敏感自卑並存的莊潔後,周雨彤似乎也在南枰這座溫暖的小城,找到了最初的自己。
這些年來,周雨彤被貼上過很多標籤。早些年她因為穿搭出圈,很多人不解地問:「周雨彤是演員嗎?演過什麼?我以為是網紅博主呢。」後來她拍出了一部部代表作,又成為了大家口中的「古希臘掌管打工的神」「內娛鬆弛感代言人」。
對於這一切,周雨彤照單全收,「我不排斥大家對我的任何說法。像之前大家覺得我是穿搭博主,問我排不排斥,我的回答也是不排斥,因為我在那個階段就是因為這件事情被大家看到了。人怎麼能否定曾經給你帶來讚譽的東西呢?如果否定這個,就等於我在否定自己的過去。」
周雨彤不抗拒標籤,但也從來沒給自己設限。在和她的交流中,我隱約看到了她在標籤之下閃爍的光芒,那是一個更有生命力、更細膩、有著溫暖理想的演員。
她還有更遠的路要走。

莊潔「活」了
莊潔是周雨彤飾演的第一個有身體缺陷的角色,周雨彤總是親切地稱呼她為小莊。最初看到劇本時,周雨彤就被小莊打動了,那是一種演員被角色滋養的感覺。
「她做了截肢手術,但是非常樂觀開朗,也不賣慘,每天就是嘻嘻哈哈的狀態,給我注入了很多能量。還有南枰這個地方,不管是陳麥冬、奶奶,還是廖濤這一家子,都讓我覺得特別有人情味,有煙火氣。我看到它的時候就覺得這是一個特別能治癒我的故事。」周雨彤說。所以最初因為檔期問題可能沒有辦法參與這部劇時,她產生了很強烈的遺憾感,「但還好緣分就像是一個圓圈,兜兜轉轉又回來了。」
確定出演後,周雨彤一直琢磨如何才能成為莊潔,她開始改變自己的肢體動作。當時劇組為她安排了兩個和莊潔有著類似經歷,也需要戴假肢的姑娘,分別和她在一起生活了三四天。她們朝夕相處,一起吃飯、聊天,周雨彤拍戲時她們就在監視器後邊,及時給出建議,這給周雨彤帶來了很大的安全感。

(圖/《春色寄情人》)
「她們平時怎麼坐、怎麼站、怎麼跑、走上坡路時要怎麼使勁、下坡路要怎麼走,其實都不太一樣。有個姑娘和我說,她們戴著假肢的腳不太喜歡平放在地上,要翹起來一點才會舒服。我剛開始嘗試的時候腿一直在抖,控制不了這塊肌肉,但後來我就形成了肌肉記憶,不會再發抖了。我挺開心的,我覺得我克服了自己本身的一些習慣。我還特別興奮地和那兩個姑娘說,我可以控制住了。殺青後有一段時間去演別的戲,我也會不自覺地把腳翹起來。」周雨彤回憶道。
那段時間,她每天都在網絡上瀏覽大量相關信息——哪個女孩的假肢會發光很炫酷、不同的截肢長度對下蹲這個動作會產生什麼影響,她都記得很清楚。那些時候周雨彤心裡想的是,「我想把小莊儘可能真實地呈現出來,不能過分誇張,要找好中間的尺度。」劇集播出後,許多觀眾感慨,「在知道莊潔截肢後,再去看她細微的動作,才明白周雨彤真是做足了功課。」這些聲音,與當初那個在片場內外一直揣摩自己如何能走得更逼真些的背影,形成了一個不算遙遠的呼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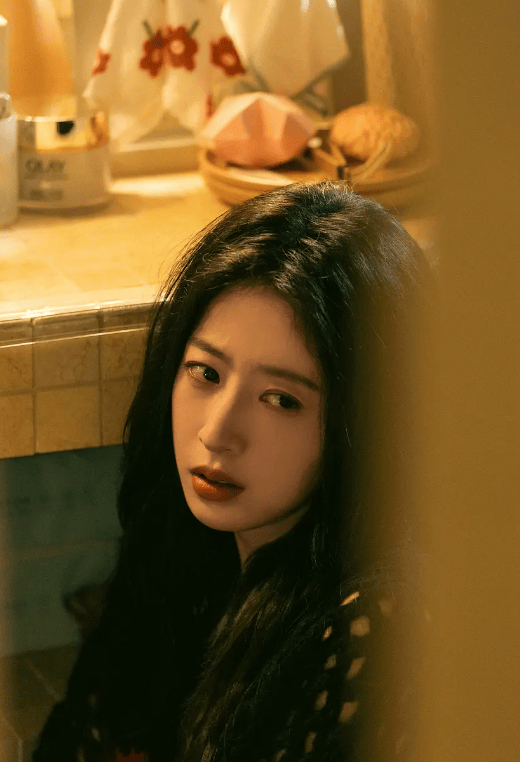
(圖/《春色寄情人》)
肢體這關過了,周雨彤開始把更多精力放在消化人物內心上。剛開始和戴著假肢的姑娘們聊天時,周雨彤有很多話都不敢提,害怕自己冒犯到她們。但接觸下來後,周雨彤發現:「是我把她們看弱了。你想一想,她們經歷了這麼大的人生變故,跨越了生死這條線,她們的勇敢和豁達我們是不能輕視的。我覺得我們要做的不是同情,過度的同情也是一種冒犯,而是應該為她們帶來更便利的生活。」她也會在網上看女孩們分享自己的愛情故事,感受她們在愛情中是否會有不同之處。在她看來,陳麥冬和莊潔,就像是兩個有些受傷的小動物走到了一起,他們內心都有安全感的缺失,不太會表達愛。但當站在分岔路口時,他們還是很堅定地選擇了彼此。
就這樣,莊潔在周雨彤心中慢慢變得鮮活起來,「我把她分成熱和冷兩個階段來看。她的熱是對外的,無論是從事銷售這個職業也好,還是在家中的長姐身份也好,她一直都像一個小太陽,是一個很溫暖的存在。但是她也有自己冷的一面,這主要體現在她的個人空間裡,比如當她在親密關係中遇到一些問題時,我會把冷的這一面單獨摘出來,轉化為她處理事情的方式。」

(圖/《春色寄情人》)
周雨彤真的相信,在平行世界裡,南枰這座被煙火氣圍繞的小城,莊潔正好好地生活在其中。

我要挖掘我身上的另外一種可能
周雨彤沒有一套固定的表演模式,有時在片場她劇本不離手,基本能做到一字不落;有時她又能根據現場情況或導演要求隨時現掛,根據情景進行大段的即興表演。她喜歡這種有變化的工作方式,「我覺得這可以挖掘我身上另外一種可能性。」
拍攝《春色寄情人》時,劇組的人達成了一個共識——不要把演員自身的習慣和狀態放置在角色前,不要過多地自由發揮或者改詞,大家想一起呵護好這個故事文藝浪漫的氣息。所以在劇組時,周雨彤一直認真研讀劇本。她開玩笑說:「我要確保我的台詞每個標點符號都是對的。」有90%的戲,他們都是完全遵循劇本去完成的,幾乎達到了一字不差的程度。

(圖/《春色寄情人》)
不過也有一些橋段是演員臨場發揮的,比如陳麥冬和莊潔在電影院吃爆米花那場戲,導演遲遲沒喊卡,他們就一直演了下去。還有讓觀眾直呼甜分超標的「你報警吧」「報警還是抱緊」的對話,也是在那一刻自然流露出的情感。
對於即興表演這件事,周雨彤一點也不發怵,在拍攝《我在他鄉挺好的》(簡稱《他鄉》)時,她已經經歷過太多次了。「我在拍《他鄉》的時候,有一種拍紀錄片的感覺。這部劇很特殊,更像是一部共創的劇。我們不是全本開的,很多場戲是告訴你一個規定的情境和任務,導演和編劇希望你在這個狀態下說你自己想說的話,很像拍紀錄片的感覺。那時候演著演著我都有點分不清自己和角色之間的界限在哪裡了。當時素汐姐說就給我們一張沙發,我們幾個人坐在那就能開始一場戲。這種創作體驗我很少遇見,也從中汲取到了很多養分。」

(圖/《我在他鄉挺好的》)
周雨彤始終對自己保持著一種審視的目光,「我自己看得很清楚,有的表演我一看就知道那天狀態沒有打開,能過得去,但不夠好。有幾場表演我自己看的時候都會覺得,哎呦,這是我演的嘛,那一刻一定是老天爺在賞我飯吃。」
在《春色寄情人》里,周雨彤有兩場特別喜歡的戲。一場是陳麥冬第一次給莊潔的假肢穿襪子,「我不知道為什麼,那一瞬間突然好感動,把自己哽咽住了。我沒有流眼淚,就是點到為止,但那種感動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真的是一股暖流充滿著我的身體,讓我覺得好溫暖。」另一場是陳麥冬在給何裊裊講生死課題,「這場戲我本來應該是一個非常堅強的長姐形象,但在那一瞬間,他給何裊裊說的那些話,我自己聽進去了。這兩場戲我都沒有預設到自己會有這麼強烈的感動,完全是生理上的反應。」

(圖/《春色寄情人》)
「我希望能把這些我可以清晰捕捉到的、自己都覺得很珍貴的瞬間,在以後變成一種可以穩定輸出的狀態。」周雨彤說。
拍攝《春色寄情人》時,周雨彤要在一天內完成三場哭戲。哭到最後一場時,周雨彤已經哭得上氣不接下氣了,她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再哭出來了。那是一場在火車站人流中崩潰大哭的戲,只剩下半個小時的拍攝時間,她只能演兩次。「我當時覺得我沒有情緒了。但『321』開始後,我坐在那真的哭出來了。然後特別逗,有一個趕車的路人,他沒看到攝像機,看見我在那哭,還給我拿了包紙,問我『沒事吧』。人家肯定覺得這個姑娘怎麼那麼奇怪啊,但真的很溫暖。」

(圖/《春色寄情人》)
這一刻,誤入的路人像是連接兩個時空的開關,他可以證明,莊潔在這一刻真的到來了。

如果向外索取,
安全感就是個無底洞
你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演員?
周雨彤的回答里,沒有提到她想拿什麼獎,也沒有提到她渴望出演什麼角色,而是講述了一段她的故事。
有快兩年的時間,她都沒有戲拍。沒有工作,那就大量刷片。當時她給自己下達了一個任務,每天至少要看三部電影,看不動了就看《老友記》,睡前也一定要看《老友記》,不然就會失眠,「它給我帶來了非常多的能量。我覺得他們就像是一群我素未謀面的朋友,一直在鼓勵著我向前走。」

(圖/《老友記》)
周雨彤不是一個喜歡給自己制定目標的人,她一直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是在去年年末,她腦中突然出現了一個問題:「演員這個職業,我在追求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想到這,她腦中閃現的是自己最迷茫的那段日子一直在看《老友記》的場景。「如果我也能有一個這樣的作品,能給睡不著覺的人內心帶來一點溫暖和光,我覺得這就是做演員最大的意義。我不知道會照亮誰,也不知道會溫暖多少人,但這不重要,有一個是一個。」
或許是受此影響,周雨彤今年特別想嘗試拍一部女性喜劇作品,「去年年底我和李漠導演二次合作拍的《180天重啟計劃》就有一點偏家庭喜劇,體驗很好,但我想再演一部偏女性喜劇的作品,比如說公路喜劇片啊,既輕巧有趣,又關注到女性的個人成長。我最早學導演時的張佳蕾老師和我說過,『不管你將來做演員還是導演,你要感受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你要知道這個世界有哪些群體想要被看見,你要知道當下的社會大家在關注什麼。』這句話我現在還記得。」

(圖/由被訪者供圖)
剛入行那幾年,周雨彤沒有什麼選擇劇本的機會,她是那個被選擇的人。現在的她,選擇劇本的範圍變大了,她也希望能嘗試自己沒見過的風格。「能夠和編劇老師、導演學到東西,或者編劇的切入點、對待事物的看法讓我覺得新鮮、有趣,開發出我更多面的作品,我都想嘗試。」周雨彤說。
在許多人眼中,周雨彤是個很會活躍氣氛、看起來沒有煩惱的人,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很愛哭。「我的開心、治癒、生命力,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一面。我記得很多年前我發了一條蠻治癒的微博,然後我無意間看到一條評論,那個人說他今天過得特別不好,但是看見我這條微博,他突然又覺得生活也沒那麼糟糕了。我覺得這就是我們作為公眾人物的意義。大家過得都挺辛苦,沒有人想承擔另外一個人的不如意,所以我想儘可能讓大家看到我好的一面。至於我的痛苦、我的糾結、我的掙扎,留給下一部戲就好了。」

(圖/《春色寄情人》)
周雨彤曾經是一個缺少安全感的人,她總想把安全感寄托在事業或者別人身上。這兩年她一直在劇組拍戲,從一個角色到另一個角色。在決定給自己放個假後,周雨彤突然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該玩什麼。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她都不知道要怎麼生活。她突然意識到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怎麼把戲變成了我的全部?我自己去哪了?在劇組的時候我可以哭可以笑,但當我回歸到自己之後,我怎麼變得空蕩蕩的?」
她開始反思自己。她突然明白:「如果我把安全感寄托在外力之上,那我的一生都會過得很辛苦,因為這些東西隨時都可能會崩塌。就像剛入行的時候你希望有戲拍,有戲拍的時候你希望能有好戲拍,有好戲拍的時候你又會希望能一直有好戲拍,你的慾望是不會滿足的。對人也是這樣,如果向外索取,那麼安全感就是個無底洞。當你把對外索取換成對內,你就會覺得享受就好了——享受這個職業是瞬息萬變的,享受今天在高處、明天占低位,享受有人愛你、有人離開。這樣你的心態就會平和很多,這也是我今年才悟出來的道理。」

(圖/《大宋少年志2》)
於是,她開始琢磨自己,「我是個很慢熱的人,有時候事情已經過去了,我才會明白原來我這樣做會更好,以至於我之前拍戲的時候會留下一些遺憾。現在我覺得當我把人性研究透了再去演戲,一定會更真實。」
周雨彤很難講自己對當下的狀態是否滿意,「我是一個比較倔的人,有時候我知道自己哪裡有問題,但我死性不改。有時候別人和我說前面有一個坑你別跳啊,我就想跳下去試試看,疼了之後我才能知道,原來人摔到坑裡是這種感覺。作為演員你總要品嘗各種各樣的情緒和滋味吧!你要知道打傘是什麼感覺,也要知道淋雨是什麼感覺。我們總要去經歷。」
就像周雨彤最喜歡的電影《時時刻刻》中的那句話:「This is my life.This is my choice.」
校對:遇見;運營:嘻嘻;排版:段枚妤

《新周刊》總658期《野孩子》
點擊封面即可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