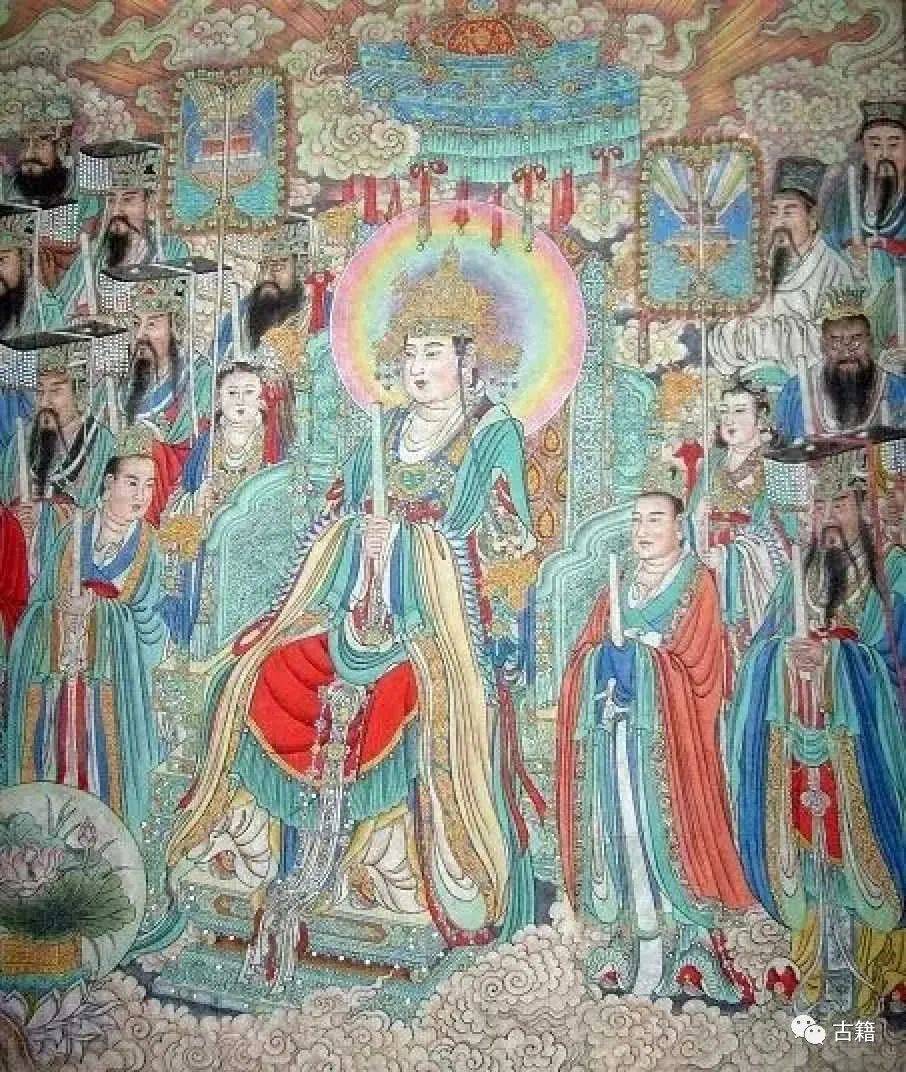
提要:西王母之地域在西漢中期發生了一次深刻的變化,由早期的不確定或較近的西方向更遠的西域國家逐漸西移。西王母為漢地本土神祗,西漢中期以後成為西方仙境的代表而有可能與西域神話相結合,隨著人們對西域認識的逐漸擴展而不斷西移,總在當時認識的最西國家之西。
西王母是中國早期神話中最為重要的神祗之一,從漢晉時期的墓葬考古材料來看,甚至一度成為佛、道教流行之前,中國宗教信仰中的一位主神。西王母信仰和西王母圖像的產生、流行有其過程,有其背景,把握西王母信仰演變的階段性是觀察這種過程和背景的最佳視角。但西王母問題包括的內容是比較複雜的,一時不能完全把握,筆者發現從其地域的演變這一角度觀察其演變之跡或許能提示出一些問題,達管中窺豹之效。
一 西漢中期以前西王母之地域
文獻中對於西王母的記載,最重要的莫過於神話色彩極濃的兩部著作——《山海經》和《穆天子傳》。這兩部書的成書年代雖然都不太明確,但其主體部分出於秦漢以前已經得到大體的認可。《山海經》中或言其居於「玉山」,或言其居於「崑崙」,[1]似乎沒有確定所在。「玉山」,「此山多玉石,因以名雲」,[2]只言其名稱來源,而未注其所在。《史記·大宛列傳》中載:「漢使窮河源,河源出於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雲。」[3]我們是否能依此判斷,《山海經》中多玉石的「玉山」即是「崑崙」?顯然不是。《大宛列傳》中的「崑崙」明顯是漢武帝的一廂情願,並非此多玉石之山即是崑崙,所以司馬遷在文末批評到: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4]
「玉山」也並非一特指,正如郭璞所說,多玉之山皆可名玉山。《蜀王本紀》中載:「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鱉靈決玉山,民得陸處。」[5]此玉山在蜀地,我們顯然不能把它等同於《山海經》中的玉山,更不能等同於崑崙。「崑崙」在《山海經》中多次出現,並無一定之地,大多在西方,但東南方亦有崑崙。《海外南經》云:「崑崙虛在其東,虛四方。一曰在岐舌東,為虛四方」,畢沅云:「此東海方丈山也。《爾雅·釋地》云:『三成為崑崙丘』,是『崑崙』者,高山皆得名之。此在東南方,當即方丈山也。」[6]《水經注·河水》亦載:「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7],大概也本於《山海經》,因為後期文獻中崑崙皆在西方。此《大荒西經》中的崑崙應該是西方某一高山,但無確指。可見《山海經》中的「玉山」、「崑崙」只是一種神話的虛指,並非一確定之地。郭璞作注時就全然不注這些地名之所在,晉之地理、神話學家尚且全然不知,今人又從何確認?《穆天子傳》雖也是神話色彩濃厚的著作,但與《山海經》不同,其以西周以來流傳的歷史故事為本,然後神化之,有真實的歷史內核。[8]所以後世正史中也屢引述其事,司馬遷作《史記》曾明言「《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但在《趙世家》中卻引述了周穆王見西王母之事,[9]可見一斑。《穆天子傳》中載周穆王西征見西王母於「弇山」、「西王母之邦」。[10]
民國時期的不少學者都曾將《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之邦考定在西域某國,如丁謙先生定其為「亞西里亞(Assyria)國」,劉師培先生定其為「亞西里亞國都之尼尼微(Nineveh or Ninua)」,顧實先生將其考定在「波斯之第希蘭(Teheran)」[11]。但多有牽強附會之處,不可深信。張星烺先生評價到「本書(《穆天子傳》)古地名,多已不可考,丁謙之書多武斷,顧實之說亦浮誇,皆不能使吾人滿足也」[12],可謂中肯。
但如前所述,《穆天子傳》並非純然神話,有一定的早期歷史內核,其所載西王母之地有飄渺難定的神話之說,亦有堪入史籍的現實之說流傳於後世。《十六國春秋》載:「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山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在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一作「玉室」),珠璣鏤飾,煥若神宮。」[13]《晉書·張軌傳》亦同,[14]皆說穆王見西王母之地在河西酒泉一帶。這種說法看似出於較晚的文獻,但仔細考徵,其自有一脈相承的來源。《漢書·地理志下》載:「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祠,有弱水、崑崙山祠。」[15]臨羌在河西金城郡,向西北塞外推進,也就愈與酒泉相近,正與前引《十六國春秋》與《晉書》所載周穆王見西王母之地相合。《論衡·恢國篇》亦載:「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遠之外,而漢屬之。」[16]言其在金城郡塞外,與《漢書·地理志》相同,可見西王母在河西之說並非後世臆造,亦是一自成系統的說法。
而上述《漢書·地理志》、《論衡》、《十六國春秋》、《晉書》中關於西王母地域之記載與後面將談到的《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魏書·西域傳》、《後魏書·西域傳》、《北史·西域傳》的記載相去甚遠,明顯出於另一系統。筆者認為,前一系統便是來源於周穆王西征的傳統說法,所以此系統的材料中屢次談到周穆王和周代,而後一系統的材料中從不涉及這一點。《漢書·地理志》中雖未明言周穆王,但其與同書《西域傳》所載完全不同,顯然屬於前一系統。可見,西王母居於河西一帶的說法是有其源流、自成體系的,是《穆天子傳》所載周穆王見西王母神話的一個現實版本,甚至是其現實來源。
綜上所述,秦漢以前關於西王母地域的說法大體上有兩類。一類是神話式的,雖有各種名目,但並無實際所在,只是西方和西極某地的虛指,以《山海經》和《穆天子傳》最為典型。這種說法一直流行到西漢中期以前,《爾雅·釋地第九》認其為西荒之地,[17]《淮南子·墜形訓》說其「在流沙之濱」[18],皆是虛指。另一類是歷史式的,是周穆王西征故事的歷史式流傳,其說西王母皆在河西(今甘肅、青海)一帶。持這種說法的雖然都是先秦以後的文獻,但傳承有序,繫於穆王之事,且與當時的流行看法完全不同,應該有更早的來源。
二 西漢中期以後西王母之地域
西漢中期以後關於西王母地域的說法亦可分為兩類:一類持其在河西一帶,已如上述;一類則隨著西域的開闢,隨著人們對西方世界認識的推進而一路將其西推,處於不斷的西進之中。後者更代表當時的流行觀點。
《史記·大宛列傳》中根據張騫等人的報告記載: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瓮。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19]
張騫等漢使者並未到達條枝,所謂「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也」[20],所以才有「安息長老傳聞」之說。
「西海」即地中海,可見「條枝」在地中海岸,說者或以其為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21]不論其地究竟在何,總之為當時人認為的最西之國,所以《漢書·西域傳》中說「自條枝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雲」[22]。《大宛列傳》言「(安息)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顏注「犛靬即大秦也」[23],《後漢書·西域傳》亦載「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24],「大秦」即羅馬帝國,似乎「黎軒」才是當時之最西之國。其實「黎軒」即「大秦」的說法起於東漢以後,[25]故而《後漢書》和顏注有此說,查《史記》、《漢書》中所列之序皆為「安息、奄蔡、黎軒、條枝」[26],即使其序非一列向西,也從未言「黎軒」在「條枝」西者,《後漢書》中才有這種說法。可知西漢時期所知之最西國應該是「條枝」,所以《漢書》中言其西便是日落之處,不復有國度矣。
「大鳥」、「大鳥卵」,說者多以為是鴕鳥,從今天的眼光看,此說固然恰當,但古人認其為神奇之物,故屢屢提及。《山海經·大荒西經》載:「西有王母之山,……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鸞鳳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郝懿行疏「『西有』當為『有西』,《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八卷引此經作『西王母山』可證」[27]。《呂氏春秋·孝行覽》亦載「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高誘注「丸,古卵字也」[28]。從當時人的角度看,或許此西王母之地的大鳥、大鳥卵,即是「西王母之山」、「流沙之西」的「鳳鳥」、「鳳鳥卵」,故多稱奇之。如前所述,漢武帝既然能根據《禹本紀》、《山海經》將河源之山認作崑崙,也可以將此大鳥、大鳥卵認作西王母之地的鳳鳥和鳳鳥卵。
「善眩」,《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悅」,顏注「眩,讀與幻同,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29]。以今天的眼光看這些不過是雜技與魔術,但古人卻以之為幻術。《列子·周穆王》中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張湛注「化人,幻人也」,而此「化人」能施行升天之幻術,令穆王「目眩不能得視」[30]。或許《列子》中西極之國的「化人」正是此處西極之國的「眩人」,當時人認為他們在西王母之地,幻術即與仙術有關。
《漢書·西域傳》中此段與《史記》所載基本相同,[31]雖然西漢中期以後對西域的認識繼有發展,所謂「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32],但終西漢一代對此「不屬都護」的西極之地的認識還沒有什麼發展,故而基本照抄《史記》。《後漢書·西域傳》中又將西王母之地望西推至當時所知的西極之國——大秦:「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或雲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33]「大秦」即羅馬帝國。東漢以來對西域的認識又有增進,西漢使者皆未能到條枝,而東漢「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枝」[34],甘英雖然最終未能渡海至大秦,但對西方的知識無疑大大增加,所以《漢書》載條枝以西便是日落之處,而此處則推至大秦之西。隨著西王母的西移,西王母之地的「眩人(幻人)」也西移至大秦:
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35]
大秦之地不僅有眩人,而且「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只是范曄出於理性的考慮,所以「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雲」[36]。
《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載:
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37]
亦言西王母在大秦西,雖然中間又生出許多地名,但皆為虛指,蓋大秦之西已無時人所知之國度。《魏略》之成書還要早於《後漢書》,但其《西戎傳》所言多詭怪混亂,為范曄所不取。如上引記載中便錯把大夏、月氏等放在大秦之西。《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在向西敘述到條枝後轉向東敘述大夏、大月氏等國,或許是根據使者報告其見聞的順序(使者根據其往返見聞的順序來報告)而記,且說明條枝才是最西端。《魏略·西戎傳》的作者(或許是裴松之錯引)不明古書體例,竟把大夏、月氏排到大秦、西王母之西,失察之深矣。
北齊魏收《魏書》、隋魏湛《後魏書》與唐李延壽《北史》之《西域傳》由於歷代轉抄刪補,以至於「收史相亂,卷第殊舛,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38],但對於西王母之記載大體上還是比較清楚的。亦言西王母在大秦之西,欲再向西推,但終是虛指。[39]
綜上所述,西漢中期以後直到魏晉南北朝,西王母之地域有了另外一種較為確切的認識,且為當時的流行觀點。認為西王母之地在當時所知的西極外國,並不斷隨著對西方認識的增進而西移。而西王母往往也與這些西極外國的種種奇聞異事聯繫起來,甚至和西域的傳聞聯繫起來。
三 西王母相關問題的討論
關於西王母地域的看法在西漢中期時有一次明顯的轉變,之前不是虛幻縹緲的神話之說,就是在河西一帶的歷史之說,而之後則流行在西極異國的說法,並且越推越遠,是一個由虛到實、由近及遠的轉變過程。這樣的過程說明西王母神話之源的方位更可能在本土,而不是西域。
西王母本是本土信仰中西方之地的一個神,西漢中期以前對西方世界的認識很有限,西王母之地或只能是西方的虛指,或只能在較近的西方(西周以來的歷史性傳說就認為在河西一帶)。張騫鑿空以後,人們對西方世界的認識大大增加,知道了許多以前不知道的國度,西王母之地才可能被西推到這些遙遠的國度上。而當西王母被西推到這些國度後便有可能與這些地方的傳說相結合,「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的記載提示了我們這種可能性。可以推想,當漢使向安息長老打聽西王母的所在時(漢使應該是有意尋找,而不是偶爾聽聞的,下詳),安息長老只能根據自己理解的「西王母」來回答,而這個「西王母」更可能不是漢使要詢問之西王母,而是安息人信仰的西方女神,西王母與西方女神的信仰便有機會結合起來。不過這是「流」而不是「源」,只有在西漢中期以後才可能出現。西漢中晚期以後,喪葬藝術中十分流行西王母的圖像,其出現之時,正是「西王母在西域」的觀念流行之時。許多學者從外來因素的角度來研究此時的西王母圖像,[40]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應該繼續深化,不過要把握源流問題,如果依此認為西王母本身就是外來之神[41]就不正確了。
張騫鑿空是人們把西王母之地確定並西推於西域外國的客觀條件,但西漢中期以後對西王母的信仰何以如此興盛,尤其是在喪葬信仰中,時人為何如此熱情地將西王母逐漸西移,這就首先要了解西王母的性質及當時的信仰背景。西漢中期以前關於西王母的性質有著不同的說法,西王母或神或人、或好或惡,[42]正與西王母地域之不確定性相同。而西漢中期以後,人們對西王母性質的認識則十分確定,西王母就是西方一位擁有不死之藥,能令人升天成仙的女神。西漢中晚期以後西王母的圖像便在喪葬文化中廣為流行,由於長生不死並不曾實現,於是死後的升仙便被寄予厚望,西王母仙境成為人們死後理想的永恆家園。這一轉變又是完成於西漢中期。
神仙思想起源於戰國時期燕國和齊國的沿渤海地區,[43]秦皇漢武更將求仙活動推到高潮。但直到武帝早年的求仙活動都是往東海進行,張騫鑿空西域後,人們便把目光投向了新奇的西方。[44]
戰國秦漢時盛行五行觀念,五行中東方屬木,其性為生,當然容易與長生聯繫;而西方屬金,「金」一方面有肅殺之性,一方面又有不朽之性。故西方一方面是肅殺之方,一方面又是不死之地。《淮南子·時則訓》中載:「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沉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45]。《山海經》中西方是不死信仰的一個主要方位,如操有不死藥的群巫便兩見於《海內西經》和《大荒西經》。[46]在東海尋仙屢屢失敗的情況下,漢武帝便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和西王母,其向西域遣使的一個目的就是尋找西王母,故而使者的報告中才有「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的內容。但西王母是永遠找不到的,所以總會在人們所知的西極之國之西,隨著人們認識的逐步推進,西王母於是也逐步向西推進,直到一串虛無的地名。
漢武帝向西域遣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求仙,還可以從其對使者的任用上看出。《史記·大宛列傳》載:「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47]而同書《孝武本紀》載方士李少君死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又載方士欒大「見用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扼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48],可見這些使者與方士何其相似,只是使者向西而方士向東而已。
筆者前面也討論過時人認為西極之國的大鳥、大鳥卵、眩人與西王母的關係。大鳥即是能助人升仙的鳳鳥,眩人則是會仙術(幻術)之人,它們皆近西王母之地,武帝得到它們時十分地高興。不少學者也相信武帝伐大宛的目的之一便是取得能載人升仙的「天馬」。[49]《漢武故事》中亦載有武帝曾向西王母求不死之藥而不遂的傳說,[50]其書雖系晚出,武帝也不可能見過西王母,但這一故事正是根據武帝對西王母的信仰而編造。
凡此種種皆可見武帝向西方和西王母求仙的熱情。上行下效,這種時代風潮便很快地流行開來,司馬相如的《大人賦》為奉承武帝之作,其中便寫到「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皓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51]。西漢中晚期以後開始流行於喪葬藝術中的西王母圖像便是這種熱情向下蔓延的產物。
東漢晚期當這種熱情極盛之時卻開始出現新的變化,即一些西王母圖像開始被佛像所替換。[52]大概因為長期以來西王母渺不可尋,而隨著時人對西方認識的增進和西域佛教的傳播,人們開始知道西方的大神原來是佛陀,於是開始用佛像來替換西王母像。雖然此時佛像的意義還只是原來西王母信仰的延續,但人們長期以來對西方之神的信仰熱情無疑為佛教的傳入準備了主觀條件。而另一方面,新興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將傳統的西王母信仰收入自己的信仰體系之中,其後西王母進入道教的神階體系,成為人們升天的第二站。[53]隨著佛、道信仰之興盛,傳統的西王母信仰雖有所保延,終衰落不振矣!
[1] 郭璞注;袁珂點校:《山海經校注》(增補修訂本),巴蜀書社,1993年,第59、358、466頁。
[2] 《山海經校注》,第60頁。
[3]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中華書局,1959年,第3173頁。
[4]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第3179頁。
[5]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八引,中華書局,1960年,第3944頁。
[6] 《山海經校注》,第241頁。
[7]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一,中華書局,2007年,第12頁。
[8] 楊善群:《〈穆天子傳〉的真偽及其史料價值》,《中華文史論叢》第5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楊寬:《〈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中華文史論叢》第55輯。
[9] 《史記》卷四十三,第1779頁。
[10] 〔晉〕郭璞註:《穆天子傳》卷三,《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頁。
[11] 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卷二,《民國叢書》第三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3冊,第130、142、143頁。
[12]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一冊)》,《民國叢書》第五編,第28冊,第78頁。
[13] 〔魏〕崔鴻撰;〔清〕湯球輯補:《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中華書局,1985年,第503頁。
[14]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六,中華書局,1974年,第2240頁。
[15] 〔漢〕班固:《漢書》卷二十八下,中華書局,1962年,第1611頁。
[16] 〔漢〕王充:《論衡》,《諸子集成》第7冊,上海書店,1986年,第193頁。
[17]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註疏》卷七,《十三經註疏》阮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下冊,第2616頁。
[18] 〔漢〕劉安著;〔漢〕高誘註:《淮南子注》卷四,《諸子集成》第7冊,第63頁。
[19]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第3163、3164頁。
[20]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註:《後漢書》卷八十八,中華書局,1965年,第2920頁。
[21]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82~209頁。
[22] 《漢書》卷九十六上,第3888頁。
[23] 《漢書》卷六十一,第2694頁。
[24] 《後漢書》卷八十八,第2919頁。
[25] 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第179頁。
[26] 《史記·大宛列傳》,第3170頁;《漢書·張騫李廣利傳》,第2694頁。
[27] 〔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巴蜀書社,1985年,第460頁。
[28] 〔漢〕高誘註:《呂氏春秋》卷十四,《諸子集成》第6冊,第141頁。
[29] 《漢書》卷六十一,第2696頁。
[30] 〔晉〕張湛註:《列子》卷三,《諸子集成》(第3冊),第31、32頁。
[31] 《漢書》卷九十六上,第3888頁。
[32] 《漢書》卷九十六上,第3874頁。
[33] 《後漢書》卷八十八,第2919、2920頁。
[34] 《後漢書》卷八十八,第2918頁。
[35] 《後漢書》卷八十六,第2851頁。
[36] 《後漢書》卷八十八,第2919、2920頁。
[37]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註:《三國志》卷三十,中華書局,1975年,第862頁。
[38]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卷四十五,中華書局,1997年,上冊,第628頁。
[39] 〔北齊〕 魏收:《魏書》卷一百二,中華書局,1974年,第2275、2276頁;〔唐〕李延壽:《北史》卷九十七,中華書局,1974年,第3228頁。
[40] 巫鴻著;柳揚,岑河譯:《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三聯書店,2006年,第149~157頁;李凇:《論漢代藝術中的西王母圖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0~309頁;周靜:《漢晉時期西南地區有關西王母神話考古資料的類型及其特點》,《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創建四十周年及馮漢驥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88、389頁。
[41] 森雅子:《西王母の原像——中國古代神話におけ地母神の研究》,《史學》第56卷第3號,1986年,第61~93頁。
[42] 參見《山海經校注》,第59、345頁;《莊子集釋》,《諸子集成》第3冊,第113頁;《穆天子傳》卷三,《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第14頁;《淮南子注》卷六,《諸子集成》第7冊,第96、98頁;〔漢〕 戴德撰,〔周〕 盧辯註:《大戴禮記》卷十一,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第192頁。
[43]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10頁。
[44] 余英時著;侯旭東譯:《東漢生死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頁。
[45] 《淮南子注》卷五,《諸子集成》第7冊,第84頁。
[46] 《山海經校注》,第352、453、454頁。
[47]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第3171頁。
[48] 《史記》卷十二,第455、464頁。
[49] 余英時:《東漢生死觀》,第31頁;霍巍:《天馬、神龍與崑崙神話》,收入霍巍、趙德云:《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的對外文化交流》,巴蜀書社,2007年,第200頁。
[50] 魯迅輯錄:《古小說鉤沉》,《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464頁。
[51] 《漢書·司馬相如傳》卷五十七下引,第2596頁。
[52] 霍巍:《綿陽何家山漢墓出土三段式神獸鏡的相關問題》,《考古》2000年第5期;霍巍:《胡人俑、有翼神獸、西王母圖像的考察》、《錢樹佛像與早期佛教的傳入》、《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的對外文化交流》;巫鴻:《早期中國藝術中的佛教因素(2—3世紀)》,收入《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下冊,三聯書店,2005年。
[53] 張勳燎:《重慶、甘肅和四川東漢墓出土的幾種西王母天門圖像材料與道教》,收入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線裝書局,2006年,第3冊。
作者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0級博士研究生
來源:《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