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賣公司對拍品不保真,是藝術品行業的一個「行規」。但為什麼實力更強,對藝術品收藏和流通更專業的拍賣機構,反而可以通過一紙「不保真」的聲明就可以免責呢?免責的範圍和效力又是什麼呢?除了法律規定,一個與著名畫家吳冠中的作品相關的案例,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通過這個案例,在我國藝術品拍賣市場重申了對拍賣法就拍賣人免責條款的確認效力,以及對於「買者自負」這一長期以來約定俗成形成的交易慣例的維護,固化了拍賣行和競拍人之間的法律地位和權利義務關係。我們再回顧一下此案的始末:
起訴和答辯
原告蘇小羅(化名)起訴稱:2005年11月,我在翰海公司網站上看到該公司將舉辦2005秋季油畫雕塑拍賣會的公告信息,其中重點介紹了此次拍賣有吳冠中的油畫作品《池塘》。為證明該畫是吳冠中所作,翰海公司提供了一組由安徽美術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的《風景油畫選輯(三)》明信片,其中第五張是《池塘》。翰海公司並在其印製的《拍賣圖錄》中對《池塘》作了詳盡的介紹。
由於翰海公司是國內著名文物專業拍賣公司,其在拍賣公告、《拍賣圖錄》中對《池塘》的描述加入其主觀意見,以肯定的口吻對該畫作了詳盡的介紹和評價,使我相信該畫的真實性。2005年12月11日,我經競價以2300000元拍得署名吳冠中的油畫《池塘》,並向翰海公司支付佣金230000元。後我發現所拍得的《池塘》是假畫,而該畫是蕭大元委託翰海公司拍賣的,故起訴請求:1、撤銷我與翰海公司拍賣合同關係;2、蕭大元(化名)、翰海公司連帶返還拍賣款2300000元、佣金230000元;3、蕭大元、翰海公司賠償律師費100000元、調查取證差旅費20000元、證據保全費1000元,共計121000元,並由翰海公司、蕭大元承擔本案訴訟費。
蕭大元在一審法院答辯稱,其與蘇小羅不存在合同關係,不是本案適格被告,且蘇小羅的起訴已經超過訴訟時效期間、行使撤銷權已超過法定除斥期間。蕭大元同時提出翰海公司在拍賣前發布了拍賣公告、展示了拍賣標的,蘇小羅怠於行使查驗權利,拍賣風險應由其自行承擔,不同意蘇小羅的訴訟請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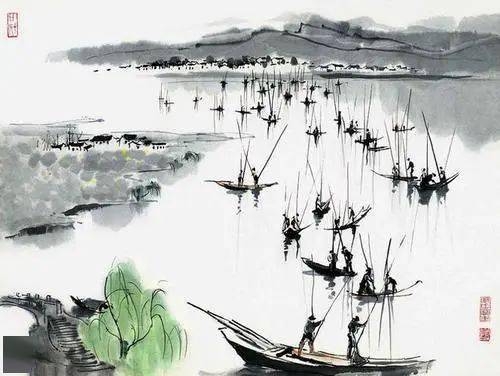
翰海公司在一審法院答辯認為,其履行了拍賣法所規定的全部義務,對委託人蕭大元的身份及其對拍賣標的的所有權、處分權進行了審核。翰海公司在《拍賣圖錄》上刊登了《業務規則》,其中作出了免責聲明,明確規定不對拍賣品真偽承擔責任。蘇小羅在現場辦理競買登記手續時,簽名確認「買方已認真閱讀《業務規則》……買方同意所有拍賣會成交之中國字畫、瓷器等其他拍賣品均無需附帶真確保證」。蘇小羅起訴請求撤銷雙方合同於法無據,不同意蘇小羅的訴訟請求。
一審事實和證據
一審法院查明:2005年9月2日,蕭大元與翰海公司簽訂《北京翰海拍賣有限公司委託拍賣合同書》(編號A0012708),約定蕭大元將油畫《池塘》委託翰海公司進行拍賣,註明作者為吳冠中,保留價2200000元,並備註「安徽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出版《風景油畫選輯》圖五」。
蕭大元稱《池塘》系從張帆處以1200000元購得,但雙方並未就此簽訂書面買賣合同。原審訴訟中,蕭大元提供2008年7月9日《北京青年報》,其中報道「張帆告訴記者當時一個新加坡的商人薛德光委託他們來賣這幅油畫《池塘》……蕭大元買了這幅畫……張帆告訴記者,去年蕭先生找過很多次,說畫可能有問題,希望能不能退畫……但薛德光一直沒有再聯繫上。」蕭大元並提供中國工商銀行2005年9月2日、7日、17日、10月17日個人業務憑證4張,借方是蕭大元、貸方是張帆,用以證明從張帆處以1200000元對價購買油畫《池塘》。
翰海公司稱拍賣公司只核實拍賣品的權利狀況,沒有義務核實真偽,也沒有詢問此畫的來源,畫的瑕疵應由蕭大元保證。就訴爭拍品在拍賣前的審核過程,翰海公司未提供任何證據。
2005年12月11日,翰海公司在網上發布2005年秋季油畫雕塑專場拍賣公告,其中重點拍品介紹有如下內容:「本場第二件『雙款拍品』是吳冠中油畫作品《池塘》,畫於1972年,時年53歲。十年後,他又將此畫修改一下,並在畫上題寫『抽暇改老畫,好似故地重遊。一九八二年』。畫面以他下放的農村為題材,崇山峻岭,迎面而立,不乏中國北宋山水畫的雄渾厚重;中景林木繁密,充分體現出他在歐洲所學到的繪畫技藝;近處則是池塘澄明,顯現出中西融合的藝術風格。該拍品評估1800000元至2500000元人民幣」。
翰海公司在其印製的《拍賣圖錄》中對油畫《池塘》有以下說明:「畫於1972年,(吳冠中)時年53歲。十年後,他又將此畫修改一下,並在畫上題寫『抽暇改老畫,好似故地重遊。一九八二年』。畫面以他下放的農村為題材,崇山峻岭,迎面而立,有中國北宋時期國畫的崇高美感;中景是茂密的樹林,充分體現出他在歐洲所學到的繪畫技藝;近處是池塘,點明要有中西融合的藝術風格。吳冠中在1970年下放到河北農村勞動之時,其妻子亦被下放到農村勞動。長子可雨在內蒙牧羊,次子有宏于山西農村勞動。1972年,53歲的吳冠中被允許每周作畫一天,因沒有足夠畫具,只好畫在紙板上,以農家柳條編成的糞筐作畫箱,人們戲稱他為『糞筐畫派』。畫了一批油畫,包括《瓜藤》《高粱與棉花》《房東家》等。他當時對自己的藝術要求是群眾點頭、專家鼓掌,由此形成他後來提出的『風箏不斷線』的目標。1977年起,吳冠中先後到廣西南寧、浙江紹興、福建廈門、鼓浪嶼、武夷山、江西井岡山等地寫生,並為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作巨幅油畫《長江三峽》,1979年,吳冠中被邀請到四川、湖北、湖南、浙江、江蘇、廣東、廣西、山西、遼寧等省巡迴展出,名聲大振大江南北」。以上內容也在翰海公司網頁資料中出現。
《拍賣圖錄》中關於《池塘》的著錄介紹中,載有:「1、《風景油畫選輯二》,安徽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出版,圖版5。2、《吳冠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p197,吳冠中年表;1972年」。
關於著錄1,蘇小羅稱翰海公司曾提供一套署名為安徽美術出版社1984年第1版的《風景油畫選輯(三)》明信片,其中第5張為「吳冠中,池塘」。蘇小羅庭審中提供的工商查詢信息顯示,安徽美術出版社成立於1986年9月25日。且該明信片的印刷企業也是偽造的,並不存在。原審訴訟中,翰海公司與蕭大元均否認曾向蘇小羅提供過該套明信片。翰海公司稱其提供的是安徽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油畫風景選輯二》明信片,在圖版五上載有《池塘》。蕭大元提供《篆刻淺談》,該書載明是安徽美術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
關於著錄2,《吳冠中》一書載明,吳冠中「1972年、53歲,年中,被軍隊領導調到邢台師部指導文藝兵作畫,作油畫《池塘》《西柏坡山村》等」。翰海公司稱在《拍賣圖錄》中對訴爭拍品的介紹內容來自該書,但關於訴爭拍品的具體描述是翰海公司自己寫的。
翰海公司在《拍賣圖錄》中印製的業務規則中,有如下規定:第八條,本公司在拍賣日前編印的圖錄或以其他形式對任何拍賣品的作者、來歷、年代、尺寸、質地、裝裱、歸屬、真實性、出處、保存情況、估價等方面的介紹,僅供買家參考,不表明本公司的任何擔保;第二十一條,本公司任何人或代理人用任何方式對拍賣品所作的介紹、描述及評價屬參考意見,不表示本公司對拍賣品的任何擔保;第二十二條,同時具備以下條件,本公司可以考慮撤銷交易並向買家悉數退款:1、從拍賣日起二十一日內,買家向本公司提出書面報告,指出該拍賣品為贗品;2、收到書面報告十四日內,本公司收回該拍賣品,該拍賣品必須保持拍賣當日原狀;3、買家提出的依據能令本公司確信該拍賣品為贗品,同時買家擁有該物品無可置疑的所有權和轉讓權;4、該拍賣品確係本公司出售;第四十九條,本公司有權對委託人委託本公司拍賣的任何物品攝影、攝像、進行圖錄出版、文告、展示和其他形式的影像作品,並擁有上述作品的著作權,但本公司及其職員或其代理人不對其意見的準確性(包括作品真偽)承擔任何責任。
2005年12月11日,蘇小羅作為競買人簽署了《競投登記單》,其中載明:買方已認真閱讀翰海公司的業務規則,並同意在拍賣交易中遵守上述業務規則中的一切條款;買方同意所有拍賣會成交之中國字畫、瓷器等其他拍賣品均無需附帶真確保證。
同日,在翰海公司舉辦的2005秋季拍賣會油畫雕塑專場中,蘇小羅現場拍得油畫《池塘》一幅,支付落槌價2300000元和佣金230000元,並取得該拍品。
2007年11月19日,蘇小羅委託上海市金茂律師事務所致函翰海公司((2007)金律函字第1115號律師函),表示《池塘》有偽作之嫌,該函顯示:2007年8月,湖南美術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國家「十一五」重點文化出版項目之一的《吳冠中全集(9卷)》大型叢書,但未收錄《池塘》;2007年8月以來,蘇小羅幾度委託多家國內知名拍賣行拍賣《池塘》,均被拒絕;2007年10月10日,雅昌藝術網發表了東南亞著名收藏家郭瑞騰的文章,題目為《提防利用拍賣活動「洗畫」》,文章直指《池塘》系偽作,並非吳冠中真跡。
2008年7月1日,蘇小羅攜油畫《池塘》到畫家吳冠中家中請求確認真偽,吳冠中認定該畫系偽作,並在該畫外裱玻璃上書寫「此畫非我所作,系偽作,2008年7月1日」。
上述事實,有委託拍賣合同、付款憑證、證書、拍賣圖錄、競投登記單、拍賣成交確認書、網頁資料、報紙書籍資料、函件、當事人陳述等證據在案證明。
一審判決和理由
一審法院認為:在拍賣交易活動中,拍賣人對拍品的瑕疵擔保責任,明顯弱於一般的買賣合同交易,其有權就拍品瑕疵作出免責聲明,因而拍賣活動中競買人或買受人對拍品瑕疵的檢查義務,將明顯重於一般的買賣合同交易。
本案中,蘇小羅通過競買獲得訴爭拍品,其與翰海公司形成拍賣合同關係。蕭大元雖非拍賣合同的直接當事人,但其作為訴爭拍品的委託人,是本案拍賣交易活動中的當事人之一,系本案適格被告;關於訴爭拍品的真偽問題,各方當事人各執一詞。目前尚無證據證明蘇小羅於起訴前的一年即應當知道訴爭拍品是偽作,故蕭大元關於蘇小羅起訴已超過法定除斥期間的抗辯意見不成立;就訴爭拍品的來源問題,蕭大元僅提供新聞報道及若干付款憑據為證,並未提供充分、翔實的證據材料。而翰海公司亦未就此進行必要的詢問和審核。但僅憑蕭大元的舉證欠缺及翰海公司的核查欠缺,尚不足以證實翰海公司或蕭大元在本次拍賣前明確知道或應當知道訴爭拍品系偽作;翰海公司在拍賣過程中,對訴爭拍品進行了一些以真實性為基礎的文字描述。但從這些文字描述本身內容看,並無否定免責聲明並對訴爭拍品做出真確性保證之含義。
在不能證實翰海公司事前知道訴爭拍品系偽作的前提下,翰海公司對訴爭拍品適當地加以真確性描述,應屬正常的交易活動範疇,其描述用語並無過分誇大之處,不構成虛假宣傳;翰海公司針對訴爭拍品真偽瑕疵所作出的免責聲明具備我國《拍賣法》第六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之效力。而蘇小羅在知曉該免責聲明並且在競買前能夠充分了解訴爭拍品實際狀況的情況下,參與競買系其自主決定的結果,其認為在拍賣交易中存在欺詐、重大誤解且顯失公平之事由,要求撤銷拍賣合同的訴訟請求不能得到支持;其要求的翰海公司及蕭大元連帶返還拍賣價款及佣金,並賠償律師費、調查取證差旅費、證據保全費的訴訟請求,亦不能得到支持。
據此,一審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條、第八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一百七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三十五條、第四十八條、第六十一條第二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蘇小羅訴訟請求。
二審訴辯主張
蘇小羅上訴稱:1、翰海公司不能享有《拍賣法》規定的「不保真」免責條款項下的權利。翰海公司未盡到對拍品真偽及拍品來源的審查義務;且翰海公司作虛假宣傳,故意誤導競買人。2、蕭大元提供偽作,並提供偽造的明信片用以證明偽作的真實性,即使免責條款適用於翰海公司,蕭大元也不能因提供偽作享有免責權利。原審法院判決擴大了免責條款的適用範圍,加重了競買人的義務,應予以撤銷。請求撤銷原審判決,支持其原審的全部訴訟請求。
蕭大元、翰海公司對原審判決無異議。
二審理由和判決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藝術品的鑑定工作在實踐中更多依賴於鑑定者的個人經驗和感受,目前尚無法律強制規定的審核方法以及市場經營自發形成並得到廣泛認可的鑑定標準。
本案中,各方當事人對訴爭拍品《池塘》的真偽存在很大爭議,根據現有證據尚不足以對拍品《池塘》的真偽性做出足以令人信服的明確結論。但不可否認,《池塘》一畫經拍賣過程指稱的作者吳冠中本人指認為偽作,該拍品的經濟價值已經受到極大影響,在無法明確拍品真偽的情況下,已客觀形成該拍品存在較大瑕疵。
蕭大元作為《池塘》的委託拍賣人,雖不能提供充分、翔實的證據證明該拍品的來源,但其作為《池塘》一畫的持有人,在並無相反證據證明的情況下,其作為拍品合法所有權人的事實應予確認。且蕭大元雖未能提供拍品來源,根據現有證據,尚不能因此推定其在拍賣前明知或應當知道拍品系偽作。
蘇小羅提出蕭大元經翰海公司向其提供的明信片是偽造的,但蕭大元否認蘇小羅持有的明信片即是其向翰海公司提交的明信片,對此雙方各執一詞,僅以蘇小羅持有的明信片無法證明蕭大元有提供偽造明信片以證明拍品真實性的事實。蘇小羅上訴主張蕭大元應對偽作承擔賠償責任缺乏證據支持,本院不予採信;關於翰海公司所作免責聲明是否有效一節,因現行法律並未明確規定拍賣公司應負有對拍品進行鑑定的責任,且實踐中由拍賣公司對所有拍品進行鑑定也是不可能、不現實的。
翰海公司在此次拍賣活動中履行了公告、展示、告知等義務,其對拍品《池塘》所做的宣傳屬於正常的商業運作,相關內容屬於正常的介紹和對拍品的具體描述範疇,並未發現其中有主觀上的誇大、誘導成分。
根據拍賣法相關規定,拍賣人、委託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者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該內容也同時載入翰海公司業務規則,對此內容蘇小羅在競拍前已簽字確認。作為競買人,蘇小羅在知曉免責聲明並能夠充分了解拍品現狀的情況下參與競拍,是其自主選擇的結果,因此,蘇小羅與翰海公司之間成立的拍賣合同關係是真實有效的,蘇小羅應當自行承擔拍品存在瑕疵的風險。
蘇小羅上訴主張翰海公司不能享有拍賣法規定的「不保真」免責條款項下的權利,於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蘇小羅上訴請求撤銷其與翰海公司的拍賣合同關係;由蕭大元、翰海公司返還拍賣款及佣金、賠償律師費等的訴訟請求,缺乏證據支持,亦不符合法律規定。綜上,原審判決並無不當,本院予以維持。
據此,二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件判決的法律分析
藝術品是拍賣市場的常見拍品之一,但由於目前對藝術品的鑑定並未形成一套為大眾廣泛認可的鑑定標準,就拍品真偽也難達成共識。於是拍賣公司在拍賣規則中規定「瑕疵擔保免責條款」便成為拍賣的行業慣例。本案的核心爭議焦點就在於瀚海公司是否做出了具有法定效力的免責聲明。
一、拍賣標的物現狀查驗責任的分擔
拍賣是一種公開競買的交易活動,它採用賣方委託、公示拍品、當場競價、落槌成交的一系列慣常固定做法來完成買賣交易。
我國《拍賣法》第三條對此亦加以明確規定,即:拍賣是以公開競價形式,將特定物品或者財產權利轉讓給最高應價者的買賣方式。雖然在法學概念上拍賣合同屬於買賣合同的一種,但與一般買賣合同相比,兩者間存在一定差異。
首先,從簽訂合同的雙方當事人來看,拍賣合同是由拍賣公司和買受人達成的協議,拍品的真正權利人作為委託人並不與買受人直接構成合同關係,即拍賣合同的雙方當事人為拍賣人和競買人。
其次,從買賣的程序來看,拍賣的進行必須遵循法定的程序,這與一般買賣可以自由達成有所區別。
再次,從交易的過程來看,拍賣過程與一般買賣合同由標的物所有權人或處分權人與買受人之間直接進行洽談磋商有所不同,拍賣是一種公開競買的現貨交易,採用買方事先看貨,當場叫價,落槌成交的做法。
最後,從法律的適用來看,一般買賣合同適用《合同法》即可,拍賣有著特殊適用的法律,拍賣的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關係以及拍賣程序等,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只有在《拍賣法》及相關法律、行政法規沒有規定的情況下才可能適用《合同法》。
從兩種合同的比較差異可以看出,拍賣的實際交易過程與一般買賣合同中買方、賣方的交易過程有著本質的區別。鑒於拍賣人並非拍品的實際所有權人或控制權人,只是接受權利人委託對拍品進行拍賣,加之拍賣交易過程的特殊性,拍賣人在客觀上無法完全保證拍品毫無瑕疵。因而拍賣合同中拍賣人的法律地位及其權利義務,不能簡單等同於一般買賣合同中的出賣人。故我國《拍賣法》在第十八條中規定「拍賣人有權要求委託人說明拍賣標的的來源和瑕疵」和「拍賣人應當向競買人說明拍賣標的的瑕疵」之際,在第六十一條第二款中又明確規定「拍賣人、委託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
由此可見,在拍賣交易活動中,拍賣人對拍品的瑕疵擔保責任,明顯弱於一般的買賣合同交易,其有權在拍賣交易中就拍品瑕疵作出免責聲明,因而拍賣的競買人或買受人對拍品瑕疵的查驗義務,將明顯重於一般的買賣合同交易。
正因如此,我國《拍賣法》在四十八條中強制性規定「拍賣人應當在拍賣前展示拍賣標的,並提供查看拍賣標的的條件及有關資料。拍賣標的的展示時間不得少於兩日」,同時在三十五條中規定「競買人有權了解拍賣標的的瑕疵,有權查驗拍賣標的和查閱有關拍賣資料」,從而在程序及實體權利上保障參加拍賣的競買人或買受人能夠在拍賣交易完成前有效地全面了解拍品瑕疵情況,處於有備而來、充分了解拍賣標的物現狀的地位,從而彌補立法規定中所弱化之拍賣人瑕疵擔保責任和所強化之買受人查驗義務,使各方當事人在拍賣交易過程中在權利義務上處於一種整體平衡狀態。
二、拍賣人、委託人瑕疵擔保責任免除要件
如前所述,《拍賣法》第六十一條第二款中明確規定「拍賣人、委託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根據該規定,如果委託人和拍賣人事先並不知道拍賣標的的瑕疵,並且向競買人聲明其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和品質,就可以視為其已經將風險事先告知競買人,一旦拍賣成交,買受人即使買受了有瑕疵的物品,也無權撤銷合同,委託人和拍賣人對此也無須承擔民事責任。結合該條規定,縱觀整個《拍賣法》,瑕疵擔保責任的免除要求滿足兩方面的要件,一是拍賣人、委託人在拍賣之前確實不知曉拍品有瑕疵,二是在整個拍賣過程中,拍賣人本著誠實信用原則嚴格依照《拍賣法》規定的程序進行拍賣活動、履行了相應義務。
本案中,從蘇小羅提供的證據及本案中各項證據鏈來看,並無證據顯示翰海公司或蕭大元在本次拍賣前明確知道或應當知道訴爭拍品系偽作,即本案無充足證據證實委託人及拍賣人在拍賣前確實知曉或應當知曉拍賣標的物存在瑕疵。
從拍賣程序是否正當的角度來看,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各方當事人對本次拍賣活動的程序本身均無異議,可以確定翰海公司在就真偽瑕疵作出免責聲明的同時,亦按照《拍賣法》的相關規定為作為競買人之一的蘇小羅行使查驗標的物等權利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條件。
另外,本案中瀚海公司作為拍賣人並沒有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對拍品做出虛假描述或虛假宣傳。翰海公司在拍賣過程中,對訴爭拍品進行了一些以真實性為基礎的文字描述。從這些文字描述本身內容的正常理解看,並沒有否定瀚海公司在業務規則中做出的免責聲明,也沒有對訴爭拍品作出真確性保證的含義。
在不能證實翰海公司事前知道訴爭拍品系偽作的前提下,翰海公司基於受委託關係在拍賣過程中對訴爭拍品適當地加以真確性描述,屬於正常的交易活動範疇,其描述用語本身並無過分誇大訴爭拍品真確性之處,因此這種描述本身尚不足以構成虛假宣傳。
綜上,瀚海公司作為拍賣人在案涉整個拍賣過程中體現出的行為特徵已經滿足《拍賣法》第六十一條關於瑕疵擔保責任免除的要件,在無證據證明翰海公司或蕭大元在本次拍賣前明確知道或應當知道訴爭拍品系偽作的前提下,可以免除他們對拍賣標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
三、拍賣人做出免責聲明的效力
本案涉及的拍賣活動進行過程中,瀚海公司在拍賣會前發布的《拍賣圖錄》中明確刊印了《業務規則》,並於該業務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四十九條明確做出了免責聲明。另外,在拍賣前瀚海公司還與蘇小羅簽署了《競投登記單》,以確定翰海公司在本次拍賣前已經就訴爭拍品的真偽瑕疵作出了免責聲明。
類似的免責聲明在各類拍賣活動中作為一種交易慣例或行業慣例而普遍存在,這類條款或聲明是否因其構成《合同法》上的格式條款而絕對無效,我們認為該類聲明的效力還是要依據《拍賣法》的相關規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該聲明以及拍賣人的實際行為能夠符合《拍賣法》關於瑕疵擔保責任免除的要件規定,即可認定此類免責聲明有效。
本案中,翰海公司在業務規則中制定的對拍品真偽瑕疵的免責聲明,雖然系單方預先擬定且事先未與競買人協商的格式條款,但該免責聲明系基於前述之《拍賣法》第六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具備法律根據,並為蘇小羅在參與競買前已經應當能夠知曉並且理解。且如前所述,在整個拍賣交易中,翰海公司作為拍賣人雖然有權就訴爭拍品的真偽瑕疵作出免責聲明,但同時應當履行《拍賣法》第三十八條、第四十八條等規定,對拍品進行公開展示並為保障競買人及買受人全面了解拍品現狀提供必要的便利條件。
此外,在業務規則中,雖然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四十九條中規定了真偽瑕疵的免責,但第二十二條又規定一定條件下買受人有權選擇撤銷交易。因此,無論就本次拍賣翰海公司所制定的業務規則整體內容而言,還是就本次拍賣活動中蘇小羅作為競買人及最終買受人所享有並能夠實際行使的權利而言,翰海公司針對拍品真偽瑕疵所作出的免責聲明並不存在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情形,故該條款應屬合理,不因其系格式條款而無效。
綜上所述,在不能證實翰海公司及蕭大元事先應知曉訴爭拍品系偽作的情況下,翰海公司在本次拍賣交易中就訴爭拍品的真偽瑕疵作出蘇小羅應當知曉的免責聲明,並通過法律規定的拍賣展示程序有效保障了蘇小羅能夠在競買前充分了解訴爭拍品的現實狀況,且在對訴爭拍品的介紹中亦未採用足以推翻免責聲明的真確性描述或虛假宣傳,故本案中翰海公司針對訴爭拍品真偽瑕疵所作出的免責聲明應當具備我國《拍賣法》第六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的效力。
而蘇小羅在知曉該免責聲明並且在競買前能夠充分了解訴爭拍品實際狀況的情況下,參與競買並因最高叫價而成為訴爭拍品的最終買受人,系其自主決定參與拍賣交易並自主作出選擇所產生的結果,固然有可能因訴爭拍品系偽作而遭受損失,但亦屬藝術品拍賣所特有之現實正常交易風險,蘇小羅在作出競買選擇之時亦應同時承擔此種風險。所以,本案一審判決駁回蘇小羅的全部訴訟請求,二審法院亦判決維持。
藝法觀點
法院認為,藝術品的真實性鑑定工作在實踐中都更多地依賴於鑑定者的個人經驗和感受,目前也沒有法律強制規定的審核方法和市場經營自發形成,並得到廣泛認可的鑑定標準。如果對真實性不能形成合法有效和準確的鑑定,則人民法院審理所依據的相關證據或者案件指向的標的的真實性,合法性以及關聯性就必然存在證明不能的可能,因此,在這樣的案件中就更依靠於由其他證據組成的完整證據鏈,來綜合證明當事人的訴求和主張。
從本案法院的立場可以看出,一方面對委託拍賣人或者畫作的原持有人,在沒有確實充分和相反的證據證明其對畫作的來源明知存在贗品而進行售賣的,其作為合法所有人的事實可以得到確認。
在本案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一張由蕭大元提供的偽造明信片,用以證明其存在故意的偽造和虛假陳述的情形,但法院認為僅以明信片無法證明畫作持有人刻意證明拍品真實性的事實。這可以明顯看出法院主要是以證據強弱來進行裁判,對當事人是否對畫作來源有明確認知,以及對於贗品的流轉是否存在主觀偽造故意的判斷,更傾向於支持和保護畫作持有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就拍賣公司免責聲明的效力,法院認為現行法律並未明確規定拍賣公司應負有對拍品進行鑑定的責任,而且由拍賣公司對拍品進行鑑定,也是不可能不現實的,拍賣公司履行了公告、展示、告知的義務,其宣傳屬於正常的商業運作,相關提供的內容是屬於對拍品介紹的正常描述範疇,未發現有主觀上的誇大、誘導成分,同時競拍人在競拍前已確認了解了拍賣公司的不保證拍賣標的真偽或者品質,以及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的業務規則,因此通過拍賣合同購買畫作的合同關係真實有效,競拍人應當自行承擔拍品存在瑕疵的風險。
可以看出,在對於藝術品流轉中因贗品買賣而發生的爭議,主張權利的一方,必須提供完整的證據鏈和擁有強大的證明能力,作為維護權益最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支撐,否則即使畫作被畫家本人確定為贗品,仍然只能自吞苦果,承擔損失和不利的訴訟後果。
參考資料:
一審判決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初字第9088號判決書。
二審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9)高民終字第3093號判決書。
本文中人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