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錦戲是明朝宮廷戲劇的一種,在明朝之前的文獻中未見記載,清代及以後的文獻亦未載錄其演出實況。清人高士奇稱過錦「迨入我朝遂廢不治」[1],程恩澤詩云:「水嬉過錦未親見,剩有輕羅拜恩久」,[2]翁心存詩曰:「過錦排當想像中,勝朝曾此建離宮」[3],這些均表明過錦戲是明朝特有的名稱,後人對過錦戲的認識唯有憑懸想而已。
《明代宮廷戲曲編年史》
就演出形式、表演形態而言,過錦戲繼承了宋金雜劇滑稽逗樂的傳統,並稍加改變,規模上略有擴大。它以其命名之新奇引起了戲曲研究者的興趣,學者對其加以考察的主要依據是明清時期的相關文獻記載。
從清人提及過錦戲的文獻來看,乾隆時期之後的學人對它已非常陌生,並由此而產生了一些曲解,誤導了後人。胡忌的《宋金雜劇考》是對過錦戲的演出形態、體制等做較早、較深入研究的成果,其他學者的相關探討亦對理解過錦戲有所助益。
然而,筆者仔細梳理相關研究成果後發現,過錦戲研究有三個方面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辨正:一是清代以來關於過錦戲的種屬所存在的一些誤解;二是關於過錦戲的形態的一些意見分歧;三是關於過錦戲的演出規模的不同見解。這些均需基於相關文獻載錄一一予以分析辨正。
以下即針對這三個方面展開討論,力爭對過錦戲研究有所推進。
一、過錦戲的種屬
根據明代宮詞等史料文獻的記載,過錦戲在明朝宮廷內經常上演,娛樂性非常突出,十分受歡迎。秦征蘭詩曰:「過錦闌珊日影移,蛾眉遞進紫金卮。天堆六店高呼唱,瘸子當場謝票兒」[4]。饒智元詩云:「水嬉過錦絕歡娛,內殿宣傳罪己書。憂及萬方多涕淚,比來長御省愆居」[5]。明清之際的著名詩人吳偉業、屈大均等亦曾吟詠及此。
清代再也沒有宮廷演出過錦戲的記載,隨著時間的推移,清人對它的認識日趨模糊。很多人僅僅知道它是明朝宮廷戲的一種,至於具體面貌則不得而知了。例如,晚清俞樾在閱讀吳偉業《琵琶行》中「先皇駕幸玉熙宮,鳳紙僉名喚樂工。苑內水嬉金傀儡,殿頭過錦玉玲瓏」等詩句時,對過錦究竟屬於何種戲曲已不甚明了。當後來看到劉若愚《酌中志》對過錦戲的記載,才對此有了一定了解[6]。
《清代宮廷承應戲及其形態研究》
以俞樾之博聞強識尚且如此,其他人產生誤解亦不足為奇。整體來看,清人對過錦戲主要存在兩種誤解,並均對後來學界相關研究產生了不小的誤導。下面分別予以梳理、辨明。
一種意見認為過錦戲是影戲,以清朝乾隆時期的吳長元為代表,他說:「明鐘鼓司,掌印太監一員,僉書司房學藝官無定員,掌管出朝鐘鼓及內樂、傳奇、過錦、打稻諸雜戲。按:過錦,今之影戲也。」[7]
按語之前的文獻引述並無問題,但是吳長元所加按語「過錦,今之影戲也」並無根據,不免有臆測之嫌。揆其致誤之由,蓋因未能細讀所引文獻的上下文所致。
吳氏引文源自於敏中《日下舊聞考》:「增鐘鼓司,掌印太監一員,僉書司房學藝官無定員,掌管出朝鐘鼓及內樂、傳奇、過錦、打稻諸雜戲。《明史職官志》。」
于敏中在此註明其文獻源於《明史職官志》,其中並無過錦戲即影戲之說明,不知吳長元何所據而云然。《日下舊聞考》此條記錄之前是:
《日下舊聞考》
原鐘鼓司陳御前雜戲,削木為傀儡,高二尺余,肖蠻王軍士男女之像,有臀無足,下安卯栒,用竹板承之,注水方木池,以錫為箱,支以木凳,用紗圍其下,取魚蝦萍藻踐(筆者按: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踐」當為「躍」之誤。)浮水面,中官隱紗圍中,將人物用竹片托浮水上,謂之水嬉。其以雜劇故事及痴兒騃女市井駔儈之狀,約有百回,每四(筆者按: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當為「回」之誤。)十餘人,各以兩旗引之登場,謂之過錦。皆鐘鼓司承應。《蕪史》。[8]
于敏中根據劉若愚《蕪史》記載了水嬉和過錦兩種宮廷雜戲,其中水嬉是以木材削製成傀儡人物,由太監隱藏於紗圍之後,「將人物用竹片托浮水上」來表演的。
而過錦則是「以雜劇故事及痴兒騃女、市井駔儈之狀,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各以兩旗引之登場」加以表演的,兩者雖然均屬「鐘鼓司承應」,卻是完全不同的藝術形式,並且兩者皆與影戲無關。
影戲是用紙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燈光映於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戲劇。據宋代《都城紀勝》「影戲」條記載:「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彩色裝皮為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姦邪者與之丑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戲也。」[9]
影戲表演是藝人通過操縱紙影、皮影或手影形成的形象來完成的,而過錦戲則是演員真人登場扮演故事,兩者依託的物質媒介和表演形式完全不同。由是觀之,影戲不是過錦戲。雖然水嬉和影戲均是通過人的操控進行表演,但是從製作材質和表演形式來看,水嬉是水傀儡,屬於傀儡戲之一種,必須在水上表演,與影戲也無直接關係。
清人鐵保《玉熙宮詞》:「嘈嘈雜劇名過錦,綽約輕旗對對引。雅俗全登傀儡場,君王何處窺民隱。水嬉之制制更神,雕刻木偶投水濱。機緘運制百靈走,出沒邋遢如生人。」[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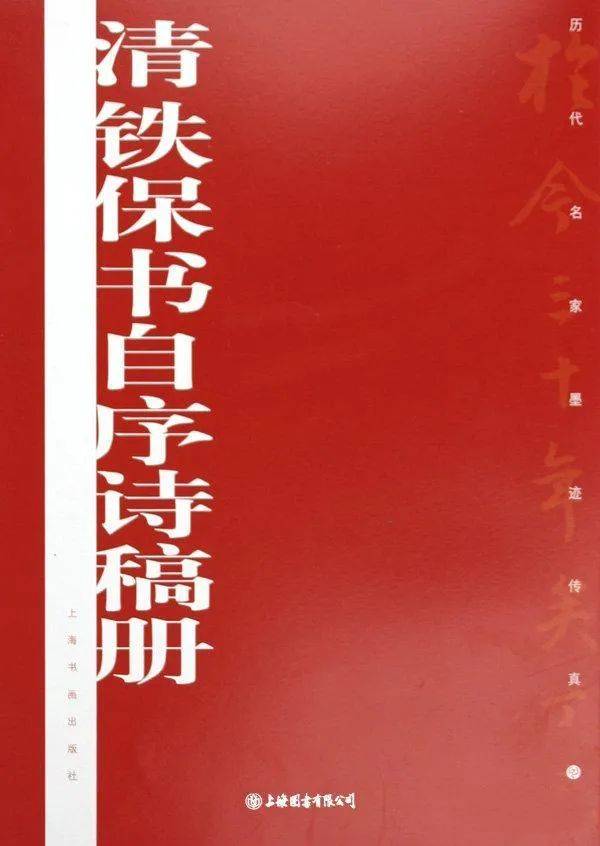 《清鐵保書自序詩稿冊》
《清鐵保書自序詩稿冊》
前四句詠的是過錦戲,後四句寫的是水嬉。「嘈嘈雜劇名過錦」,指過錦是雜劇的一種,表演起來非常熱鬧。「水嬉之制制更神,雕刻木偶投水濱」,指水嬉是在水裡表演的木偶戲,即水傀儡,「機緘運制百靈走,出沒邋遢如生人」是說水嬉的演出像真人表演一樣栩栩如生。
今人湯際亨根據吳長元之說得出結論:「可知明朝影戲已見盛行,宮廷內且有專司之官」,此說前提有誤,斷語自然難以信從。
另外,至今未見明朝宮廷有專司影戲之官的記載。針對此說,江玉祥徵引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三「禁中演戲」、劉若愚《明宮史》木集「鐘鼓司」、秦征蘭《天啟宮詞一百首》、蔣之翹《天啟宮詞一百三十六首》、程嗣章《明宮詞一百首》等文獻的相關記載,較為細緻地考辨了過錦戲並非影戲[11]。其說甚為允當。
此外,郝可軒徵引吳長元按語稱「皮影戲在明朝時名『過錦』」[12],學者型作家高陽以為「皮影稱為過錦」[13],想必也是受吳長元之說的影響。
另一種意見以為過錦戲是木偶戲,以晚清的震鈞為代表。他說:「明代宮中有過錦之戲。其制以木人浮於水上,旁人代為歌詞,此疑即今宮戲之濫觴。但今不用水,以人舉而歌詞。俗稱托吼,實即托偶之訛。《宸垣識略》謂:『過錦即影戲』。失之」[14]。
《宸垣識略》
近人夏仁虎《傀儡戲》詩:「日長無事慰慈懷,內里傳呼過錦來。春耦齋中風景好,玲瓏特構小宮台。」其自注云:「傀儡戲俗呼托吼,即明代之過錦。清曰宮戲,以娛太后、宮眷。其演唱技藝皆由內監供役,故亦稱宮戲,於春耦齋構宮台。自孝欽後,外優入演,此戲遂廢」[15]。章乃煒等《清宮述聞續編》採納其說[16]。
震鈞、夏仁虎均認為過錦即托吼,後者進一步坐實過錦為清代宮戲,考慮到夏仁虎稍晚於震鈞,受震鈞影響的可能性大一點。
托偶是木偶戲的一種,張次溪云:「托偶戲之偶字,北京讀偶如吼。此種戲約分三種,一種名傀儡,一名提線,一即此種,名曰托吼」。
托偶的表演與形制是「以其真人皆須隱藏帳內,不得窺視外邊,而觀者亦只見偶人,不見真人,極便於宮中觀看,故又名大台宮戲。其舞法則上搭一戲樓,下截四周,圍以布帳,人在帳中,托偶人舞之,故名托偶。每一真人,舞一偶人,一切喜怒哀樂,皆可形容出來。」[17]
也就是說,木偶戲是藏在幕後的每個真人通過操控一個偶人來表演的,觀眾是完全看不見操縱者的,而過錦則是演員真人登場扮演,插科打諢,觀眾欣賞的是真人的表演。兩者依託的物質媒介和表演形式不同,顯系不同的表演伎藝。由此可知,震鈞指出吳長元之失是歪打正著,其「過錦即托偶」之說也是錯誤的。
根據前文所引《琵琶行》《日下舊聞考》《玉熙宮詞》的片段可知,震鈞顯然是混淆了過錦與水嬉兩種雜戲。
《明宮史》
明人劉若愚詳細記錄了水嬉的製作與表演體制:
又,水傀儡戲,其制用輕木雕成海外四夷蠻王及仙聖、將軍、士卒之像,男女不一,約高二尺余,止有臀以上,無腿足,五色油漆,彩畫如生。每人之下,平底安一榫卯,用長三寸許竹板承之,用長丈余、闊數尺、進深二尺余方木池一個,錫鑲不漏,添水七分滿,下用凳支起,又用紗圍屏隔之,經手動機之人,皆在圍屏之內,自屏下游移動轉。水內用活魚、蝦、蟹、螺、蛙、鰍、鱔、萍、藻之類浮水上。聖駕升殿,座向南。則鐘鼓司官在圍屏之內,將節次人物,各以竹片托浮水上,游斗玩耍,鐘鼓喧鬨。另有一人,執鑼在旁宣白題目,替傀儡登答、贊導喝采。或英國公三敗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七縱,或三寶太監下西洋、八仙過海、孫行者大鬧龍宮之類。惟暑天白晝作之,猶耍把戲耳[18]。
由上引文獻可知,水嬉(即水傀儡戲)表演的題材比較豐富,其中軍事戰爭題材有英國公三敗黎王、孔明七擒七縱孟獲等故事,神怪題材有三寶太監下西洋、八仙過海、孫行者大鬧龍宮等故事,表演之時「鐘鼓喧鬨」,非常熱鬧。
其表演形式才是震鈞所謂「其制以木人浮於水上」;「另有一人,執鑼在旁宣白題目,替傀儡登答、贊導喝采」即震鈞所謂「旁人代為歌詞」。水嬉是通過人操控木偶浮在水上表演,而托偶是通過人托舉木偶表演,它們之間的區別才是「但今不用水,以人舉而歌詞」,顯而易見,過錦並非托偶。
《明代宮廷戲劇史》
震鈞此說對後來的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李家瑞徵引震鈞之說以證明懸絲傀儡與水傀儡在明代都沒有消失的觀點,[19]佟晶心在論證傀儡戲時亦引證震鈞之說[20]。孫作雲稱:「按過錦之戲,其說非一,果如《天咫偶聞》所說,『其制以木人浮於水上,旁人代為歌詞』,當即水傀儡無疑。」[21]
他十分清楚關於過錦戲「其說非一」,卻在諸種說法中誤信了震鈞的意見。雷齊明也根據《天咫偶聞》認為過錦戲與木偶戲有類似之處[22]。
其他文史研究者亦多受震鈞誤導,如王娟以為:「水傀儡:古稱水飾、水戲、水嬉……後來進入宮廷,被稱為宮戲與過錦戲」[23]。周耀明說:「水傀儡戲又叫『過錦戲』」[24]。吳剛、馮爾康等也或多或少受到此說的影響[2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學者中還有將過錦、水嬉混淆的,有的以為有所謂「過錦水嬉」之戲,有的認為有所謂「水嬉過錦」之戲。前者如傅起鳳等認為:「過錦戲除上述形式外,有時也在水中表演。
據《續文獻通考》載,愍帝朱由檢(1628—1643在位)曾宴玉熙宮,作過錦水嬉之戲。曹靜照宮詞云:『口敕傳宣幸玉熙,樂工先侯九龍池;妝成傀儡新番戲,盡日開簾看水嬉』。文獻還記載,朱由檢曾數次觀看這種過錦戲」[26]。
然而,《續文獻通考》註明是根據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作如上記載的,並未將兩者混淆,而《金鰲退食筆記》對過錦、水嬉是分別介紹的,兩者界限分明[27]。
《金鰲退食筆記》
另外,曹靜照宮詞只描述了水嬉的表演,並未提到過錦。清人史夢蘭《全史宮詞》的簡釋者云:「《金鰲退食筆記》載,崇禎帝每宴玉熙宮,作『過錦水嬉』之戲。」[28]
後者如荊清珍認為過錦之戲又叫水嬉過錦[29],其依據是:「《蕪史》御前雜戲有水嬉過錦,皆鍾鼔司承應」[30]。
此引文前的條目雖為「水嬉過錦」,但姚之駰顯然明白水嬉、過錦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否則就不會說「皆鍾鼔司承應」。「皆」,俱詞也,針對的對象肯定不止一個。如果姚之駰認為水嬉過錦是一種藝術形式,絕不會用「皆」字。
高志忠認為:「過錦戲中有一種叫做『水嬉過錦』的值得一提。《柳亭詩話》卷18 『過錦』條云:「何次張宮詞『昆明池水漾春流,夾岸宮花繞御舟,歌舞三千呈過錦,琵琶一曲唱梁州。』蓋在水上進行演出的過錦之戲為『水嬉過錦』」[31]。
《明代宮廷戲曲與外交研究》
然詳考其所引文獻,僅提及過錦而未涉水嬉。所謂「歌舞三千呈過錦」當指在眾多歌舞表演中穿插了過錦戲的表演。「蓋在水上進行演出的過錦之戲為『水嬉過錦』」之說不知何據?以上諸位之所以產生誤讀,可能是因為水嬉、過錦在文獻中經常被同時提及,將兩者連讀而未參考其它相關文獻所致。
二、過錦戲的形態
迄今為止,學術界關於過錦戲的形態有三種主要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過錦戲與雜扮相似,以王國維為代表。作為近代最早關注過錦戲的學者,他指出:「則元時戲劇,亦與百戲合演矣。明代亦然。呂毖《明宮史》(木集)謂:『鐘鼓司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說笑話之類,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裝扮者,備極世間騙局俗態,並閨閫拙婦騃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雜耍把戲等項。』則與宋之雜扮略同。」[32]
這一觀點得到多數學者的贊同。如周貽白據《酌中志》記載認為:「『過錦戲』雖有戲劇的形式,而無戲劇的排場,僅為活動地隨上隨下。頗與宋代所謂『雜扮』相仿,或即由其轉變而別立新名,亦未可知」[33]。
董每戡以為:「照沈氏所說,明代的『過錦戲』只名稱新鮮,實際內容跟笑樂院本是差不多的,仍然是唐代參軍戲,兩宋雜劇,金元院本的繼承,甚至沒有什麼發展和提高,只不過取了這麼個漂亮名兒罷了……可是依書本上的一些零星記載看來,它大致是放在正戲完後『打散』用,有點兒象兩宋雜劇的最後一段『雜扮』」[34]。
趙景深等認為,過錦戲是宋雜劇中雜扮的延續[35]。上述諸家注意到過錦與雜扮的相似處,但用「略同」「相仿」「有點兒象」等詞語表述,未遽下斷語,態度嚴謹。此說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
《趙景深文存》
過錦戲與雜扮確有不少相似之處,如兩者均具有一定的敘事性和諧謔性,結構都比較簡短,場面皆十分熱鬧。然而它們又有一定的差異,不能等量齊觀,其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表演的次序(位置)不同。雜扮在正雜劇的結尾表演,也稱打散。據《夢粱錄》記載:「又有『雜扮』,或曰『雜班』,又名『紐元子』,又謂之『拔和』,即雜劇之後散段也。」[36]
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品題》云:「蓋扮雜劇至末折尾聲止,正劇雖完,而當場之藝猶未結束,觀者猶未去也。至打散訖而承應之事始畢。打散乃正劇之後散段,其事實為送正劇而作者」[37]。過錦戲則不然,其表演位置較為靈活,不拘於正戲之末,既可以在正戲之前搬演,又可以在正戲之中進行,亦可以在正戲之後演出(說詳後)。
二、表現的題材不同。雜扮裝扮的人物是鄉村老叟,地域範圍局限于山東、河北,題材是嘲謔這類人物的孤陋寡聞,即所謂「頃在汴京時,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為山東、河北村叟以資笑端」。
而過錦裝扮的人物則是市井人物,地域範圍沒有限制,題材也相對廣泛,包括「世間騙局俗態,並閨閫拙婦騃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等內容,並不專以戲弄莊稼人為能事。因此,儘管過錦戲與雜扮很相似,但不能等同。
《崑劇演出史稿》
第二種觀點以為過錦戲包括說笑話、滑稽戲和北雜劇及雜耍把戲三種形式,以陸萼庭為代表。
他說:「『過錦』何解?自來眾說紛紜,或謂即『今之影戲』,或謂系宋雜劇之別立新名。細味引文表述層次,所謂過錦其實含有『多樣』的意思,並非單一的戲劇形式名稱。其事甚古,劉若愚雖經目睹,惜不明淵源,以致分厘不清,敘述失序。『每回』指每檔節目,『百回』極言其多而已。這裡至少包含三種形式:一說笑話、滑稽戲,漸伴有樂聲歌呼動作以渲染氣氛,應該與『御前插科打諢』是一物,是宋元雜劇原本的遺制,有傳統段子,更多是新編的;二北雜劇,新舊兼有;三雜耍把戲,所演節目今知有狻猊舞(獅子舞)、擲索、壘七桌、齒跳板、蹬技等。我認為明代的宮戲實際囊括了宋代的『雜伎藝』,名副其實的沿『金元之舊』」[38]。
陸先生敏銳地指出過錦戲並非單一的戲劇形式名稱,具有多樣的意思即雜的特徵,過錦戲確實包括不止一種體制。
但是以為北雜劇也是過錦戲之一種則值得商榷。根據前引《酌中志》《明宮史》對過錦戲的記載,過錦戲的題材以「世間騙局俗態,並閨閫拙婦騃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為主,而北雜劇的題材包羅萬象,十分廣泛,明顯不同於過錦戲。
過錦戲的藝術特徵是「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即以詼諧熱鬧的插科打諢收場,而北雜劇則或悲、或喜、或悲喜交乘,插科打諢只是其中的調料而已,並不構成戲劇的主體,絕大多數也並非作為雜劇結局之用。考引文所載 「雜劇」故事當指沿金元之舊的院本,與以正旦、正末為主角演唱四大套曲的偏重敘事的北雜劇是不同的。因此,北雜劇不屬於過錦戲的範疇。
第三種觀點認為過錦戲就是院本,以胡忌為代表。
《宋金雜劇考》(訂補本)
他認為:「在他處未見『過錦』資料前,據前引四例,我們不妨說:明代宮中所演出的院本尚有『過錦』的別稱。而且就這些記載看來,過錦應屬於優諫類的滑稽戲而不是歌舞類戲。自南戲、北曲雜劇相繼盛行以來,院本即相對屬於小戲之流,以《金瓶梅詞話》和《客座贅語》證之,它仍然有夾雜在雜耍、隊舞、伎藝之間演出的。『過錦』的『過』,似有夾帶的含義;『錦』字可能約如現今習慣語『什錦糖』『十樣錦』之類(南曲集曲中有『五樣錦』也正同此義),有零碎、好玩的意義」[39]。
說過錦是院本的別稱,顯然以為過錦戲就是院本。廖奔也認為:「很明顯,過錦戲就是院本,其表演要求『濃淡相間』,不是令人想起唐代參軍戲的『鹹淡最妙』」[40]。
此說有一定道理,似尚可補充一則資料以證之。《明史》記載:「阿丑,憲宗時小中官也,善詼諧。帝嘗宮中內宴,鐘鼓司以院本承應,為過錦戲,丑毎雜諸伶中作俳語,間入時事,帝輒喜,或時作問之以為娛,而丑顧心疾汪直弗置也」[41]。
揆「鐘鼓司以院本承應,為過錦戲」之意,則院本顯然屬於過錦戲的表演形式之一。
明人沈德符云:「有所謂過錦之戲,聞之中官,必須濃淡相間、雅俗並呈,全在結局有趣,如人說笑話,只要末語令人解頤,蓋即教坊所稱耍樂院本意也。」[42]此處明確交代其關於過錦的信息是「聞之中官(宦官)」,說明沈德符並未親眼看過過錦戲的表演。
《萬曆野獲編》
鑒於他與劉若愚年代相近,生活或有交集,其所謂「聞之中官」的「中官」很可能即指劉若愚。即便並非如此,也不妨礙親眼看了過錦戲表演的劉若愚所記更加可信,其《酌中志》記載過錦戲時明確指出:「雜耍把戲等項,皆可承應。」[43]意即雜耍、把戲亦是過錦戲的表演內容。
雜耍把戲是雜耍與把戲的合稱,兩者往往有交叉。明人劉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二稱:「雜耍則隊舞、細舞、筒子、筋斗、蹬壇、蹬梯」[44]。清人李斗記載,雜耍之技包括竿戲、飲劍、壁上取火、席上反燈、走索、弄刀、舞盤、風車、簸米、躧高蹺、撮戲法、飛水、摘豆、大變金錢、仙人吹笙等[45]。除了撮戲法、飛水、摘豆、大變金錢屬於魔術,其餘均屬於雜技。把戲亦兼指雜技和魔術。
明傳奇《蕉帕記》第三齣「下湖」形象地描述了把戲表演:「﹝中凈﹞列位相公在上,看小的做一會把戲討賞。﹝凈﹞妙妙!你有什麼本事?﹝中凈帶做介﹞﹝北寄生草﹞﹝中凈﹞賣解單身控。﹝生﹞會走馬的了。﹝中凈﹞千鈞只手拿。﹝小生﹞是有手力的了。﹝中凈﹞吞刀任把青鋒插。﹝凈﹞妙!怕人。﹝中凈﹞拋丸盡著流星打。﹝凈﹞看腦袋。﹝中凈﹞飛槍直向雲端下。﹝凈﹞罷了,壞了眼。﹝中凈﹞有時百尺上竿頭,撒身慣使飛鷹怕。﹝凈﹞掉下來跌折了腰,妙妙!好手段!」[46]此處把戲指雜技。明人謝肇浙《五雜俎》卷六所記幻戲既有魔術亦有雜技[47]。
李漁曰:「如做把戲者,暗藏一物於盆盎衣袖之中,做定而令人射覆,此正做定之際眾人射覆之時也」[48]。這裡把戲指魔術。章炳麟《新方言·釋言第二》云:「其謂幻戲曰把戲,或曰花把戲,把即葩字,花即蒍字」[49]。則幻戲又名把戲,幻戲和雜耍有交叉重合之處,故可統稱為雜耍把戲。
由此可見,過錦戲不是單一的品種,而是混雜的形態,它不僅包括以滑稽調笑為目的的院本,而且還包含非常精彩聳人視聽的魔術、雜技等表演,娛樂性突出,稱之「絕歡娛」名副其實,屬於典型的「雜」戲。
《戲曲劇種演進史考述》
三、過錦戲的演出規模
學術界對過錦戲的演出規模有兩種不同看法:一種意見以為過錦戲屬於大戲之範疇,演出規模較大;另一種意見以為過錦戲屬於小戲之範疇,演出規模較小。
過錦戲究竟屬於大戲還是小戲,牽涉到學者對大戲、小戲的認知,而以往學者談論大戲、小戲時,指稱的往往是不同的戲曲現象,難免言人人殊。
對此,李玫、曾永義作了系統深入的辨析。李玫指出:「所謂小戲,在明清曲家對明清傳奇的評論中,指傳奇中某些凈、丑、雜等次要角色出場的場次,或指在特定場合表演生動的配角;在清代地方戲的語境中,除了指小劇種,通常指一類表現普通人生活、且風格諧謔的短劇。這些短劇,既包括表現手法簡單的民間戲,也包括那些從晚明至清代一直流傳的成熟的劇作。所謂『大戲』,除了指整本戲和連台本戲以及大劇種外,還指一類吉祥戲」[50]。
《中國民間小戲史論》
曾永義著眼於戲曲的發展史,認為:「所謂『小戲』,就是演員少至一個或三兩個,情節極為簡單,藝術形式尚未脫離鄉土歌舞的戲曲之總稱……而其『本事』不過是極簡單的鄉土瑣事,用以傳達鄉土情懷,往往出以滑稽笑鬧,保持唐代『踏謠娘』和宋金雜劇『雜扮』的傳統。所謂『大戲』即對『小戲』而言,也就是演員足以充任各門腳色扮飾各種人物,情節複雜曲折足以反映社會人生,藝術形式已屬綜合完整的戲曲之總稱」[51]。
綜合上述觀點可以看出,小戲的特點是形制短小、風格諧謔、情節簡單;大戲的特點是形制長大、風格多樣、情節複雜。下面以此為標準考量以上兩種觀點。
先看第一種意見,翦伯贊在論明代戲劇時說:「在結構方面,則由『四折劇』發展而為百回以上的長篇巨製。劉若愚《酌中志》謂:『(明代)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由此可知明代戲劇,無論在劇曲本身音樂配合方面,都已經超越了金元時代的水準」[52]。以過錦戲證明代戲劇的長篇巨製,應是將其作大戲看待。
周妙中認為:「太監學的宮戲,有《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曲選所收的曲子,也有所謂『過錦之戲』,以及雜耍等等的節目。只是玉熙宮檔案早已散失,演出情況如何,無從作詳細的了解,只可以從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得知一斑……看來所演的內容,與民間並沒有太大差異,只是規模龐大得多。長達百回左右的『過錦之戲』很可能就是乾隆年間一些宮廷歷史大戲的藍本」[53]。
王正來認為清宮大戲《勸善金科》《異平寶筏》的結構是一段一段的,乃受明代宮廷過錦的影響,可以稱為清代的過錦戲[54]。李真瑜論及過錦戲時據《酌中志》所載認為:「戲長至百回,演出的內容很多,演員陣容龐大,所以場面也很宏大」[55]。
《酌中志》
持這種看法的學者均著眼于于過錦戲約有「百回」的記載,以為它既然有百回,當然是規模龐大的長篇巨製,屬於大戲之屬。以「回」稱戲早有先例,宋人孟元老云:「般雜劇:杖頭傀儡任小三,毎日五更頭回小雜劇,差晚看不及矣」[56]。元人楊立齋《哨遍》套曲云:「更那碗清茶罷,聽俺幾回兒把戲也不村呵」[57]。元人高安道散套《哨遍·嗓淡行院》云:「打散的隊子排。待將回數收」[58]。
此處回均可指可斷可連的獨立場次段落。據劉若愚的記載,過錦戲的形制是短小的,風格是諧謔的、情節是簡單的,當屬小戲,所謂百回是極言過錦橋段之多,而非像大戲那樣的連貫長篇、情節複雜。
再看第二種意見,認為過錦戲類似於雜扮和認為過錦戲是院本的學者顯然認同過錦戲屬於小戲的觀點,前文已述茲不贅引。
其他如薛寶琨以為:「明代有所謂『過錦戲』,繼承唐參軍、宋滑稽遺風穿插於大戲之中,以『濃淡相間、雅俗並陳』,『諧謔雜發,令人解頤』取勝。敷演其中段落也絕似現代相聲。」[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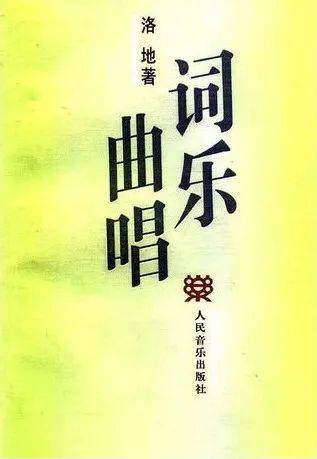 《詞曲樂唱》
《詞曲樂唱》
洛地稱:「所謂過錦,大致便是若干『錦』組練成隊串連(『過』)而演吧。包括雜耍在內的各式戲耍的『耍樂院本』串演,稱『過錦之戲』……過錦戲(弄),將若干戲弄段子串演:以(任何)一個由頭,造成或提供一個過程或背景,便可能收納若干相近的戲弄段子,組練串連而演。其收納的戲弄段子,相互間是平列的,段數可多可少;其中每個段子又仍保持其為段的狀態,可長可短」[60]。
曾永義以為:「像這種一折或一出式的『小戲』,明代有所謂『過錦戲』……可見過錦戲就是『笑樂院本』(沈氏之語),『約有百回』,則是一個大型的小戲群,內容包羅萬象,而其中既有『世間市井俗態』及『拙婦騃男』,則應當也包含類似『踏謠娘』或『紐元子』那樣鄉土小戲式的演出」[61]
李玫說:「從此段話看,崇禎朝,在李自成沒有打到河南以前皇宮裡一直演過錦戲。……這既有宋代雜劇的遺韻,又與明清的小戲作品在審美效果上異曲同工[62]。上述學者未局限於百回之說,而是從形制、風格、情節的特點出發,認為過錦戲屬於小戲或小戲群,這種看法是相對準確的。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因未見學者對此分歧專門論證辨析,故立足另兩則材料對此問題進一步申說。過錦戲僅限於在明代宮廷表演,親眼目睹其表演者甚少,相關文獻記載只有劉若愚是據親眼所見載錄,其他記載基本輾轉源於《酌中志》。據筆者所知,似乎只有兩個例外,一個是吳偉業,一個是吳棠楨,他們關於過錦戲的看法源於不同的信息渠道,分別來自於明代宮廷中的其他兩個宦官,既可以印證劉若愚之說,又對過錦戲演出規模的辨析大有助益,因而顯得彌足珍貴。
吳偉業《琵琶行》序云:「坐客有舊中常侍姚公,避地流落江南,因言先帝在玉熙宮中,梨園子弟奏水嬉、過錦諸戲,內才人於暖閣齎鏤金曲柄琵琶,彈清商雜調。自河南寇亂,天顏常慘然不悅,無復有此樂矣。相與哽咽者久之,於是作長句紀其事,凡六百二言,仍命之曰琵琶行」[63]。
吳梅村明確指出其關於過錦的認知源自明朝宮廷中親眼看過過錦戲表演的宦官姚公(姚在洲),信息源是可靠的。吳偉業既是著名詩人也是戲曲家,曾創作過傳奇《秣陵春》和雜劇《臨春閣》《通天台》等,對戲曲非常精通。其《琵琶行》中詩句「苑內水嬉金傀儡,殿頭過錦玉玲瓏」直稱「過錦戲」「玲瓏」,玲瓏乃精巧、靈活之意。
《吳梅村詩集箋注》
正因為過錦戲內容簡單、體制短小,屬於精巧的雜戲,稱其「玲瓏」十分貼切,如此則過錦戲當屬小戲。若過錦戲是百回大戲,吳偉業以「玲瓏」評之顯屬不倫。再看另一個證據。清人宋長白記載:
何次張《宮詞》:「昆明池水漾春流,夾岸宮花繞御舟。歌舞三千呈過錦,琵琶一曲唱梁州。」吳雪舫云:「宮中以『饒戲』為過錦,得之黃開平座上高內相所言」。宮詞故實甚多,然歷朝各有所尚,五百揀花,三千掃雪,番經奏籙之類。詩人尚未摭拾也[64]。
吳雪舫即吳棠楨,清初戲曲家,《今樂考證》著錄其《赤豆軍》《美人丹》雜劇兩種。金烺《漢宮春·讀吳雪舫新制四種傳奇》:「小立亭台,見一雙麼鳳,競啄丹蕉。愛看吳郎樂府,直壓吳騷。移宮換羽,卻新翻、字句推敲。雄壯處、將軍鐵板,溫柔二八妖嬈。 如許錦繡心胸,想琅玕劈紙,翡翠妝毫。自有寶簪低畫,紅豆輕拋。當筵奏伎,聽鶯喉、響徹檀槽。若更付、雪兒唱去,座中怕不魂銷」[65]。
據此則吳氏至少有四種傳奇問世。宋長白明確指出吳雪舫以「饒戲」為過錦的看法來自明朝宦官高內相,當較為可信。既然明朝宮中以饒戲為過錦,則兩者的形態應該是相似的,若饒戲是小戲則過錦戲亦為小戲。
《詩詞曲語辭彙釋》
「饒戲」即「饒頭戲」。張相說:「『饒,猶添也;連也;不足而求增益也。即今所云討饒頭之饒……斷送,即贈品之意;所謂饒個某某項者,即饒頭戲之意。」[66]。
姜書閣稱:「饒就是添,饒戲就是正戲之外,再添演別的節目,那外添的部分便叫饒頭。饒頭與正項可以是同品種,也可以不是同品種。如買一棵大白菜,又搭一棵蔥,即非同種;買一斤橘子,外搭一個小的,則屬同種,都叫做饒頭。所以在正戲之外,不一定必須加其他說唱、雜技才名饒戲,另演一段小戲也是饒戲。[67]
由此觀之,饒戲是與正戲相對而言的,是正戲之外額外添加、贈送的小戲。饒戲表演的位置有三種,一種是在正戲之前,一種是在正戲之中,還有一種是在正戲之後。
饒戲在正戲之前表演的如《張協狀元》正戲之前「饒個攛掇末泥色,饒個踏場,……饒個《燭影搖紅》斷送」是如此,《風月紫雲庭》劇:『我唱的是《三國志》,先饒十大曲。』亦如此。
饒戲在正戲之中表演的如《長生殿》演出本,洪昇在《長坐殿例言》中指出:「 今《長生殿》行世,伶人苦於繁長難演,竟為傖輩妄加節改,關目都廢。吳子憤效《墨憨十四種》,更定二十八折,而以虢國、梅妃別為饒戲兩劇,確當不易。且全本得其論文,發予意所涵蘊者實多,分兩日演唱殊快。取簡便,當覓吳本教習,勿為傖誤可耳!」[68]
饒戲表演在正戲之後的情況較多,如明代小說《療妒緣》中許雄等先點了一本《滿床笏》,「未幾正本已完,來點饒戲。許雄說一些不知,推與秦仲點。秦仲取戲目一看,說:『索性做學出來的罷。』就點了《獅吼》一回。又將戲目送入簾內,尤氏就點了《萬事足》擲棋盤、《療妒羹》上團圓」[69]。
《療妒緣》
此處,《滿床笏》是正戲(正本),《獅吼》《萬事足》《療妒羹》中的折子戲均是饒戲。在李漁所作小說《譚楚王戲裡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中,劉絳仙「更有一種不羈之才,到那正戲做完之後,忽然填起花面來,不是做凈,就是做丑。那些插科打諢的話,都是簇新造出來的,句句鑽心,言言入骨,使人看了分外銷魂,沒有一個男人,不想與他相處」[70]。
這裡正戲之後的凈丑戲,就是饒戲。明末張岱接待魯王時,演《賣油郎》傳奇,劇完,饒戲十餘出,起駕轉席[71]。饒戲亦名「找戲」,如明代《檮杌閒評》第四十三回「到了城外,戲子已到,正戲完了,又點找戲。」[72]以此觀之,從體制、結構、篇幅、表現內容等來看,饒戲屬於小戲之範疇。宦官高內相說明宮中以「饒戲」為過錦,則過錦亦屬小戲。
綜上所述,過錦戲是明代一種宮廷雜戲的專稱,表演以滑稽逗樂、精彩熱鬧為目的,在繼承宋金雜劇的基礎上有所發展,體現在表演人數增加到十餘人,品種更加豐富,有約百回的獨立成章的段子,可分可合。
《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王昊著,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2月版。
它由真人扮飾表演,既不是影戲,也不是木偶戲,更沒有過錦水嬉或水嬉過錦的品類。其形態是混雜的,不同於單一的雜扮、北雜劇、院本,主要包含了院本和雜耍把戲兩大類。就演出規模而言,其形制短小、風格諧謔、情節簡單,個體上屬於小戲,不同段子合演則屬於小戲群。
注釋:
[1]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卷下「玉熙宮」條(與劉若愚《明宮史》合刊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頁。
[2]程恩澤《厲宗伯競渡圖為滇生同直題》,《程侍郎遺集》卷四,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冊,第84頁。
[3]翁心存《陽澤門內小馬圈是前明玉熙宮遺址》,《知止齋詩集》卷五,清光緒三年(1877)常熟毛文彬刻本,第21頁。
[4]秦征蘭《天啟宮詞》,朱權等《明宮詞》,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頁。
[5]饒智元《明宮雜詠》,《明宮詞》,第304頁。
[6]參見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八「過錦」條,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冊,第396頁。
[7]吳長元《宸垣識略》卷三「皇城一」,北京出版社1964年版,第44頁。
[8]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三九「皇城」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冊,第617頁。
[9]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俞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唐宋元編)》,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116頁。
[10]鐵保《梅庵詩鈔》卷二,《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476冊,第305頁。
[11]參見江玉祥《中國影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5頁。按:本文與江先生徵引的文獻與考辨的角度有所差異。
[12]郝可軒《漫談皮影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08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頁。
[13]高陽《明武宗正德艷聞秘事》,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頁。
[14]震鈞《天咫偶聞》卷七「外城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頁。
[15]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光緒宣統朝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冊,第14474頁。
[16]參見章乃煒等編《清宮述聞續編》(與章乃煒等編《清宮述聞初編》合刊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775頁。
[17]張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橋》,中國曲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頁。
[18]劉若愚《明宮史》木集「鐘鼓司」條,(與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合刊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頁。
[19]李家瑞《傀儡戲小史》,《文學季刊》第1卷第4期,1934年。
[20]佟晶心《中國傀儡劇考》,《劇學月刊》第3卷第10期,1934年。
[21]孫作雲《孫作雲文集•美術考古與民俗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頁。
[22]雷齊明《明清劇種源流談》,《北京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按:雷先生引震鈞《天咫偶聞》誤作李人《天咫偶窗》,其後又雲「若據《勝朝彤史拾遺記》的記載,過錦戲『取時事諧謔,以備規諷』又有些類似唐代的參軍戲」。可見,對過錦戲究為何物,頗有猶疑。
[23]王娟《民俗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頁。
[24]周耀明《漢族風俗史》,學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頁。
[25]參見吳剛《中國古代的城市生活》,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88頁;馮爾康《古人社會生活瑣談》,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頁。
[26]傅起鳳、傅騰龍《中國雜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251頁
[27]《金鰲退食筆記》,第145頁。
[28]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下,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年版,第725頁。
[29]荊清珍《明廷禁戲與戲曲芻議》,《長江學術》2008年第3期。
[30]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二七「水嬉過錦」條,《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884冊,第437頁。
[31]高志忠《明代宦官演戲種類考略》,《文化遺產》2011年第3期。
[32]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27頁。按:王國維先生意識到過錦戲與雜扮的不同,所以他接著又說:「至雜耍把戲,則又兼及百戲,雖在今日,猶與戲劇未嘗全無關係也」。
[33]周貽白《中國戲劇史》,中華書局1953年版,第470頁。
[34]董每戡《「滑稽戲」漫談》,《戲劇藝術》1980年第2期。
[35]參見趙景深、李平、江巨榮《中國戲劇史論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7頁。
[36]吳自牧《夢粱錄》卷四「妓樂」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頁。
[37]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上雜出版社1953年版,第227頁。
[38]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頁。
[39]胡忌《宋金雜劇考》,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頁。按:胡先生後來修正了觀點,認為過錦是隊戲。參見《菊花新曲破:胡忌學術論集》,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95頁。
[40]廖奔《論中華戲劇的三種歷史形態》,《戲劇》1995年第2期。
[41]萬斯同《明史》卷四五「宦官上」,《續修四庫全書》,第331冊,第385頁。
[42]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禁中演戲」條,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98頁。
[43]劉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頁。
[44]劉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頁。
[45]李斗著、許建中注評《揚州畫舫錄》卷一一,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頁。
[46]佚名《蕉帕記》,章培恆主編《四庫家藏六十種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8冊,第4頁。
[47]《明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8—1599頁。
[48]李漁《閒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頁。
[49]章炳麟《新方言·釋言》,《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冊,第47頁。
[50]李玫《明清戲曲中「小戲」和「大戲」概念芻議》,《文學遺產》2010年第6期。
[51]曾永義《論說「小戲」與「大戲」之名義》,劉禎主編《中國戲曲理論的本體與回歸》,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417頁。
[52]翦伯贊《清代宮廷戲劇考》,《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1輯,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頁。
[53]周妙中《清代戲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187頁。
[54]吳新雷主編《中國崑劇大辭典》,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頁。
[55]李真瑜《明代宮廷戲劇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頁。
[56]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頁。
[57]張月中、王鋼主編《全元曲》(下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4頁。
[58]隋樹森編《全元散曲》(下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111頁。
[59]薛寶琨《相聲藝術的源流》,《中國幽默藝術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頁。
[60]洛地《「戲弄」辨類》,《藝術研究》第12輯,1990年。
[61]曾永義《論說「折子戲」》,《戲劇研究》2008年1月創刊號。
[62]李玫《明清小戲的演出格局探源——兼及宋代「小雜劇」研究》,《文學遺產》2012年第6期。
[63]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順治朝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冊,第1438頁。
[64]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八「過錦」條,《續修四庫全書》,第1700冊,第285頁。
[65]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4冊,第8087頁。
[66]張相《詩詞曲語辭彙釋》,中華書局1953年版,第127—128頁。
[67]姜書閣《說曲》,江蘇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133頁。
[68]洪昇著,康保成校點《長生殿》,嶽麓書社2003年版,第3頁。
[69]佚名《療妒緣·聽月樓》,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頁。
[70]李漁著,於文藻點校《李笠翁小說十五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頁。
[71] 張岱《陶庵夢憶》補遺「魯王」條(與《西湖夢尋》合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頁。
[72]佚名著,金心點校《檮杌閒評》,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