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街頭官僚」的權力與……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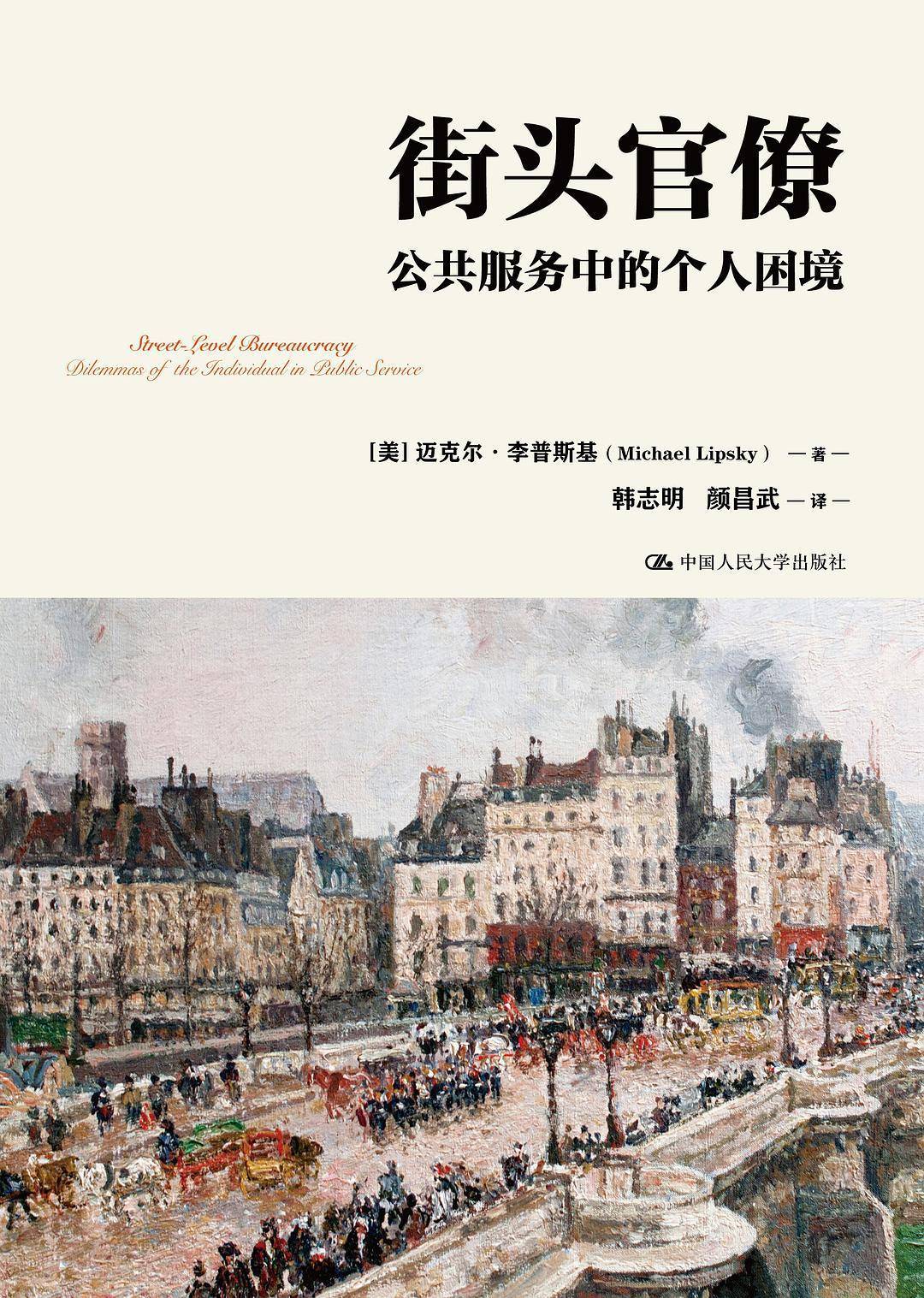
《街頭官僚:公共服務中的個人困境》,[美]麥可·李普斯基著, 韓志明、顏昌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4年2月版,88.00元
著名政治學家、美國公共行政科學院院士麥可·李普斯基(Michael Lipsky)的《街頭官僚:公共服務中的個人困境》(Street-Level Bureaucracy: 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是公共行政與社會政治學研究的名著,街頭官僚研究的開山之作,但是在我看來同時也是一部有關公共治理與服務的工作手冊——在概念性和理論性的深刻論述之外,作者更多的是對政策機構、公務執行者以及服務對象的真實狀況、存在問題和可能出路的揭示和討論。從1980年原書出版到現在雖然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但是所論述的許多問題和思路並沒有過時。因此這本書不應該僅僅被放在學者的書齋里,也應該回到街頭,回到那些站在街頭的「官僚」和被他(她)們服務或管制的對象的手中。
當然,正如「譯者前言」所提醒的,本書作者主要是立足於西方國家的政治和社會語境來開展對街頭官僚的研究,許多觀點都具有明顯的西方話語特質,「因此,對於街頭官僚的解讀和思考都必須紮根於本土網絡」(XVII)。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作為公共政治研究的門外讀者,我在本文中更多只是根據作者的西方語境來談一點閱讀體會,並不涉及對「本土網絡」的研究。
這本中譯本是根據由羅素·塞奇基金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 )於1980年出版的原版翻譯,「譯者前言」中提到之前在2010年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了繁體中譯本,書名為《基層官僚:公職人員的困境》。該書原著在2010年出版了第二版,據說其內容對自1980年以後二十多年的社會現實的變化和學界研究的新進展有進一步更新(further updated),有點可惜的是,現在這本新的中譯本沒有根據新版翻譯。
說來有點意思的是,麥可·李普斯基在1969年為一本研究警察的書寫了一篇書評,由此激發了他對街頭官僚共同的工作特徵的研究興趣。同年他為美國政治科學協會年會寫了一篇題為《建立一種街頭官僚理論》(Toward a Theory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cy)的論文(後來收錄於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Urban Politics ,1977),正式提出了「街頭官僚」的概念和理論,主要探討了工作結構對於建立公眾與公職人員之間聯繫的重要性。這本《街頭官僚:公共服務中的個人困境》就是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擴充而成,並且提出了許多新的思考。
關於什麼是本書所說的「街頭官僚」,作者在「導論」中有清楚的界定:「本書所說『街頭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是指在其工作過程中與公眾直接打交道,並在執行公務的過程中擁有實質性裁量權的公職人員。如果某一公共服務機構中街頭官僚占有很大比例,那我們就可稱之為『街頭官僚機構』(street-level bureaucracies)。典型的街頭官僚有老師、警察和其他執法人員、社會工作者、法官、公共律師和其他法院工作人員、衛生工作者及其他在政府項目內提供服務的公職人員。」(第3頁)應該注意到這是作者在美國生活語境中對「街頭官僚」的分類,在不同語境中或許像教師、法官這樣的職業不會被列入「街頭官僚」之列。
從繁體和簡體兩個中譯本的翻譯來看,把書名中的「Street-Level Bureaucracy」譯作「基層官僚」或「街頭官僚」是各有優劣。「Street-Level Bureaucracy」直譯是「街道級官僚制(或機構)」的意思,而在作者書中談「街頭官僚」用的是「street-level bureaucrats」,兩者之間本來是有區別的。但是考慮到書中主要論述的就是「官僚」,因而書名的譯法也是可以的。從上述作者對「街頭官僚」的界定來說,實際上指的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一線工作人員」(Front-line workers),或者是從職務身份的角度來強調的「公職人員」——要注意的是在這裡不能等同於「公務員」。對於「street-level」,譯作「基層」似乎更符合我們熟悉的語境用法,譯作「街頭」則位階太低,甚至在用於表示身份的時候有時會與「混混」連在一起。但是在這本書的內容語境中,「街頭官僚」這個譯法卻是更為傳神、更接地氣。在我看來,「街頭」比「基層」更能突出一線工作人員與工作空間的關係——他(她)們基本不是端坐在辦公室,而是在廣場、街道、高速公路等公共空間,街頭是最通俗、最有象徵性的表述。另外在「街頭」的背後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可以馬上追問的是哪裡的「街頭」、什麼樣的「街頭」?更準確的提問就是「何種科層體制中的街頭?」——從某一條橫貫東西的大街到一線大城市的街頭再到鄉鎮上的街頭,真正的區別在於在這些「街頭」背後那些科層體制的巨大區別。因此籠統地談「基層」或「街頭」也是沒有用的,正如籠統地談「空間」是不接地氣的。
再看「官僚」,就是剛才說的「一線工作人員」,或者說就是常用的「基層幹部」這個稱呼。但是如果這樣譯的話就完全沖淡了作者在書中一直強調的那種徹底籠罩著這些「工作人員」「幹部」身上的官僚制、科層制的色彩,而關於這種體制對個體的影響正是作者在書中論述的核心議題,而且用在書中所描述的那些現實生活語境中也顯得太書面化甚至是太落入另外一種語境中的「政治正確」了。譯作「官僚」,當然也不是沒有問題。過去談起「官僚」就會想到「官僚主義」和如何「反對官僚主義」,後來又會想到什麼級別的官僚,到現在恐怕更會想到的是真的官僚還是假的官僚——究竟是體制內的還是體制外的?產生這樣的疑問是因為許多人可能有過這樣的經驗:對方看起來一身的官威,後來才知道只是臨時工。這麼說當然沒有看不起臨時工的意思,只是因為每當需要啟動問責的時候,這些「官僚」的臨時工身份常常造成無人需要負責的結果。
總之,從這些不同地域的真實語境中的各種用法綜合起來看,把「street-level bureaucrats」譯作「街頭官僚」應該說是形象的、接地氣的。
其實,「街頭官僚」這個譯法在2000年以來就開始被國內政治學、社會學界使用,在網絡檢索中可以看到有不少論文的題目就是用這個概念。甚至在最權威的主流官媒中也使用這個概念,如出現《管住「街頭官僚」是吏治新課題》這樣的題目(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3/1204/c241220-23744437.html)。但是也要看到,「街頭官僚」還是沒有在大眾傳媒、文宣輿論中成為流行使用的概念,原因似乎不難理解:「官僚」總是容易與「主義」「作風」連在一起而帶有貶義。
還有一個問題是李普斯基沒有想到、在書中也沒有談到的,那就是與「街頭」和「官僚」有緊密聯繫的「身體」——既然不是坐在辦公室而是站在街頭,無論官僚還是他的服務對象或控制對象,首先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就是他們活生生的身體。雙方身體的動態、動作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街頭政治的形象呈現,傳達出不再被遮蔽的權力意志或權利意志,是具身的街頭政治社會學議題。可能在人們關於某些特殊時期的記憶中,街頭官僚與服務對象最經常發生的衝突就是身體對身體的控制——是否允許穿制服的公職人員進入某一空間?在沒有受到任何合法的行為約束管制之前,被管理的服務對象是否有權自由出入某一空間?個別街頭執法者不斷上演的某些身體行為是否徹底顛覆了人們對於「公共服務」的認知?所有這些都是刻骨銘心的街頭政治記憶。由於身體的在場和認識到身體的在場,街頭政治中的「人性」概念有了具身化的形象顯現,表現為身體的語言、節奏、情緒等不同形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身體政治就是衡量街頭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天然尺度,也是街頭官僚如何表明自己的屬人性質的重要指標。一個理性的、有倫理良知的街頭官僚應該不難發現他的身體語言是關乎公共政治的合法性以及塑造人與世界的良善關係的重要因素。
再看該書副標題是「公共服務中的個人困境」(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指的是在公共服務的領域中,無論是執行政策的街頭官僚還是尋求服務的個體都會面臨個人選擇和行動的困境,經常出現行動的悖論和必須承受的各種壓力。作者在書中一方面研究了作為個體的公職人員在公共服務中的作用、行為模式和面對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反覆論述和分析了作為管理或服務對象的公民所面臨的各種個人困境。中譯本繁體版把副標題譯作「公職人員的困境」,把「個人」理解為單純指公職人員,應該說是不完整的。
經過從書名的翻譯中引起的相關概念的思考和討論,也可以看到作者的研究語境與讀者的接受與理解語境的差異性,這或許有助於在「本土網絡」中閱讀與思考。現在可以回到該書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論點來談。
李普斯基在「前言」中首先說該書是「在探尋個體公職人員在公共服務中的作用」,接著馬上就強調了街頭管理機構的工作人員「直接與公眾打交道,並在決定對公眾的獎勵或懲罰上具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這一核心議題。接下來他說社會學家常常對組織和政府的行為進行一般性解釋,但很少具體解釋作為個體的公民和公職人員如何受到這些政府行為的影響以及如何引發各種各樣的個體行為(前言,xix)。這也是近年來我在閱讀一些有關國內公共決策研究和經濟社會研究著述時深感困惑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在這些高論中只見宏觀意義上的機構、形勢和文本,而作為個體的決策者、執行者和各種行動者不知道哪裡去了,更不用說對這些個體的選擇、決定和反應行為的微觀分析。
因此,李普斯基說的這段話就非常有針對性:「我認為,街頭官僚的決定、他們確立的工作慣例,以及他們為應對不確定性和工作壓力而開發的手段,實際上構成其所執行的公共政策。我認為,對公共政策的最佳理解,不應限於立法機構或高層行政官員的頂層辦公室,因為在某些重要方面,公共政策實際上是在嘈雜的辦公室和街頭官僚的日常境遇中所形成的。我認為,政策衝突不僅表現為利益集團之間的爭執,還體現為個體公職人員與公眾之間的鬥爭——後者對前者的工作或質疑,或服從。」(前言,xix)這就是說,不能認為街頭官僚僅僅是執行政策的人——雖然他們在執行任務過程中常常是這樣對公眾表白的。實際上由於他們在執行任務過程中擁有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他們形成的工作慣例、手段實際上就是對公共政策的某種制訂或修訂。這讓人想起白德瑞(Bradly W. Reed)在《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Talons and Teeth :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尤陳俊 、賴駿楠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中對清代巴縣衙門的胥吏群體如何針對日常行政運作的實際問題而創製並奉行一些慣例、規則與程序的分析,這些慣例、規則既可以部分滿足完成職責的需求,同時也建立起內部的「班規」以規範秩序。雖然在價值評價上為清代胥吏翻案做得有點過了,但是也涉及李普斯基所講的街頭官僚的那種工作環境與自由裁量權的問題,對於被管轄的老百姓來說實際上也就是成為他們必須遵守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回頭來看全書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導論」分別討論了「街頭官僚的關鍵角色」和「作為政策制定者的街頭官僚」這兩個重點問題,論述了作為公共利益的供給者和公共秩序的維護者的街頭官僚如何成了政治論爭的焦點,論證了街頭官僚既是政策的執行者也是制定者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對於讀者來說,重要的是要充分認識到「街頭官僚提供獎勵和進行懲罰的方式,建構和設定了公眾的生活和機遇。這些方式規定了人們行動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目錄,第1頁)。——在思考「當我們在談論生活、機遇和環境的時候,我們究竟是在談什麼」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我們是否都會把與街頭官僚打交道的經驗聯繫起來呢?第二部分談「工作情境」,涉及機構與個人獲得的資源、目標與績效如何評估、街頭工作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等問題,這些工作情境的性質與特徵無疑對基層官僚執行政策帶來的各種影響。第三部分「實踐模式」主要談的是機構提供公共服務的限量配給問題、當事人在各種情境中進行自我調適的心理策略、街頭官僚與服務對象打交道時的心態等問題,指出研究者「必須仔細地探究街頭官僚為應對工作上的困難和不確定性,所形成的慣例和帶有主觀性的回應方式」(目錄,第3頁)。第四部分「街頭官僚的未來」對於評估機制中以量化指標推斷服務質量的做法質疑,也評估了財政危機對於基層官僚所造成的影響,最後圍繞「對人性化服務的支持」提出了改革和重建公共服務功能的方向與建議。
在街頭官僚的執法行為中,自由裁量權是一個最核心、最容易產生爭議的問題。由於執法現場的情境、問題極為複雜多變,公共政策中的規章絕無可能預設能夠恰當判斷和解決所有問題的條文,因此街頭官僚必須握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這種權力不僅使許多現場問題得到判定或解決,也為街頭官僚針對不同服務對象的情況作出正確的區別對待、對機構政策中的那些明顯不合適的規定作出靈活調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也是政策的制定者)以及在對機構的問責中保持自己的權利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但是自由裁量權也必然帶來不利的因素,如存在個人主觀性偏見的可能、難以問責等。在這裡李普斯基有一個觀點很值得重視:「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不願意完全限制街頭官僚的自由裁量權。然而,在某些情形中,限制自由裁量權是可取的。很難說街頭官僚所扮演的每一個自由裁量角色都應繼續存在。如果街頭官僚的自由裁量權導致服務對象受到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待遇,且沒有任何補償性福利,就應該改革制度,消除這種無法彌補的不公平的根源」(200-201頁)。他提到一些例子來說明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權的,如將公共福利中的社會服務職能與核定收入補助職能分開,可以限制街頭官僚在決定是否補助時的自由裁量權,同時也使官僚在提供服務時不必受累於服務對象的投訴或其旨在獲取更多福利而設計出來的策略(201頁)。這是合理的、有建設性的策略。
在全書的分析、論述中,作者充分使用了來自美國社會語境中的各種調查數據、媒體專題論述以及學界研究等成果,實證性分析與理論闡釋並重,重點始終圍繞著公共服務領域中所有當事人的選擇、行為、心理和困境。如果把作者基於美國經驗的分析話語用更通俗的語言表述出來,大致上就是這樣的圖景:處於行政體系的「神經末梢」的官僚在街頭上與服務對象的距離就是「最後一百米」或「最後一米」,肩負著落實公共政策和服務群眾的光榮使命。但是由於某些聯邦與地方機構的政出多門,出台公共政策常常具有隨意性、重複性、壓力性,壓力層層傳導、任務壓緊壓實的結果是越累越忙成為街頭官僚的工作常態。作者在書中也用了很多數據和例子揭示了在機構中一方面崗位濫設、冗員膨脹;另一方面崗位職責不清,基層人少事多,一人多崗和一崗多責的情況相當常見,最後的結果是由於沒有嚴格、清晰的崗位職責,「問責」就成了空話。
但是在這裡還應該指出和補充的是,由於作者研究語境中的經驗與視野的局限,在李普斯基關於機構與個體的衝突的問題意識中缺少了更關鍵的「問題」意識——這個「問題」意識就是當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機構是否會把「街頭官僚」看作是要解決的問題、「街頭官僚」是否也會把服務對象看作是要解決的問題。在書中基本上也沒有觸及許多官僚機構都有的「N多」現象(會多、文件多、指標多、表格多、檢查評比多、審計彙報多……),也沒有把「N多」現象的後果進一步提煉為「責任無限大、事情無限多、休息無限少」這樣的通俗講法,另外在有關崗位職責的微觀分析中也沒有談到在白紙黑字表格中「崗位職責」欄里的那句常見的話 「完成領導交辦的其他工作」——至於什麼是「其他工作」,只能等「領導交辦」的那一刻才會知道。最後還有一點遺漏的是關於績效的問題,雖然在書中談了很多如何統計績效,但是卻沒有談到在科層等級關係中常見的一種統計績效的現象:成績都是上面的。至於從大的方面來說,某些街頭執法者通過受賄等方式以權謀私的現象由於既是普遍性的,也是屬於違法犯罪的性質,因此沒有在書中展開更多的論述則是合理的。
對於街頭官僚所起作用的總體評價,李普斯基似乎是不太經意地給出一個表述:「在最好的情形下,街頭官僚能發展出一套良性的大規模處理模式,這或多或少地允許他們公平、恰當和成功地與公眾打交道。在最壞的情形下,他們屈從於偏見、刻板印象和例行公事,以服務於自身或所在機構的目的。」(前言,xx)看來這是比較審慎和客觀的評價。由此想起在十多年前我讀英國社會政策學者哈特利·迪安(Hartley Dean)的《社會政策學十講》(岳經綸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的時候,對於書中出現的「街頭官僚」這個概念的印象是很負面的,因為作者是在談到為了爭取貧困社區利益而與英國政府辦事部門作鬥爭的語境中使用「街頭官僚」這個概念,並且對其所作所為深感無奈和憤怒。而正好在那個時候,我們正在媒體上開展有關本地醫保制度新政與醫院博弈的困境、經濟適用房的制度設計對低收入者的價格歧視、電梯時代的公共責任等問題的公共討論,當時的焦點是關於「社會支出」「福利體制」「公共責任」等社會政策的基本概念和理性思辨,而這些概念和價值認知還遠未成為公共輿論的共識;尤其是在當時個別相關利益部門負責人的自我陳述或辯解中,對社會政策中的價值問題的漠視、曲解甚至敵意比比皆是,因此感到哈特利·迪安使用的「街頭官僚」概念中的貶義就很有針對性。
其實,李普斯基對於街頭官僚的個體處境一直充滿了同情的了解和熱情的支持態度。很令我感動的是他對理想主義受挫的街頭官僚的理解與同情:當他們的理想和主動工作的熱情在現實面前逐步磨滅的時候,他們能夠如何繼續選擇自己的人生呢?繼續留下來,自然會在工作中成長,其技能也日臻完善,「但他們也會調整自己的工作習慣和態度,降低對自己、對服務對象、對公共政策潛力的期望值」(前言,xx)。更殘酷的是,繼續留下來是否意味著「繼續為聲譽不佳,有時甚至是殘酷無情的公共機構效力?如果當前的模式重演,這就意味著要與犬儒主義和現實的工作環境進行一場註定失敗的鬥爭,並眼睜睜地看著服務理想轉成為個人利益的鬥爭」(同上,xxi)。儘管不知道有多少街頭官僚會產生這樣的內心焦慮,這也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同樣更令我感動的是在李普斯基的身後有一位支持者給予他的影響和支持:Suzanne Lipsky「對本書做出了許多貢獻,其中之一就是,她認識到並分析了人們維繫和恢復其人性光輝的潛力,雖然人們也在助長壓迫性社會制度或成為其壓迫對象」(致謝,xxiv)。關於「人們維繫和恢復其人性光輝的潛力」,這個問題實在太重要了,太需要互相支持以恢復我們的信念。
作者在全書最後提出要通過「一場廣泛的爭取社會和經濟正義的運動」和具體的改革措施,在街頭官僚機構中發展出一種「支持性的環境」——對此我的理解和概括是:支持管理機構能夠堅持以服務對象為導向,支持所有的服務對象都能夠在每一項議題中獲得尊重和保持尊嚴,支持街頭官僚能夠在不利的環境中也能體面地工作、實現自己的理想人格(210-213頁)。這是全社會在面對街頭官僚的權利、邊界等問題困境中應該共同全力爭取的公共服務前景。這樣的話,許多工作在「街頭」情境中的「官僚」都會成為爭取歷史進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