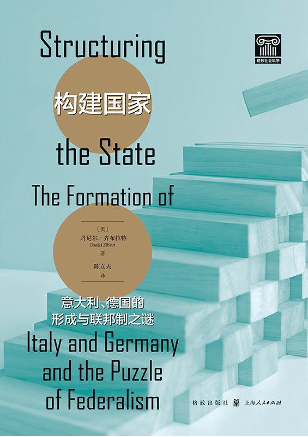
《構建國家》,作者: [美] 丹尼爾·齊布拉特,譯者: 陳立夫,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
研究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學者普遍關注以下議題:在特定區域內的若干小型領土國家,在何種力量的作用下,會以民族話語聚合成一個領土面積涵蓋整片區域的大國。不同學者通常會在此議題上作深化或細化。《構建國家》一書作者 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聚焦德國和義大利的民族統一進程,通過考察兩個國家的制度形成,提出以下研究問題:為什麼兩片在諸多方面表現相似的語區會在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走出截然不同的軌跡,即德語區國家最終統一成聯邦制國家,而意語區國家卻聚合成單一制國家?
齊布拉特考察了兩國從1830年至1880年的建國史,即被作者稱為「民族時刻(National Moment)」的時間段。據作者介紹,關於民族國家建構這一議題,過去的研究路徑大致有三,即從觀念、文化和力量三個面向切入。作者認為,傳統路徑無法用於解釋德國和義大利的道路分化,因為兩者在統一進程啟動前,在觀念、文化和力量分布方面有諸多相似性,但是進程啟動之後,卻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軌跡,即德語區走的是「協商性統一(negotiated unification)」之路,而意語區走的卻是「征戰性統一(unification by conquest)」之路。
齊布拉特 的核心論點大致可作如下表述:
「一塊區域最終能否通過協商之路升級成聯邦制國家」與「該區域內中心政治單位相對於非中心政治單位而言的軍事力量優勢」無關,其主要取決於「這塊區域內的非中心政治單位是否具備相對於自身社會而言的滲透性能力(infrastructural capacity)」,如果有,這些非中心政治單位就能整合起來,獲得和中心政治單位進行協商或話語博弈的籌碼,從而促成聯邦制的建立。
齊布拉特所指的政治單位是現代德國各州以及現代義大利各行政大區的前身,19世紀中葉以前,它們是擁有固定邊界、由特定的統治集團及有限人口組成的領土型國家(後文將簡稱「邦」,states)。德國建國前,德語區有17個邦,普魯士(Prussia)是中心邦,義大利建國前,意語區有7個邦,皮埃蒙特(Piedmont)是中心邦。中心邦是指統一化進程的發起者,其餘則是邊緣邦。
統治集團在固定領土內總是享有設置政治議題的特權,但設置議題不等於貫徹議題,因為後者通常受到外部條件的約束。所謂滲透性能力,是指政治單位內的統治精英能夠憑藉官僚系統及各類社會資源以貫徹議題的能力,如收稅、徵兵等。齊布拉特將其用作解釋國家政治制度形成的自變量,指出德語區內非普魯士邦的滲透性能力普遍較強,在一體化進程中可以免於普魯士的干預與整合,而意語區的非皮埃蒙特邦的滲透性能力普遍較弱,在一體化進程中無法免於皮埃蒙特的權力攫取。
齊布拉特在研究中綜合定性與定量方法,在測量各政治單位的特徵時採取了較為巧妙且可複製的做法,總體敘事也清晰。但是,他對力量/軍事力量論者和觀念論的反駁並不怎麼成功,而且在案例選擇和提問預設上也都有問題。本文將先概述《構建國家》一書的寫作邏輯,而後對其展開批判性分析。
撰文|陶力行
《構建國家》的寫作邏輯
政治制度乃人為建構的產物,但人建構國家的方式並非任意,其行動方式及策略選擇常受現有條件的約束。在處理該議題時,歷史學家傾向於突出具體個人的影響,而社會學家則傾向於突出原有條件的約束。齊布拉特的自我定位是社會科學家,其將自己的理論稱為供應端理論(supply-side theory),即敘事上,傾向於強調各邦在建國以前就已經具備的制度性及歷史性條件對於國家建構進程的影響。因此,其在研究中,花了大量筆墨描述德意兩國在前國家時期的各邦狀態,以及在其筆下,被歷史學家視為重要的政治行動者多扮演「道具」角色。
全書共七章。第一章是導論,用於交代研究問題、說明方法論以及排除傳統解釋。齊布拉特先總結了三種解釋聯邦制形成的傳統理論,然後逐一排除。觀念論認為,前國家時期各邦意識形態越主張去中心化理念,越有可能導出聯邦制,作者反駁稱,義大利中心邦的政治精英普遍持聯邦主義立場,但最終走向單一制;文化論認為,各邦文化越有獨立性,越有可能導出聯邦制,作者反駁稱,德國和義大利各邦在建國前都持堅定的文化地方主義立場,但最終分化;力量論認為,中心邦相對於邊緣邦的軍事力量越弱,越有可能導出聯邦制,作者反駁稱,建國前的普魯士相對邊緣邦而言有絕對的軍事優勢,但最終導出聯邦制。
在齊布拉特看來,無論是單一化還是聯邦化進程,都是各邦博弈的結果,即地區間相互作用的產物。就博弈而言,一個玩家能否常駐牌桌,不在於其是否有高超的牌技,而在於其是否有足夠的籌碼。如果各邦的籌碼差不多,自然會走向聯邦制,但如果籌碼相差懸殊,那麼就會走向單一制。問題是,籌碼來自哪裡?齊布拉特通過引入滲透性能力這一概念,向讀者說明:籌碼來自社會,一個邊緣邦只要能從社會中汲取足夠的資源作談判籌碼,那麼它就能上牌桌、與中心邦抗衡。
第二章是對兩國情況的概覽,作者通過定量手段測量兩塊語區內中心國家間的差異、非中心國家間的異同,以及中心國家與非中心國家關係的差異。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回溯了民族時刻的德國和義大利的民族統一過程,用定性敘事補充了第二章的定量描述,藉此說明為什麼理解地區間的相互作用對解釋新型民族國家的崛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對核心問題的回答,作者通過定量手段測量了兩地各政治單位的「政治發展」及「滲透性能力」,並回顧了政治領導人針對不同的制度條件及歷史過程做出了哪些反應及策略。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結尾中,作者分別指出,皮埃蒙特邦的政治精英之所以能推行單一制並非其有意的結果,而是由於邊緣邦太弱,無法阻礙中心邦的進程,以及德國之所以會走向聯邦制,並非普魯士領導人俾斯麥的個人智慧,而是因為民族統一之前各邦已經建起了強大的官僚組織,具備較強的滲透性能力,相互之間已經達成平衡。最後一章是結論,除總結上述內容以外,作者進一步說明為什麼其論點可以被擴展至其他案例的分析。

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兼伊頓政府學教授,2023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齊布拉特的研究重點是歐洲政治和民主比較研究。
《構建國家》的問題
整部作品篇幅不大,而且書寫清晰,所以讀者很容易抓住作品要點。但是,好的寫作不代表好的研究。簡單來說,該作有以下五點問題:
第一,作者對於軍事力量論的反駁顯得太過隨意。在作者看來,如果軍事力量論是對的,那普魯士也應該執行征戰式統一,因為普魯士相對於其他德意志邦的優勢要遠高於皮埃蒙特相對於其他義大利邦的優勢。他所提供的證據是兩國在統一進程開啟前的軍事實力比較:「普魯士占據了未來德意志帝國人口的57%,軍事支出占所有德意志國家軍事支出的54%,所占領土占未來德意志領土的54%,而皮埃蒙特占未來義大利人口的6%,軍隊人口占義大利全體軍隊人口的 29%,領土也只占義大利總體領土的 22%」。
上述數據屬於靜態數據。靜態數據而言,普魯士若要執行征戰性統一確實會比皮埃蒙特做得更容易,但比較靜態數據本身缺乏說服力,因為軍事實力在戰爭啟動之前通常無法顯現。軍事實力的衡量需要依賴於互動性數據的測量,否則,類似於戰爭動員能力、軍隊對於地理條件的適應能力、單兵作戰能力等更能反映軍事實力的證據無法被看到。畢竟,長得瘦不見得不能打。有意思的是,作者自己還提供了「自我反駁」的證據:就強制性能力——即徵兵率——而言,皮埃蒙特相對於其他義大利國家的優勢(1.53:1)要明顯高於普魯士相對於其他德意志國家的優勢(1.09:1)。如果我們把徵兵率視為戰爭動員能力的話,那軍事力量論依舊有較強的說服力。
第二,作者提出的解釋變量——即非核心政治單元的滲透性能力——和軍事能力存在較強的相關性。軍事能力的獲得依賴於嚴密的組織訓練或戰爭經驗的日積月累,一般而言,有能力進行組織訓練以及積累戰爭經驗的國家本身也是有較強滲透力的國家,否則無法在即時性條件下動員起足夠多的資源。從滲透性力量或組織力量角度看,德意志非中心國家應該實力也不差。雖然單個來說都不是普魯士的對手,但是難保他們不會在特定條件下形成統一共識。
19世紀中期的普魯士非常強大,俾斯麥上任總理之位後執行鐵血政策,靠軍事實力帶領普魯士軍隊順利地趕走了丹麥人、奧地利人以及法國人,為德國統一鋪平了道路,但由於其過於強硬的政策,以至於德意志內部各國都視其為洪水猛獸。即便軍事上,普魯士強大,皮埃蒙特弱小,但皮埃蒙特面對的博弈對手只有6個,而普魯士的對手多達16個。普魯士面對的軍事壓力不見得比皮埃蒙特小。而且,德意志外圍也都是一批虎視眈眈的狼,一旦開戰,那些先前被趕出的「狼」,很有可能重返。為什麼俾斯麥不會因為軍事上的擔憂而有意選擇協商呢?

腓特烈大帝肖像。
第三,作者對於觀念論的反駁也不怎麼成功,因為他沒有區分意識形態和話語。所謂意識形態,就是一套以分類、排序、篩選為目的而設定的優先性原則;所謂話語,就是用特定語詞、語句表達特定原則的敘事。作者錯在,看到義大利和德國在統一之前都盛行聯邦主義論調或都流傳聯邦主義觀念,就假定兩者共享同一種意識形態。為了突出這一論點,作者還援引皮埃蒙特政治領袖 Cavour 於 1950 年在議會上發表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論調。可問題是,在當時的歐洲,在那個所謂「民族時刻」的關鍵年代裡,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時髦話語。
從十七世紀開始,歐洲就有一大批知識分子都是聯邦論者,比如魯道夫·雨果、孟德斯鳩、大衛·休謨、讓雅克·盧梭、伊曼努爾·康德、約翰·米爾、蒲魯東,等等。一個政治領導人,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援引聯邦主義話語並不是什麼稀奇之事,為什麼作者會認為他的話是對某種意識形態的堅信呢?從操作的角度而言,一個人既可以做到意識形態上不信聯邦主義,同時又可以在話語上不斷訴諸聯邦主義,畢竟,說一套做一套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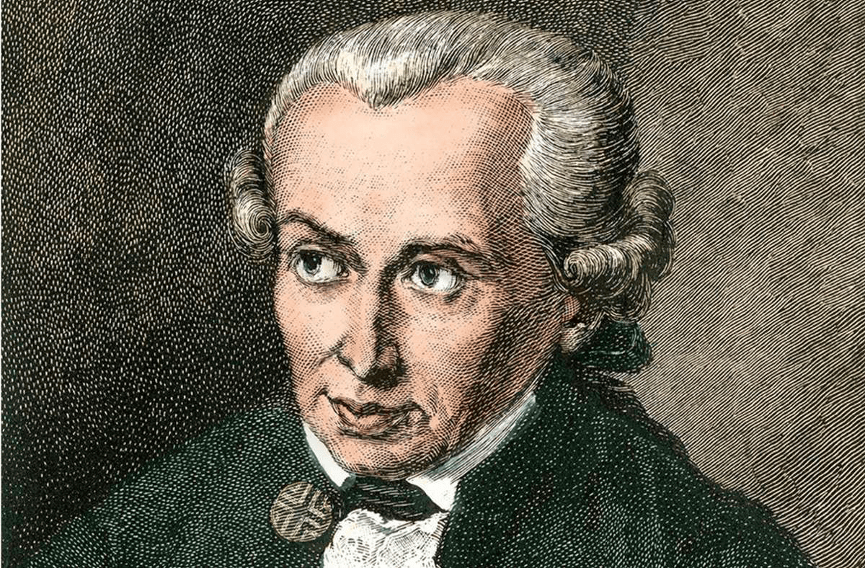
伊曼努爾·康德畫像。
如果一個人有很強的意識形態且認為話語應該與意識形態保持高度一致,那麼這個人往往會順著自己的意識形態「一根筋」走到底,不顧現實條件發生什麼變化,他都會堅持到底,但如果一個人本來就沒有很強的意識形態並認為意識形態與話語可兩分,那這個人就會在自己認為有必要的「關鍵時刻」,迅速修正自己的話語,以適應環境的需要。就「皮埃特蒙領導人能夠在特點時刻輕易地改變自己的話語並修訂自己的行動策略」一事就可看出,皮埃蒙特的領導人或領導群體是一波弱意識形態者,其並不堅守某種特定的原則。就這點而言,作者認為德國和義大利在統一前擁有相同的觀念條件是一種誤判。
第四,作者將自己的理論稱為供應端理論,這就意味著,他忽視了需求端的訴求,即工業化的要求。十九世紀的義大利和德國相對於英國與法國而言,都是後發國家。對於亟待發展工業的後發國家而言,官僚系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對於工業化的追求不僅會迫使官僚系統升級,同時也會促使官員採取更激進的行動策略。德語區在1830年前後就啟動工業化,1850年之後,工業化高漲,但是意語區直到1860年都很「落後」。從產業結構角度講,兩個地區在統一進程啟動前已相差太多,以至於他們對未來國家的形態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期待。
從行為路徑看,德國是先立產業,後統一,而義大利則是先統一,再立產業。促進工業化是民族國家建構的最重要事項之一,但由於兩國在統一之前就已在工業條件方面展現出顯著差異,那兩國在建國之後的制度安排上自然會有明顯的傾向性不同。對於一個已然工業化的國家而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找對未來產業,以便能在大國競爭時實現彎道超車,但對於一個尚未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而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通過「搞雞娃」打下穩固的工業基礎。單一制國家有利於「搞雞娃」。從「義大利在1860年建國之後就迅速啟動工業化」這一事實就可看出,義大利領導人在建國之前就已經有了明確的「搞雞娃」計劃。
工業化的比較如此重要,可作者壓根就沒提——儘管他本來是有機會提的。搜索作者英文版文本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的關鍵詞「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可發現,在涉及德國的內容中,工業化總計出現了 12 次,而在有關義大利的內容中,只出現了1次。很遺憾,他連自己寫什麼都沒細看。為什麼會沒看到呢?我推測有兩個原因:第一,太想排除各種變量的干擾;第二,太想弱化行動者的重要性。在結構與行動者的選擇上,他的結構主義立場太濃。
第五,研究案例太少,不足以析出明確的因果關係。社會學科研究歷史議題的難點在於其研究對象總是處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之中,以至於針對任何一種現象都會產生多因解釋,且每一種解釋都會顯得「多多少少有點道理」。也正因為此,研究者很容易在自己的研究進程中植入自己的價值偏好,並憑藉自身眼光任意敲定自變量。解決該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增加比較案例以稀釋自身偏見的影響。比較的案例越多樣,能排除掉的干擾因素就越多。然而,齊布拉特的對比研究只用了兩個案例。改進方式就是將印度、日本等國納入比較。
「聯邦制/單一制」這組範疇是從央地關係角度描述現代民族國家政治制度的概念工具,但就現實經驗而言,在聯邦制和單一制之間,並非界限完全明晰。一個國家完全可以在政治結構上表現為單一制,但在具體政策的制定與貫徹上,更顯聯邦性。例如,義大利這個國家雖然是單一制國家,但在一些大區內,立法和行政享有非常高的自主性。依我見,聯邦制/單一制的起源問題已經過時,更值得研究的是聯邦性和單一性。後續研究者如果有興趣在此議題上作深化,可從單一制下的聯邦性或聯邦制下的單一性角度出發以構建研究問題,這樣更有助於挖掘有意思的反常案例。

紀錄片《俯瞰德國》劇照。
總結
西方學者在研究國家建構時,總是會將聯邦制與單一製作為分析的先驗概念,這是因為政體還原論是他們理解社會現象時的內在意識。這一意識傳統在古希臘時期就已形成,一直延續至今。雖然齊布拉特宣稱自己的研究是經驗研究,但就我的閱讀感受而言,該作是從理論出發但有意包裝成從經驗出發的研究,其通過演繹聯邦制這一概念,尋找能夠表征聯邦性的證據。與過去研究相比,其只不過是找了不一樣的證據。但如我之前所言,由於沒有將前人理論駁倒,所以其研究至多算是補充說明,而非超越。依我見,學者若要擺脫前人的束縛,那就要起底自己的認識論,從認識論層面將思想傳統中的先驗假設踢掉。
雖然《構建國家》漏洞百出,但在西方學究眼裡,該作還是做出了一定的學術貢獻,其於2007年獲得年度美國政治社會學會歐洲政治與社會分會的最佳著作獎。我推測,該作的主要貢獻可能體現在方法運用上,即同時引入量化描述和歷史敘事,這樣的融合性嘗試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緩和了定性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之間的張力。但即便如此,該作的學術貢獻也非常有限。研究方法的創新主要依賴於議題的重置,只有好的問題才能迭出新的方法。齊布拉特的研究問題算不上新穎,所以其研究方法的結合也算不上新穎,其只不過是將手裡有的刀法輪番用了一遍而已。
撰文/陶力行
編輯/李永博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