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訓因地而異,對西方人來說,羅馬帝國的衰亡始終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話題,畢竟希臘、羅馬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根。
雖然有影射史學之嫌,但《帝國為什麼衰落》還是有一些奪目的地方。兩位作者挑戰了愛德華·吉本在其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中的經典論斷——羅馬帝國的衰亡是內生的,是羅馬社會道德和經濟墮落的結果,是羅馬帝國的內部腐敗使得羅馬在四世紀面對野蠻人的敵對入侵時變得無能為力。相比之下,希瑟和拉普利則認為,羅馬的衰落是多種因素和力量交織的結果。
這些因素和力量是羅馬在過去幾個世紀的擴張中無意中創造出來的。本書認為,羅馬帝國通過擴張,永久性地改變了歐洲和地中海世界的權力格局,在無意中在其邊緣內圍和外圍中創造了新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中心,在與它們的競爭中,羅馬帝國這才內外交困倒下。這種敘事無疑帶有極強的現代影射意味。
撰文|鄭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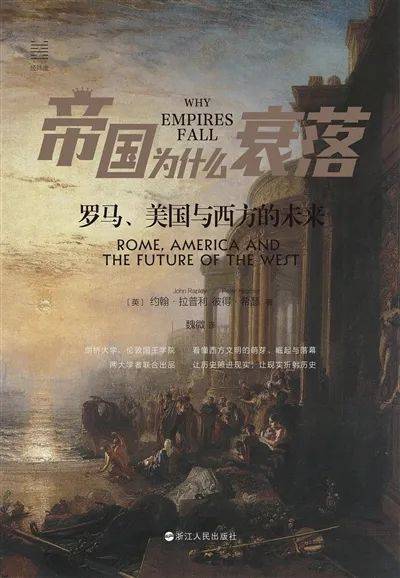
《帝國為什麼衰落》,[英]約翰·拉普利、[英]彼得·希瑟著,魏微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為什麼羅馬會衰落?
希瑟和拉普利首先指出,羅馬帝國的衰落並不是一條持續緩慢下跌的過程,在其末期,也不是一副民窮財盡的慘澹景象。正相反,有考古證據表明,正是在帝國崩潰前夕的公元4世紀,羅馬帝國的經濟總產出達到了羅馬歷史上的峰值。兩位作者甚至用「黃金時代」來形容這一時期。

電視劇《羅馬》劇照。
那為什麼羅馬帝國還會陷落?希瑟和拉普利歸結為以下幾種力量的交叉影響。
首先是經濟的自然流動,原先的羅馬帝國以義大利為其經濟核心地區,但是隨著羅馬和平的到來,帝國其他地區的自然資源得到了更充分的開發,帝國各行省開始繁榮昌盛,從而超越了義大利,傾覆了義大利作為帝國政治與經濟中心的地位。這一過程由內到外層層展開,在羅馬帝國的萊茵河邊界外,由於帝國財富、技術的流入,由於與帝國的長期互動,在一個狹長地帶內,蠻族開始了自己的早期國家建設。這增大了帝國在邊境地區使用武力的難度,使得羅馬帝國越來越需要通過外交手段(換句話說,離間、拉一派打一派、賄賂與收買)來保衛邊疆。
其次則是與超級大國波斯的國際競爭。在公元三世紀,隨著波斯薩珊王朝的崛起,羅馬帝國再次與波斯對峙,而這一次,羅馬帝國無法速勝。據保守估計,羅馬軍隊的數量在三世紀被迫擴大了50%(也有可能是一倍),國家稅收的四分之三被用于軍事開支,由此給羅馬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財政壓力。帝國的應對之策有如下幾條:貨幣貶值(從而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奪取地方城邦的財政收入給中央(這又導致了地方城邦公共精神的消亡,行省精英開始不關心地方治理,要麼進入中央為官,要麼退入農村自守);將帝國一分為二,東西部各自為戰(但這實際上影響了帝國體系的順利運作)。
到了公元四世紀末,蠻族開始成規模地遷入帝國境內,羅馬帝國大多數時候都能夠擊敗/安撫他們,但是,鑒於帝國財政的緊張程度,帝國實際上是在走鋼絲。無論多少次勝利都會被一次重大失敗所抵消,因為帝國缺乏必要的財力來重建其軍事力量。簡而言之,帝國耗不起,持續湧入的蠻族集團卻將帝國拖到了消耗戰上。而隨著帝國的軍事力量越來越不可能保證地方秩序與地方人士的財富,他們開始同入侵者進行談判與合作。「戰事一開則田稅加重,鄉紳遂為叛徒做爪牙」這種事就是當時局勢的寫照,這進一步削弱了中央財稅,增加了蠻族的力量,從而加劇了帝國秩序瓦解的惡性循環。
簡而言之,希瑟和拉普利認為,羅馬帝國的衰落是經濟轉移、外部挑戰和內部分裂共同作用的結果。

電影《迷蹤:第九鷹團》劇照。
在他們看來,歐洲近代帝國乃至當代西方也存在相似的形勢(但更有可能的是,希瑟和拉普利以今日形勢來比附昔日)。世界的經濟重心在過去的幾百年內在發生持續轉移,從原有的歐陸重心地帶開始向四周蔓延,從義大利北部,到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然後到美國。在西方世界的內圍邊緣地帶,隨著歐洲經濟秩序的擴張,隨之而來的經濟機遇也為印度塔塔家族這樣的地方精英人物所掌握,隨著時間的過去,他們開始利用手中的財富來謀求更多的政治權力,並最終推進了去殖民化的政治進程。這些西方國家的前殖民地構成了西方社會的內圍邊緣地帶。
希瑟和拉普利也認為,過去西方對世界的統治,也刺激了外圍邊緣地帶的重組。在全球化浪潮下,西方國家和邊緣地帶的國家達成了某種合作,為西方,也為邊緣地帶國家帶來了更多的財富。這種普遍繁榮改變了權力格局,而邊緣地帶國家的崛起對西方世界形成了明顯的挑戰。
最後則是西方國家的內部分裂。在過去,西方國家存在某種財政契約,即國家用普遍提高大眾生活水平為條件,來交換人民的忠誠。為了維繫這個財政契約,國家向富豪徵稅。但是在當代這一財政契約已難以為繼,許多西方精英已經將他們的資產組合轉移到邊緣國家,利用全球化謀取更多的利益,在如此做的時候,他們面對國家就有了更大的議價能力。與此同時,工薪階層則陷入債務、通貨膨脹和實際收入降低的境地,他們對全球化持相當批評意見。總之,希瑟和拉普利指出,過去四十年的經濟重組,在大多數西方社會中形成了兩個擁有不同經濟利益的政治選民團體。為了彌補社會分裂,大多數西方國家不得不借債度日,從而深陷債務危機之中。
希瑟和拉普利認為,正是以上這些相似性,使得當代西方人應該提高警惕——與羅馬帝國一樣,西方面臨著自己製造的危機。它的經濟運行在內圍製造了更多的競爭對手,在外圍則刺激著超級強權的興起;同羅馬帝國一樣,當代西方政府面臨著財政困難,難以提高稅收、維護社會秩序;同羅馬帝國一樣,當富人看到他們的特權下降,他們往往選擇與最近的野蠻國王/獨裁者勾兌,以保護他們的資產;同羅馬帝國一樣,西方社會面臨大規模的外來移民的衝擊。
西方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嗎?
筆者認為希瑟和拉普利與其是在總結帝國衰亡教訓,或者對羅馬帝國的衰亡做一精確的分析,倒不如說是在借古喻今。
不過,他們並沒有把這種比附貫徹到底,還是指出了古代羅馬帝國與現代西方社會並不完全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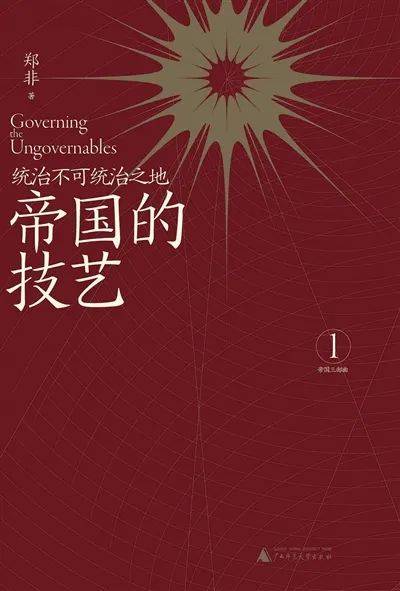
《帝國的技藝》,鄭非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頁folio,2021年11月。
1.儘管羅馬帝國和現代西方社會都有大量的外來移民,使得很多人產生了「野蠻人就在門口」的聯想,但這恰恰是古代與現代最不像的地方。
這是因為,在羅馬的例子中,外來移民往往伴隨著軍事化的征服浪潮而來,而且當時是一個靜態的農業經濟社會,外來移民不可避免地要與本地人之間進行零和競爭,爭奪有限的土地資源。相比之下,目前的移民是和平到來的,而且他們所遷徙而至的社會是一個現代社會,從總體上來說,移民參與了本地的工業經濟,做大了蛋糕,實現了經濟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估計,移民人口每增長1%,長期GDP將增長2%。這多出來的增長,可以有效緩解移民與本地人的衝突。希瑟和拉普利指出,在現代經濟體中,在對待移民的態度上,日本是一個顯著的例外,由於人口老齡化/缺乏移民,導致日本的退休人員已經占到總人口的30%,政府稅收的一半以上要用來提供社會保障。當然,日本這麼做的好處是保持了其文化和社會的凝聚力。
2.在超級大國政治方面,希瑟和拉普利認為,儘管其他地區的國家和美國之間存在激烈競爭與對立,但是目前雙方的競爭主要體現在經濟上,而非羅馬與波斯那樣進行直接的軍事對抗,雙方爭奪的是對生產性資產的控制。由於雙方經濟交織的程度如此之深,使得雙方的對抗很不經濟。
3.正如羅馬的繁榮也導致了其省份的繁榮,從而使這些省份有能力(最終有願望)與羅馬離心離德,西方創造的全球化已經導致了其周邊地區的繁榮和崛起,它們的實力不斷上升,也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但是同羅馬帝國不同,現代西方社會建立起了一系列國際合作機制,足以實現與發展中國家的協調,實現共同繁榮。
4.現代西方國家的組織程度較之羅馬帝國要強很多。羅馬帝國建立在帝國與行省地主的合作之上,統治基礎狹窄。而現代西方國家所建立的法治、言論和媒體自由、民選機制使得國家與其廣大人民之間有更強的聯繫,因而有更強的國家能力。
因此,希瑟和拉普利得出的結論是現代西方尚未面臨公元五世紀西羅馬帝國那種「最後關頭」,事尚可為。在最後,他們給出的政策建議是:緩和與其他地區國家的競爭,應致力於共同面對諸如全球變暖的公共問題;加強國際合作,實現共榮互利;建立新財政契約,減少社會不平等現象。

電影《拿破崙將軍》劇照。
古代與現代國家可以等量齊觀嗎?
《帝國為什麼衰落》的主要邏輯大致可以總結為——帝國的生命周期是由經濟移動決定的。帝國形成的目的是為帝國核心地區創造財富,但是這樣做的同時,也在帝國征服的內外地區造成了新的經濟格局,而這種經濟轉型必然會產生政治後果。這個說法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帝國衰落過程的新視角,這是本書的貢獻。
但是,這本書也有較明顯的缺陷,正如前所述,希瑟和拉普利並不是在做一個史學研究,而更多的是在借古喻今,為現代西方社會的治理提供一個鏡鑒,所以其論述論證並不周密完備。姑且不論具體史實的考據,只說將西方社會比擬成一個帝國,然後把它同羅馬帝國做整體對比,其實是需要更多論證的。同樣,把羅馬時代的地區經濟流動與近現代的全球化看成一樣的東西,似乎也有不妥,因為兩者的根本動力很是不同。這樣,將古代歷史和現代事件聯繫在一起進行比較的基礎就並不牢固。又比方說,儘管他們對羅馬帝國的衰落給出的是一個結構主義解釋,但是他們又暗示說羅馬帝國的衰落並不是必然的,本可簡單地阻止它的崩潰。
最後,兩位作者給出的政策建議似乎過於淺薄。他們對世界秩序的未來似乎過於樂觀,認定只要西方進行國際合作,就能夠容納內圍和外圍邊緣等諸多挑戰國家。對西方國家的國內政治,他們的方案也只是泛泛而談增加稅收和財富再分配,幾乎完全不提西方國家在政制方面也許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以適應新的社會形勢。這使得本書最終缺少必要的深度。
作者/鄭非
編輯/李永博 西西
校對/薛京寧